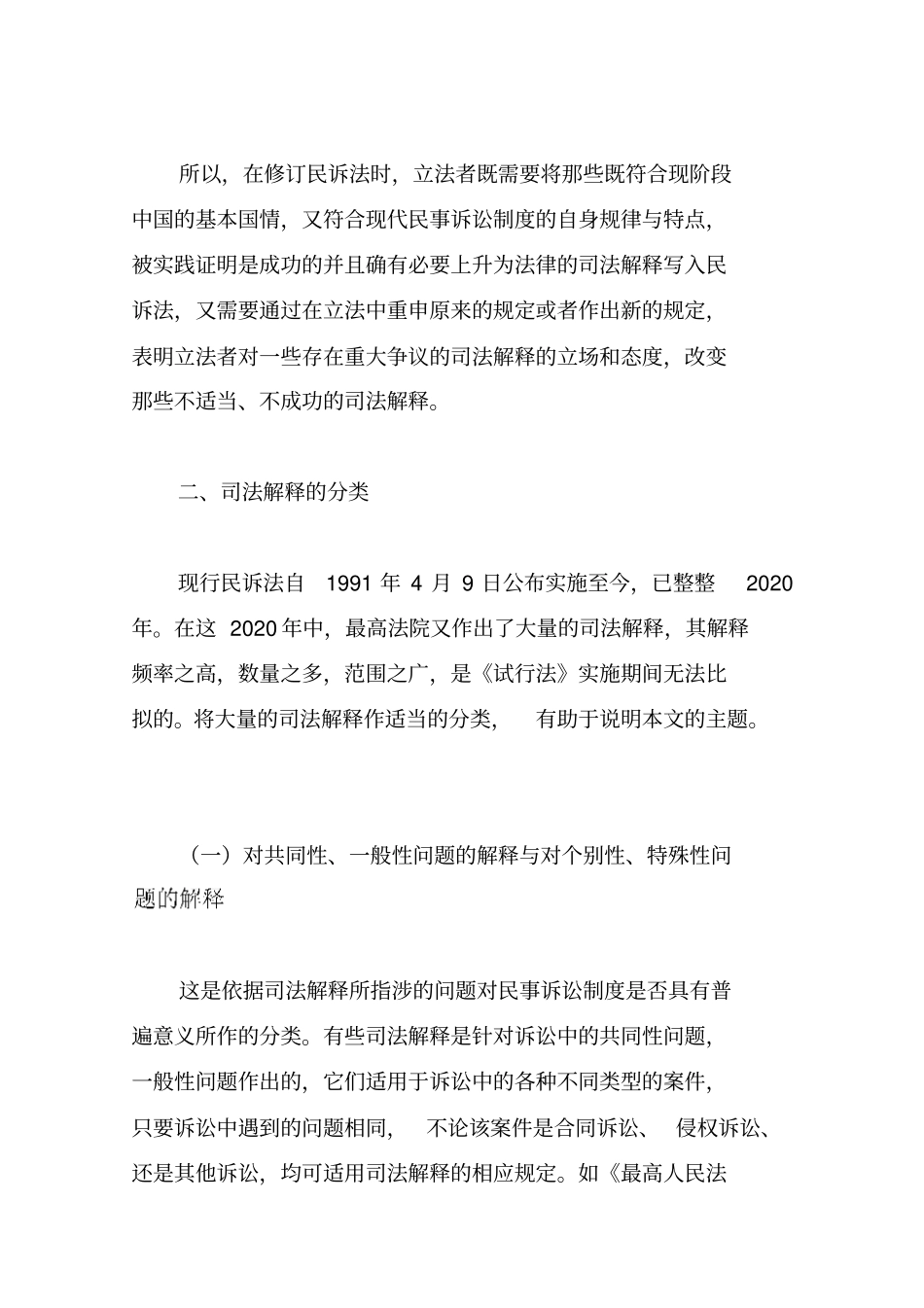司法解释与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司法解释与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司法解释与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司法解释与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一、民诉法修订与司法解释的关系尽管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司法解释包括法官处理具体案件时在裁判文书中对法律条文具体含义的阐述,但从规范意义上说,我国的司法解释特指享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所作的解释。在我国,虽然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都是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但由于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的范围相当窄,仅仅是在抗诉监督问题上同民事诉讼发生联系,最高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法所作的解释是非常之少的。几乎所有的司法解释都是由民诉法一进入审判实务,解释的必要性也就随之产生。司法解释是法律条文与诉讼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行动中的民诉法,是充满生命力的活的民诉法。民诉法是随着司法解释一起生长的,在审判实践这一肥沃土壤中,民诉法不断长出新枝嫩叶。从我国民诉法发展的历程看,无论是新中国第一部民诉法的制定,还是1991年对该法的修订,都从审判实践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以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为制定、修改法律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即将进行的对民诉法的再次修订,无疑也应当高度重视现行民诉法颁布以来最高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将审判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民诉法的修订也为立法机关审视、检讨司法解释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司法解释有不少是应对审判实务中的紧迫需要而作出的,解释者无法像立法者那样有充裕的时间从容不迫地作长时间的考量;司法解释虽然是针对法院在审理和执行民事案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的,但关涉的主体往往并不只是法院,在涉及其他主体的解释中,解释者有时也难免更多地从自身利益或自己工作便利出发;现行民诉法颁布实施以来的1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一步步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走向法治的10多年。在这一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期,我国法院为建构适应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需要的新型民事审判方式,一直持续不断地在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而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期望每一改革举措都获得成功或令人满意的效果是不现实的;[1]改革与现行法律和制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除旧布新是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反映了改革的一般规律。所以,改革者在努力进行制度创新时,总是会力图突破现有制度的束缚。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亦受上述规律的影响,依法裁判的制度要求虽然会抑制法院改革中产生的突破法律甚至改变法律的冲动,但却无法完全消除这一冲动。司法解释与法院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息息相关,许多司法解释实际上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产物,体现了改革的理念、改革的举措,它们既反映了改革的成果,也反映了改革的所以,在修订民诉法时,立法者既需要将那些既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基本国情,又符合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自身规律与特点,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并且确有必要上升为法律的司法解释写入民诉法,又需要通过在立法中重申原来的规定或者作出新的规定,表明立法者对一些存在重大争议的司法解释的立场和态度,改变那些不适当、不成功的司法解释。二、司法解释的分类现行民诉法自1991年4月9日公布实施至今,已整整2020年。在这2020年中,最高法院又作出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其解释频率之高,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试行法》实施期间无法比拟的。将大量的司法解释作适当的分类,有助于说明本文的主题。(一)对共同性、一般性问题的解释与对个别性、特殊性问这是依据司法解释所指涉的问题对民事诉讼制度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所作的分类。有些司法解释是针对诉讼中的共同性问题,一般性问题作出的,它们适用于诉讼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案件,只要诉讼中遇到的问题相同,不论该案件是合同诉讼、侵权诉讼、还是其他诉讼,均可适用司法解释的相应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民诉法意见》)第34条、第35条关于管辖权恒定的规定就是对各类民事诉讼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在司法解释中,更多的是针对个别性、特殊性问题作出的。这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种是专门针对如何审理某类案件所作的司法解释,如关于审理票据纠纷、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民事赔偿案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