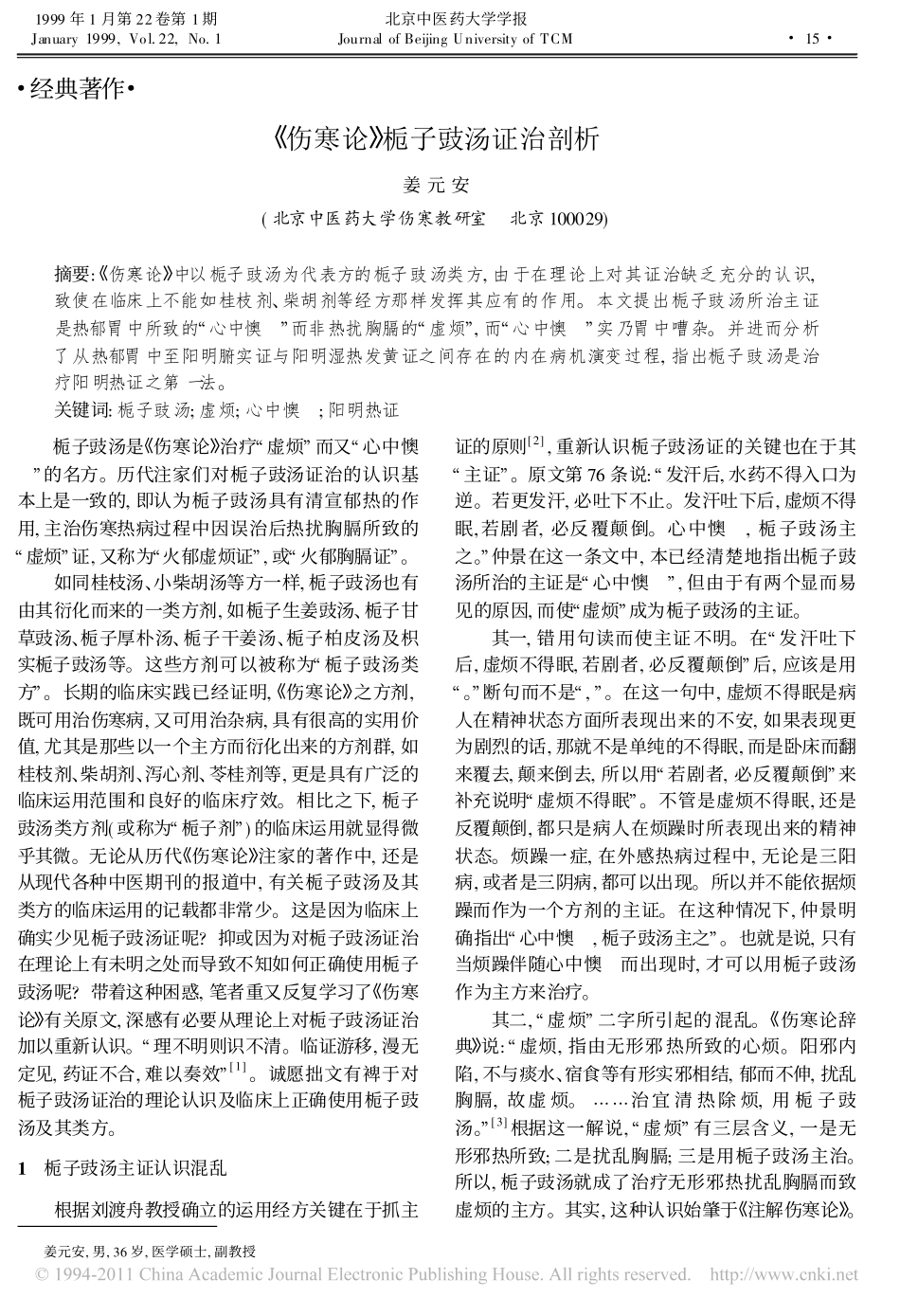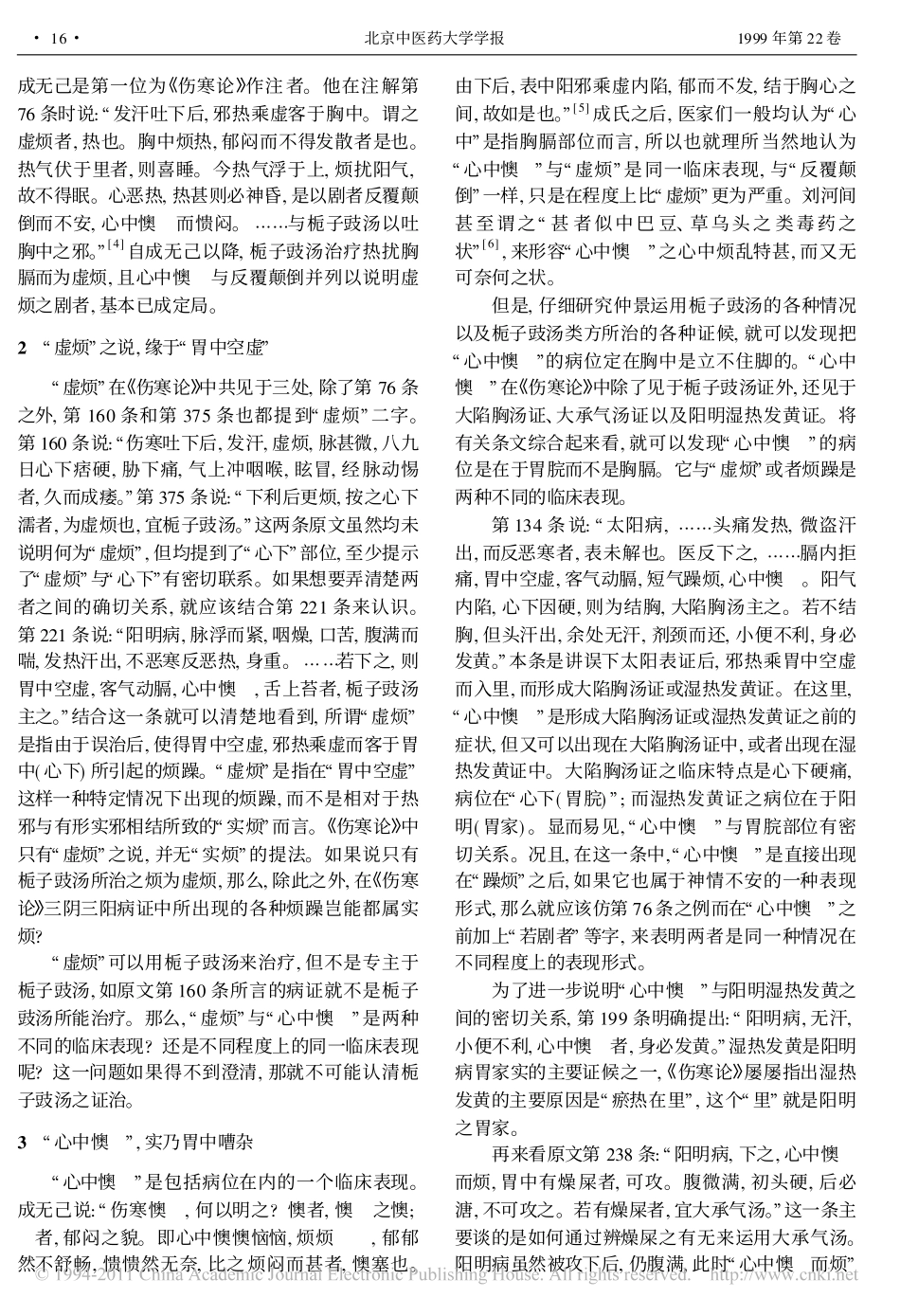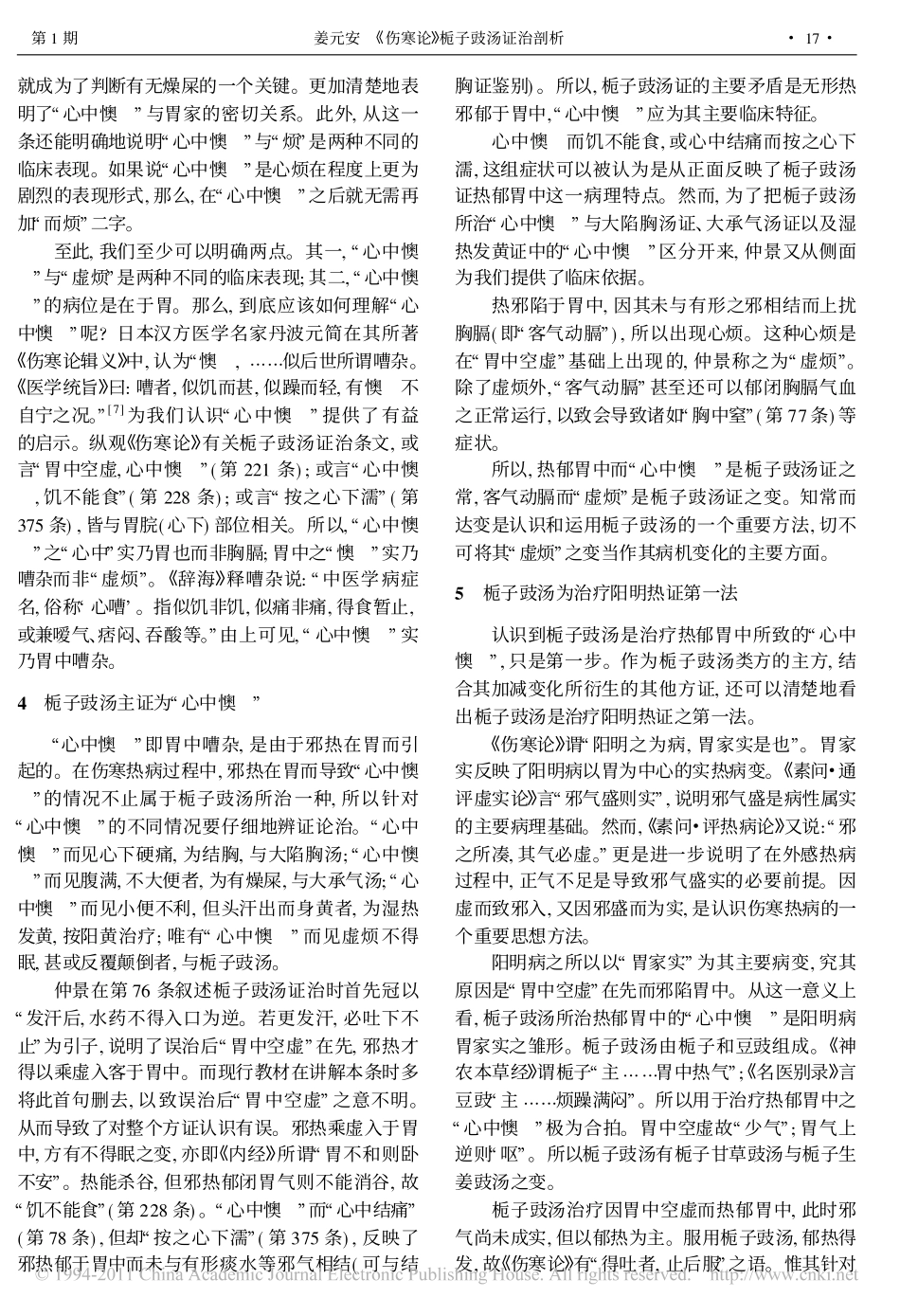姜元安,男,36岁,医学硕士,副教授�经典著作��伤寒论�栀子豉汤证治剖析姜元安(北京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北京100029)摘要:�伤寒论�中以栀子豉汤为代表方的栀子豉汤类方,由于在理论上对其证治缺乏充分的认识,致使在临床上不能如桂枝剂、柴胡剂等经方那样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提出栀子豉汤所治主证是热郁胃中所致的�心中懊�而非热扰胸膈的�虚烦�,而�心中懊�实乃胃中嘈杂。并进而分析了从热郁胃中至阳明腑实证与阳明湿热发黄证之间存在的内在病机演变过程,指出栀子豉汤是治疗阳明热证之第一法。关键词:栀子豉汤;虚烦;心中懊;阳明热证��栀子豉汤是�伤寒论�治疗�虚烦�而又�心中懊�的名方。历代注家们对栀子豉汤证治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栀子豉汤具有清宣郁热的作用,主治伤寒热病过程中因误治后热扰胸膈所致的�虚烦�证,又称为�火郁虚烦证�,或�火郁胸膈证�。如同桂枝汤、小柴胡汤等方一样,栀子豉汤也有由其衍化而来的一类方剂,如栀子生姜豉汤、栀子甘草豉汤、栀子厚朴汤、栀子干姜汤、栀子柏皮汤及枳实栀子豉汤等。这些方剂可以被称为�栀子豉汤类方�。长期的临床实践已经证明,�伤寒论�之方剂,既可用治伤寒病,又可用治杂病,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尤其是那些以一个主方而衍化出来的方剂群,如桂枝剂、柴胡剂、泻心剂、苓桂剂等,更是具有广泛的临床运用范围和良好的临床疗效。相比之下,栀子豉汤类方剂(或称为�栀子剂�)的临床运用就显得微乎其微。无论从历代�伤寒论�注家的著作中,还是从现代各种中医期刊的报道中,有关栀子豉汤及其类方的临床运用的记载都非常少。这是因为临床上确实少见栀子豉汤证呢?抑或因为对栀子豉汤证治在理论上有未明之处而导致不知如何正确使用栀子豉汤呢?带着这种困惑,笔者重又反复学习了�伤寒论�有关原文,深感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栀子豉汤证治加以重新认识。�理不明则识不清。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1]。诚愿拙文有裨于对栀子豉汤证治的理论认识及临床上正确使用栀子豉汤及其类方。1�栀子豉汤主证认识混乱根据刘渡舟教授确立的运用经方关键在于抓主证的原则[2],重新认识栀子豉汤证的关键也在于其�主证�。原文第76条说:�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栀子豉汤主之。�仲景在这一条文中,本已经清楚地指出栀子豉汤所治的主证是�心中懊�,但由于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而使�虚烦�成为栀子豉汤的主证。其一,错用句读而使主证不明。在�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后,应该是用�。�断句而不是�,�。在这一句中,虚烦不得眠是病人在精神状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安,如果表现更为剧烈的话,那就不是单纯的不得眠,而是卧床而翻来覆去,颠来倒去,所以用�若剧者,必反覆颠倒�来补充说明�虚烦不得眠�。不管是虚烦不得眠,还是反覆颠倒,都只是病人在烦躁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烦躁一症,在外感热病过程中,无论是三阳病,或者是三阴病,都可以出现。所以并不能依据烦躁而作为一个方剂的主证。在这种情况下,仲景明确指出�心中懊,栀子豉汤主之�。也就是说,只有当烦躁伴随心中懊而出现时,才可以用栀子豉汤作为主方来治疗。其二,�虚烦�二字所引起的混乱。�伤寒论辞典�说:�虚烦,指由无形邪热所致的心烦。阳邪内陷,不与痰水、宿食等有形实邪相结,郁而不伸,扰乱胸膈,故虚烦。��治宜清热除烦,用栀子豉汤。�[3]根据这一解说,�虚烦�有三层含义,一是无形邪热所致;二是扰乱胸膈;三是用栀子豉汤主治。所以,栀子豉汤就成了治疗无形邪热扰乱胸膈而致虚烦的主方。其实,这种认识始肇于�注解伤寒论�。�15�1999年1月第22卷第1期January1999,Vol.22,No.1�������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JournalofBeijingUniversityofTCM成无己是第一位为�伤寒论�作注者。他在注解第76条时说:�发汗吐下后,邪热乘虚客于胸中。谓之虚烦者,热也。胸中烦热,郁闷而不得发散者是也。热气伏于里者,则喜睡。今热气浮于上,烦扰阳气,故不得眠。心恶热,热甚则必神昏,是以剧者反覆颠倒而不安,心中懊而愦闷。��与栀子豉汤以吐胸中之邪。�[4]自成无己以降,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