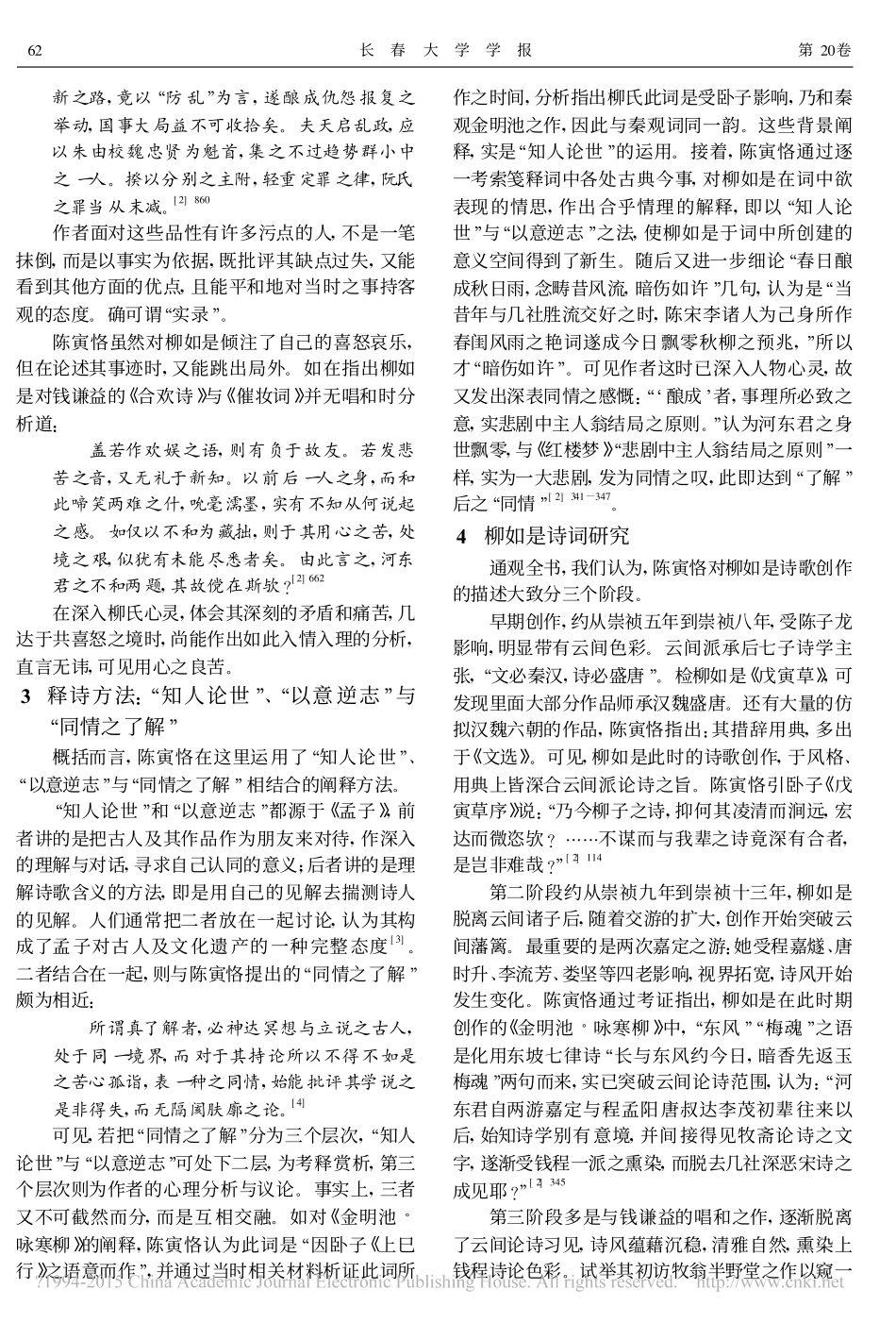第20卷第3期长春大学学报Vol.20No.32010年3月JOURNALOFCHANGCHUNUNIVERSITYMar.2010收稿日期:2009-11-08作者简介:廖雯玲(1984-),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略谈《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的文学思想廖雯玲(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摘要:从文学角度解读文史大作《柳如是别传》,认为其众体兼备,亦文亦史,深刻体现了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同时,作者既采用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传统释诗方法,又深入人物内部世界进行心理分析,研究了与柳如是相关的诗人词客,特别是对柳如是诗词创作阶段与特点的梳理分析,为后人继续开展相关工作打下了基础。关键词:《柳如是别传》;文体;实录;阐释方法;诗词研究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3907(2010)03-0061-03《柳如是别传》(以下简称《别传》)是陈寅恪先生晚年在目盲足膑的情况下,历时十年而成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对于这部文史巨著,学者们大多从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而针对其文学角度的研究一般和史学融合在一起。本文试图从文学角度对蕴含其中的陈寅恪的文学思想进行部分挖掘。1文体:亦文亦史,众体兼备据《辞海》,传记一般分为两大类,一以记述翔实的史事为主,一以史实为根据,多用形象化描写。前者更大程度地倾向史书,后者带有更多的文学色彩,《柳如是别传》则介于二者之间。一方面,《柳如是别传》具有史书价值。它以柳如是为中心,概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以及当此之际与柳如是有关的各种人的种种际遇。其中,着重叙述了柳如是与陈子龙等云间胜流的交往以及钱柳姻缘、复明运动。作者通过对人物作品的大量笺证考释来记叙,同时又搜检各种方志笔记等史料,博考慎取,因此,它较传统意义上的史传,少了故事性的叙事和描写,多了学术上的考据,相对来说更具史料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作品中充满了诗词歌赋及对它们的析赏,具有文学批评的性质。由于传主及相关人物是诗人词客,这也给作品打上了作家研究的印迹。更兼陈寅恪在释诗赏析中,又深入人物心灵,刻画了天崩地坼时代人与人、人与政治、人与文化的深刻冲突,并抒一己之叹,在兴之所致时,还以情付诗;更重要的是,作品突出展现了柳如是独立不屈的个性,出类拔萃的才情,不同于流俗的气节和勇气,读之但觉300多年前的这个历史生命是如此鲜活,让人心神飞动,这就使整部书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书,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部文学作品。此书的另一文体特点是众体兼备。刘梦溪曾称《柳如是别传》“可以说是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的文备众体的典范”[1]。陈寅恪在书后的偈语中说道:“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亦可证明,作者也并不打算把它当成一部纯史书来写,这无疑更说明了本书的文学性。2实录精神《柳如是别传》突出的表现出对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对于《史记》的“实录”精神,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概括描述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陈寅恪作为“四大史家”之一,对史学老祖宗司马迁的这种精神应有深刻的体认,写作中也时时以“实录”要求自己。一方面,整部作品建立在对诗词、方志、笔记等历史资料的笺释考证基础上。另一方面,作者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态度,无论是对其反复赞叹的柳如是,还是对史有恶评的阮大铖等,都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判断。对阮大铖,作者一方面肯定“圆海人品,史有评价”而不多论,同时又颇喜他的《咏怀堂集》,认为“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肯定其文学修养,赞誉《燕子笺》、《春灯谜》二曲为当时之绝艺[2]859。至于圆海与东林党人之间的一段恩怨,作者也以客观的眼光予以评价,云: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之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2]860作者面对这些品性有许多污点的人,不是一笔抹倒,而是以事实为依据,既批评其缺点过失,又能看到其他方面的优点,且能平和地对当时之事持客观的态度。确可谓“实录”。陈寅恪虽然对柳如是倾注了自己的喜怒哀乐,但在论述其事迹时,又能跳出局外。如在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