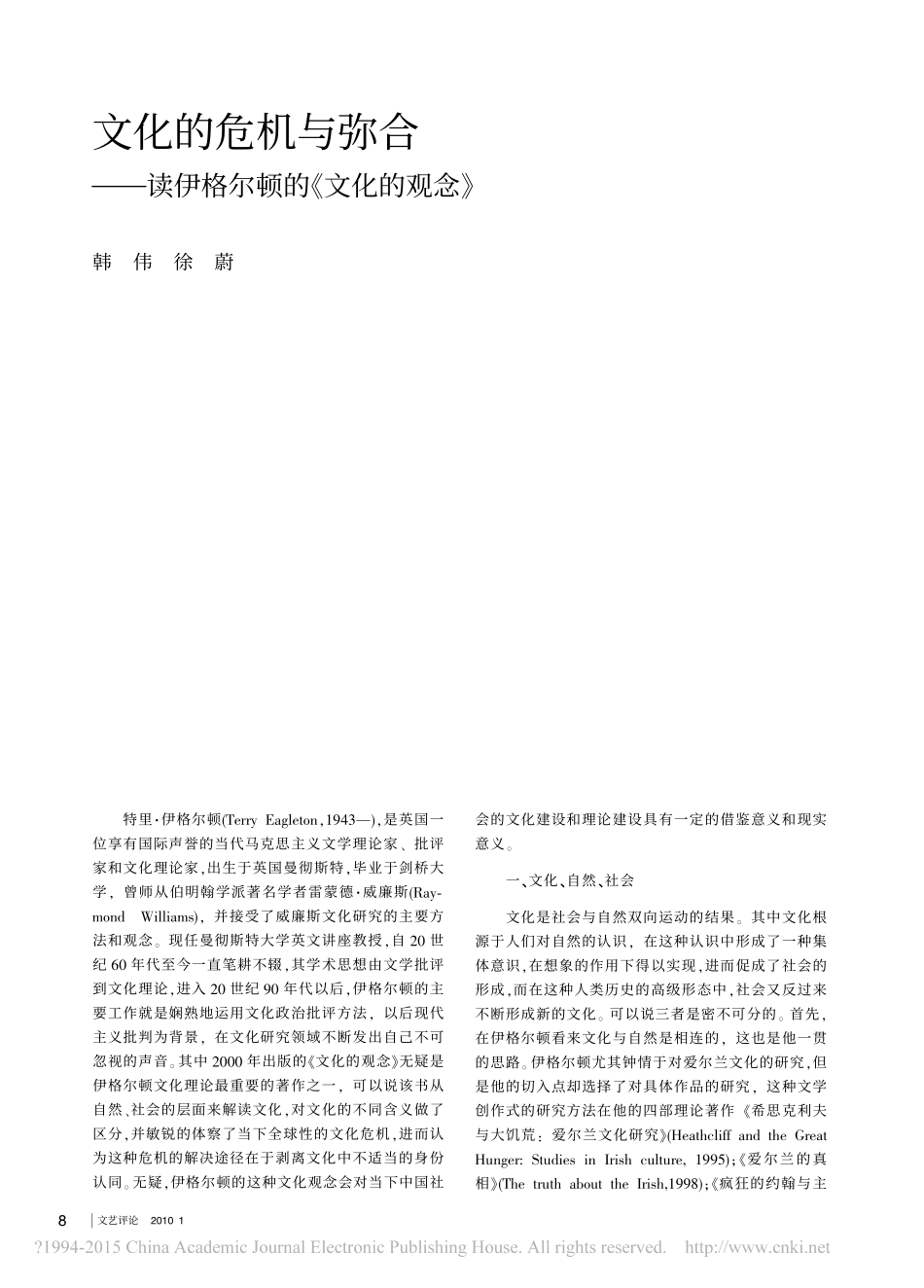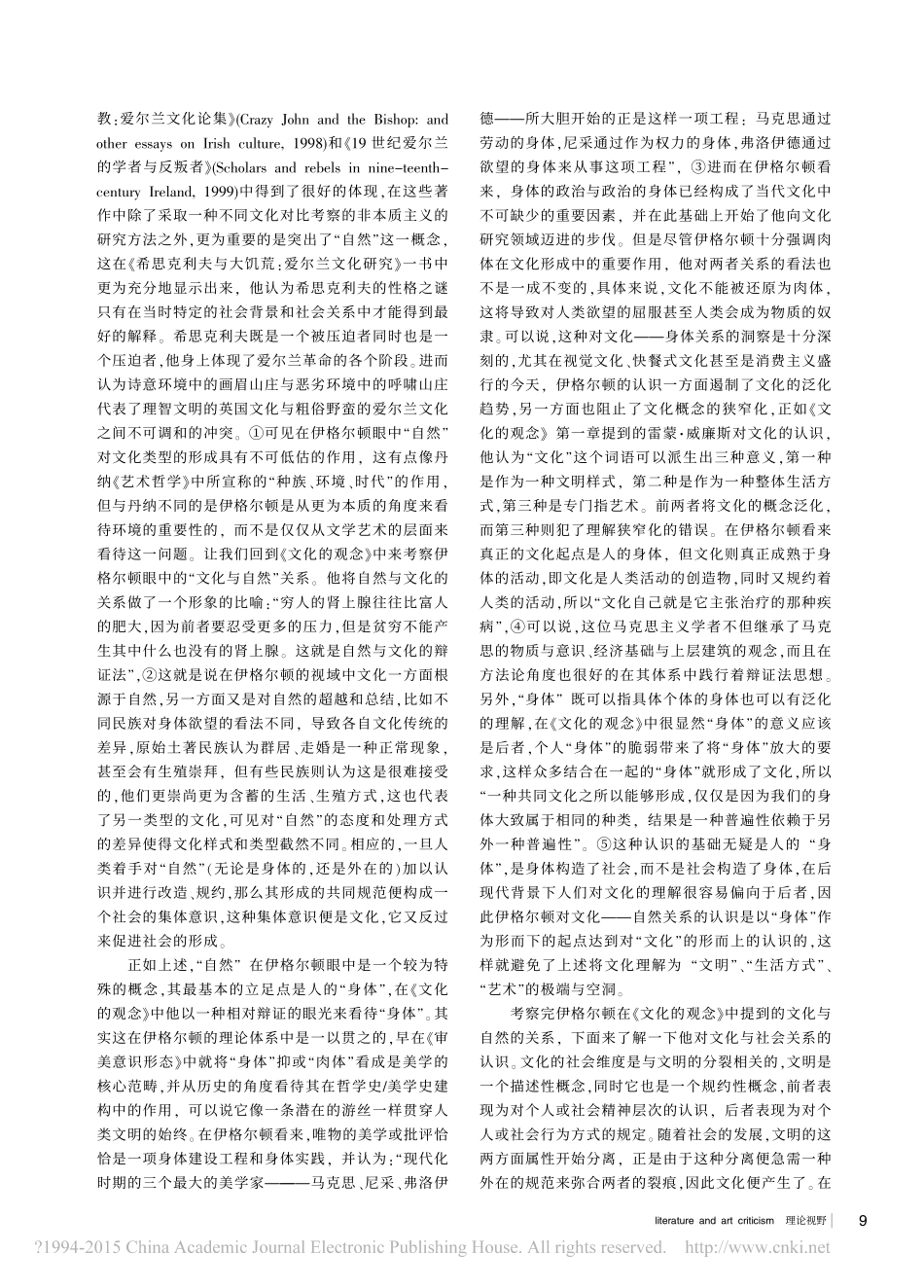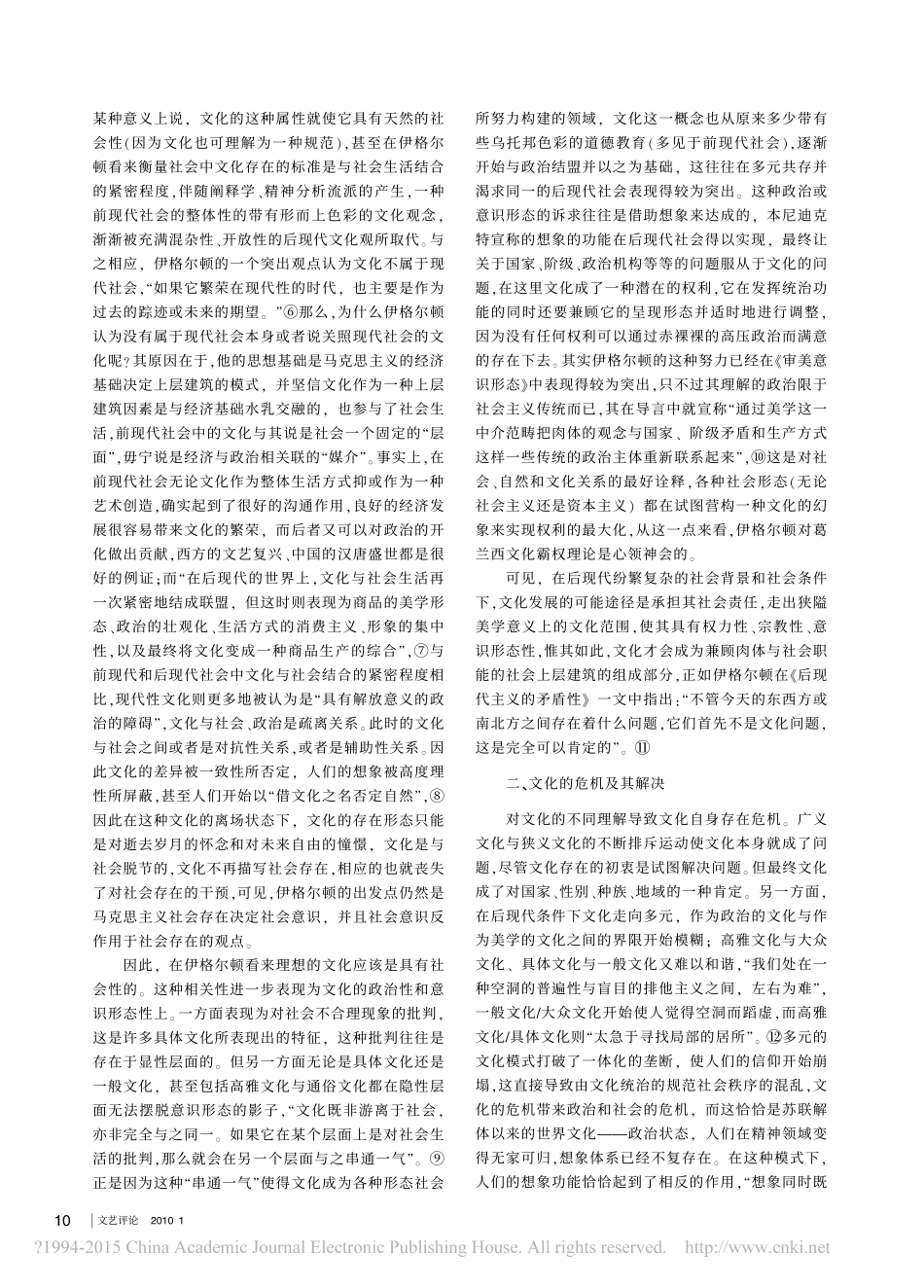文化的危机与弥合韩伟徐蔚———读伊格尔顿的《文化的观念》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是英国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毕业于剑桥大学,曾师从伯明翰学派著名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并接受了威廉斯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观念。现任曼彻斯特大学英文讲座教授,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笔耕不辍,其学术思想由文学批评到文化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的主要工作就是娴熟地运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以后现代主义批判为背景,在文化研究领域不断发出自己不可忽视的声音。其中2000年出版的《文化的观念》无疑是伊格尔顿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可以说该书从自然、社会的层面来解读文化,对文化的不同含义做了区分,并敏锐的体察了当下全球性的文化危机,进而认为这种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剥离文化中不适当的身份认同。无疑,伊格尔顿的这种文化观念会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和理论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文化、自然、社会文化是社会与自然双向运动的结果。其中文化根源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中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在想象的作用下得以实现,进而促成了社会的形成,而在这种人类历史的高级形态中,社会又反过来不断形成新的文化。可以说三者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与自然是相连的,这也是他一贯的思路。伊格尔顿尤其钟情于对爱尔兰文化的研究,但是他的切入点却选择了对具体作品的研究,这种文学创作式的研究方法在他的四部理论著作《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HeathcliffandtheGreatHunger:StudiesinIrishculture,1995);《爱尔兰的真相》(ThetruthabouttheIrish,1998);《疯狂的约翰与主8文艺评论20101教:爱尔兰文化论集》(CrazyJohnandtheBishop:andotheressaysonIrishculture,1998)和《19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Scholarsandrebelsinnine-teenth-centuryIreland,1999)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些著作中除了采取一种不同文化对比考察的非本质主义的研究方法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突出了“自然”这一概念,这在《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一书中更为充分地显示出来,他认为希思克利夫的性格之谜只有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希思克利夫既是一个被压迫者同时也是一个压迫者,他身上体现了爱尔兰革命的各个阶段。进而认为诗意环境中的画眉山庄与恶劣环境中的呼啸山庄代表了理智文明的英国文化与粗俗野蛮的爱尔兰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①可见在伊格尔顿眼中“自然”对文化类型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有点像丹纳《艺术哲学》中所宣称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作用,但与丹纳不同的是伊格尔顿是从更为本质的角度来看待环境的重要性的,而不是仅仅从文学艺术的层面来看待这一问题。让我们回到《文化的观念》中来考察伊格尔顿眼中的“文化与自然”关系。他将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穷人的肾上腺往往比富人的肥大,因为前者要忍受更多的压力,但是贫穷不能产生其中什么也没有的肾上腺。这就是自然与文化的辩证法”,②这就是说在伊格尔顿的视域中文化一方面根源于自然,另一方面又是对自然的超越和总结,比如不同民族对身体欲望的看法不同,导致各自文化传统的差异,原始土著民族认为群居、走婚是一种正常现象,甚至会有生殖崇拜,但有些民族则认为这是很难接受的,他们更崇尚更为含蓄的生活、生殖方式,这也代表了另一类型的文化,可见对“自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的差异使得文化样式和类型截然不同。相应的,一旦人类着手对“自然”(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外在的)加以认识并进行改造、规约,那么其形成的共同规范便构成一个社会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便是文化,它又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形成。正如上述,“自然”在伊格尔顿眼中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概念,其最基本的立足点是人的“身体”,在《文化的观念》中他以一种相对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身体”。其实这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以贯之的,早在《审美意识形态》中就将“身体”抑或“肉体”看成是美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