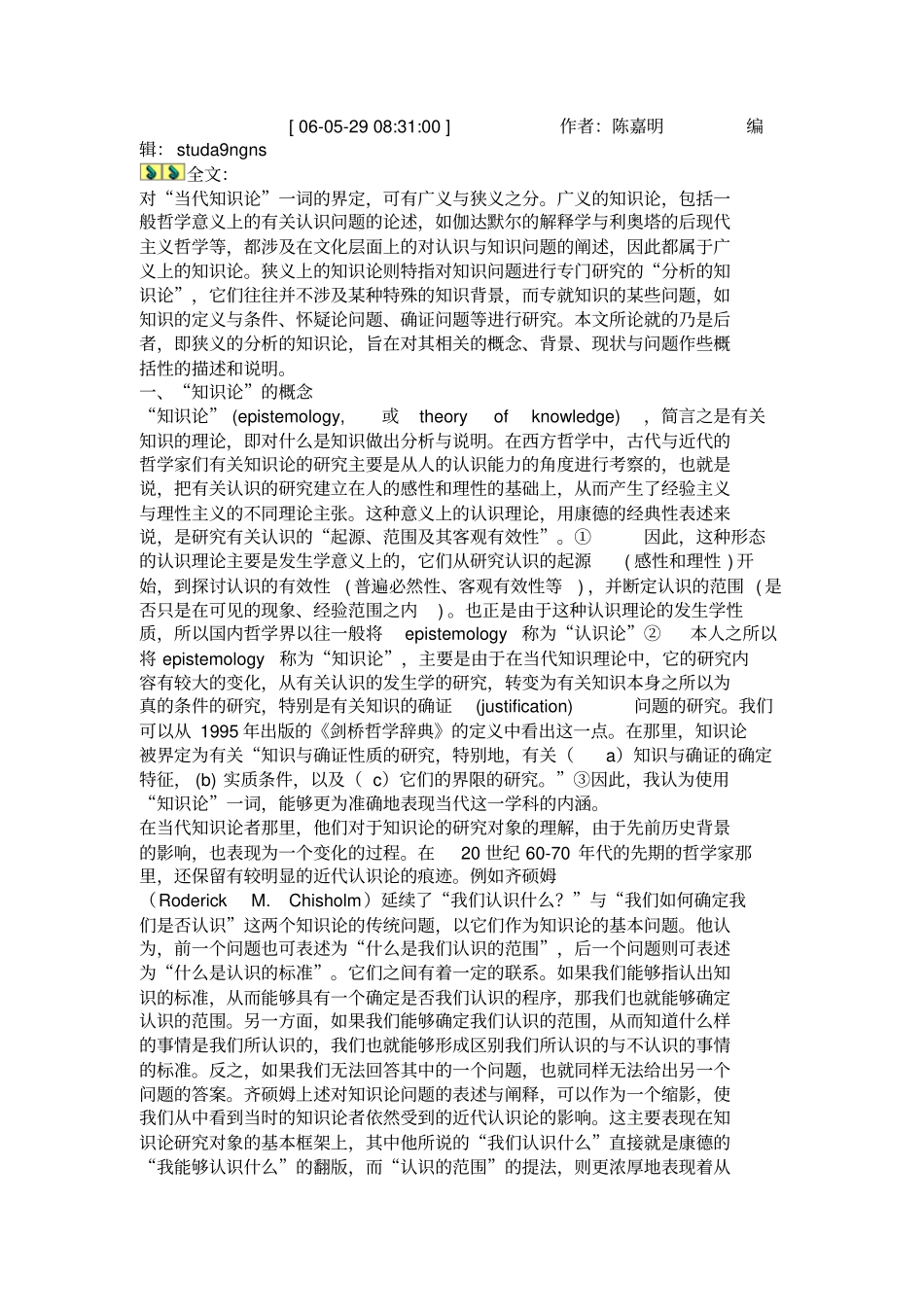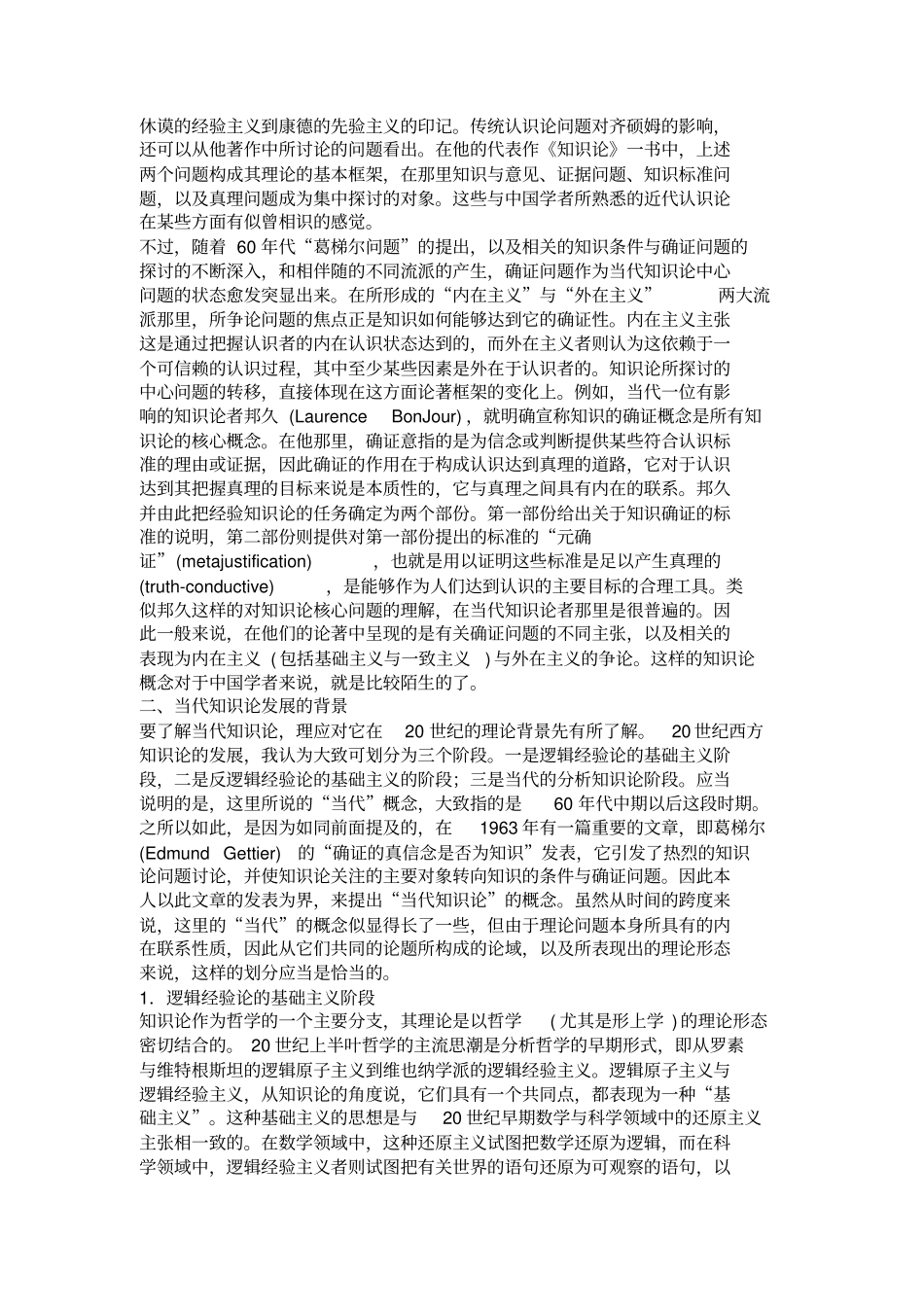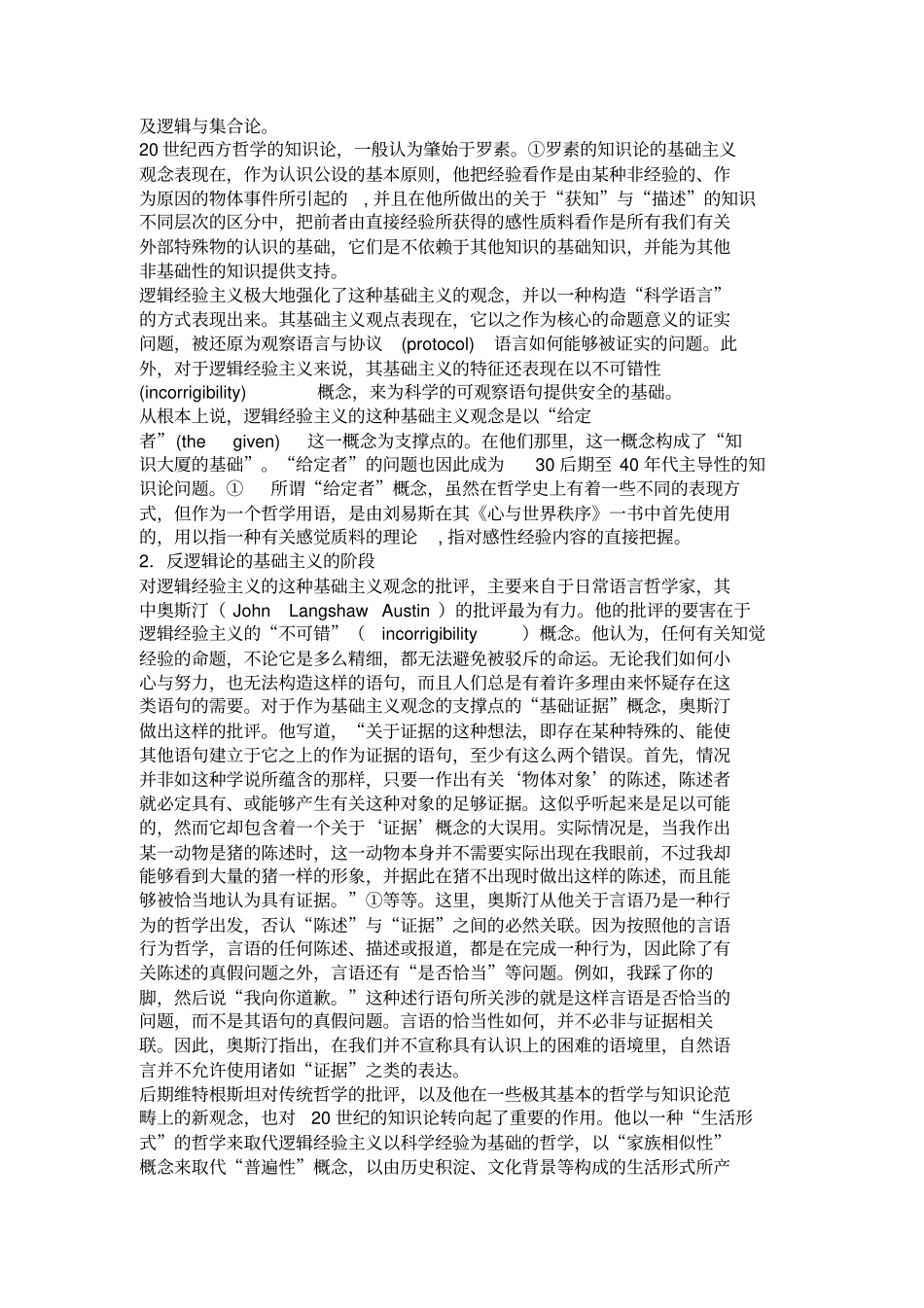[06-05-2908:31:00]作者:陈嘉明编辑:studa9ngns全文:对“当代知识论”一词的界定,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论,包括一般哲学意义上的有关认识问题的论述,如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等,都涉及在文化层面上的对认识与知识问题的阐述,因此都属于广义上的知识论。狭义上的知识论则特指对知识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分析的知识论”,它们往往并不涉及某种特殊的知识背景,而专就知识的某些问题,如知识的定义与条件、怀疑论问题、确证问题等进行研究。本文所论就的乃是后者,即狭义的分析的知识论,旨在对其相关的概念、背景、现状与问题作些概括性的描述和说明。一、“知识论”的概念“知识论”(epistemology,或theoryofknowledge),简言之是有关知识的理论,即对什么是知识做出分析与说明。在西方哲学中,古代与近代的哲学家们有关知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人的认识能力的角度进行考察的,也就是说,把有关认识的研究建立在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基础上,从而产生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不同理论主张。这种意义上的认识理论,用康德的经典性表述来说,是研究有关认识的“起源、范围及其客观有效性”。①因此,这种形态的认识理论主要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它们从研究认识的起源(感性和理性)开始,到探讨认识的有效性(普遍必然性、客观有效性等),并断定认识的范围(是否只是在可见的现象、经验范围之内)。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理论的发生学性质,所以国内哲学界以往一般将epistemology称为“认识论”②本人之所以将epistemology称为“知识论”,主要是由于在当代知识理论中,它的研究内容有较大的变化,从有关认识的发生学的研究,转变为有关知识本身之所以为真的条件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知识的确证(justification)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从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辞典》的定义中看出这一点。在那里,知识论被界定为有关“知识与确证性质的研究,特别地,有关(a)知识与确证的确定特征,(b)实质条件,以及(c)它们的界限的研究。”③因此,我认为使用“知识论”一词,能够更为准确地表现当代这一学科的内涵。在当代知识论者那里,他们对于知识论的研究对象的理解,由于先前历史背景的影响,也表现为一个变化的过程。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先期的哲学家那里,还保留有较明显的近代认识论的痕迹。例如齐硕姆(RoderickM.Chisholm)延续了“我们认识什么?”与“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否认识”这两个知识论的传统问题,以它们作为知识论的基本问题。他认为,前一个问题也可表述为“什么是我们认识的范围”,后一个问题则可表述为“什么是认识的标准”。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够指认出知识的标准,从而能够具有一个确定是否我们认识的程序,那我们也就能够确定认识的范围。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我们认识的范围,从而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所认识的,我们也就能够形成区别我们所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事情的标准。反之,如果我们无法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也就同样无法给出另一个问题的答案。齐硕姆上述对知识论问题的表述与阐释,可以作为一个缩影,使我们从中看到当时的知识论者依然受到的近代认识论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知识论研究对象的基本框架上,其中他所说的“我们认识什么”直接就是康德的“我能够认识什么”的翻版,而“认识的范围”的提法,则更浓厚地表现着从休谟的经验主义到康德的先验主义的印记。传统认识论问题对齐硕姆的影响,还可以从他著作中所讨论的问题看出。在他的代表作《知识论》一书中,上述两个问题构成其理论的基本框架,在那里知识与意见、证据问题、知识标准问题,以及真理问题成为集中探讨的对象。这些与中国学者所熟悉的近代认识论在某些方面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随着60年代“葛梯尔问题”的提出,以及相关的知识条件与确证问题的探讨的不断深入,和相伴随的不同流派的产生,确证问题作为当代知识论中心问题的状态愈发突显出来。在所形成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两大流派那里,所争论问题的焦点正是知识如何能够达到它的确证性。内在主义主张这是通过把握认识者的内在认识状态达到的,而外在主义者则认为这依赖于一个可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