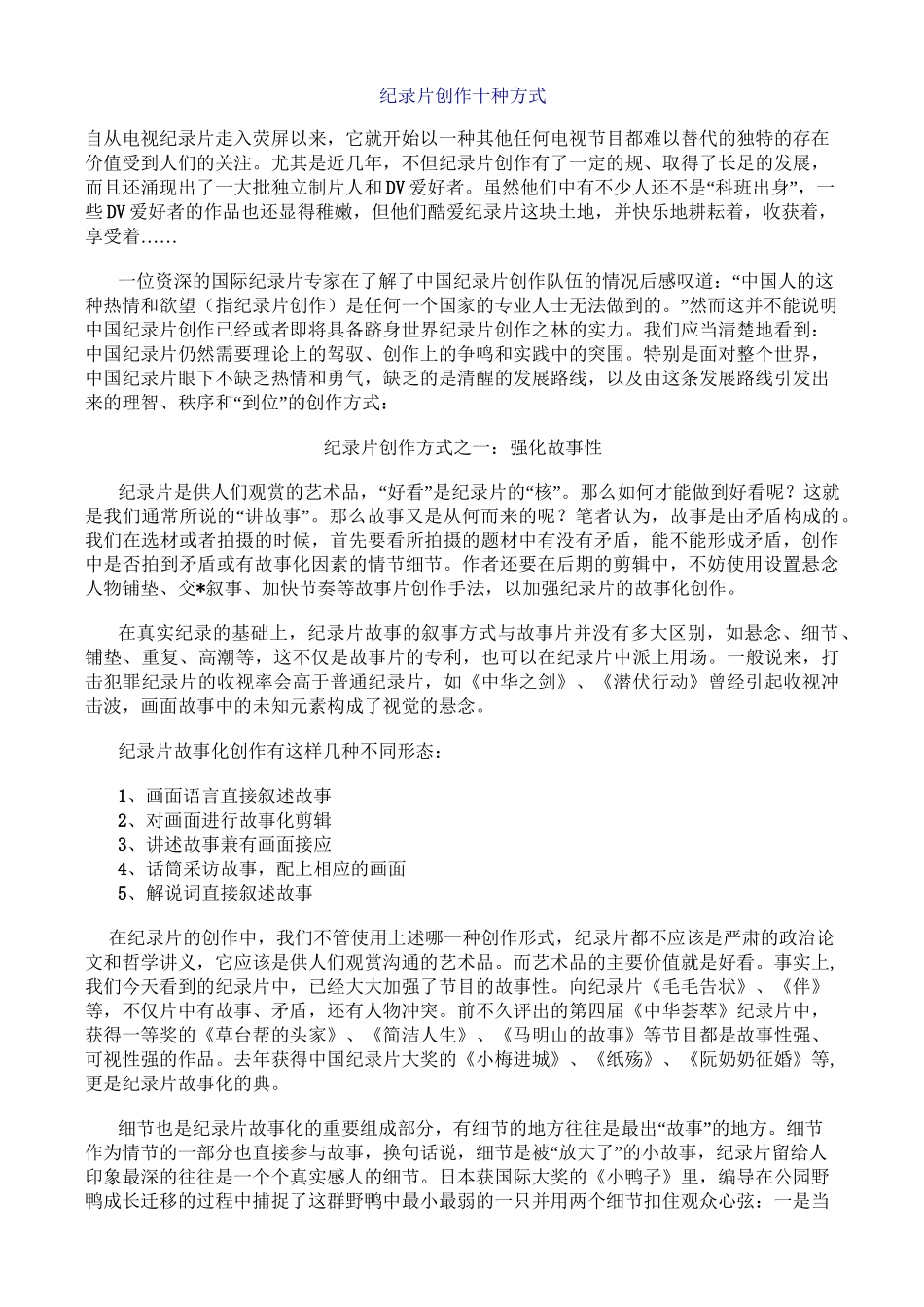纪录片创作十种方式自从电视纪录片走入荧屏以来,它就开始以一种其他任何电视节目都难以替代的独特的存在价值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近几年,不但纪录片创作有了一定的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独立制片人和DV爱好者。虽然他们中有不少人还不是“科班出身”,一些DV爱好者的作品也还显得稚嫩,但他们酷爱纪录片这块土地,并快乐地耕耘着,收获着,享受着……一位资深的国际纪录片专家在了解了中国纪录片创作队伍的情况后感叹道:“中国人的这种热情和欲望(指纪录片创作)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专业人士无法做到的。”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纪录片创作已经或者即将具备跻身世界纪录片创作之林的实力。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中国纪录片仍然需要理论上的驾驭、创作上的争鸣和实践中的突围。特别是面对整个世界,中国纪录片眼下不缺乏热情和勇气,缺乏的是清醒的发展路线,以及由这条发展路线引发出来的理智、秩序和“到位”的创作方式:纪录片创作方式之一:强化故事性纪录片是供人们观赏的艺术品,“好看”是纪录片的“核”。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好看呢?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讲故事”。那么故事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笔者认为,故事是由矛盾构成的。我们在选材或者拍摄的时候,首先要看所拍摄的题材中有没有矛盾,能不能形成矛盾,创作中是否拍到矛盾或有故事化因素的情节细节。作者还要在后期的剪辑中,不妨使用设置悬念人物铺垫、交*叙事、加快节奏等故事片创作手法,以加强纪录片的故事化创作。在真实纪录的基础上,纪录片故事的叙事方式与故事片并没有多大区别,如悬念、细节、铺垫、重复、高潮等,这不仅是故事片的专利,也可以在纪录片中派上用场。一般说来,打击犯罪纪录片的收视率会高于普通纪录片,如《中华之剑》、《潜伏行动》曾经引起收视冲击波,画面故事中的未知元素构成了视觉的悬念。纪录片故事化创作有这样几种不同形态:1、画面语言直接叙述故事2、对画面进行故事化剪辑3、讲述故事兼有画面接应4、话筒采访故事,配上相应的画面5、解说词直接叙述故事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我们不管使用上述哪一种创作形式,纪录片都不应该是严肃的政治论文和哲学讲义,它应该是供人们观赏沟通的艺术品。而艺术品的主要价值就是好看。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纪录片中,已经大大加强了节目的故事性。向纪录片《毛毛告状》、《伴》等,不仅片中有故事、矛盾,还有人物冲突。前不久评出的第四届《中华荟萃》纪录片中,获得一等奖的《草台帮的头家》、《简洁人生》、《马明山的故事》等节目都是故事性强、可视性强的作品。去年获得中国纪录片大奖的《小梅进城》、《纸殇》、《阮奶奶征婚》等,更是纪录片故事化的典。细节也是纪录片故事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细节的地方往往是最出“故事”的地方。细节作为情节的一部分也直接参与故事,换句话说,细节是被“放大了”的小故事,纪录片留给人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细节。日本获国际大奖的《小鸭子》里,编导在公园野鸭成长迁移的过程中捕捉了这群野鸭中最小最弱的一只并用两个细节扣住观众心弦:一是当鸭群纷纷离开池塘,只剩最后一只最小的不能飞,它几次想条跳过最后一个石阶,却一次一次总是失败,它并不灰心,再跳,再跳……直至跳了十几次,才成功。这个细节在展示过程中,观众绷紧了神经,心也随着小鸭子的起跳而跳动。第二个细节是当鸭群长大,欲离开皇家公园时,所有的小鸭均挥舞着翅膀直冲云霄,惟独那只最小的鸭子试飞了一次又一次,毫不气馁的小鸭直至第八次才稳稳地升空与伙伴们会合。这一细节是鸭子故事的终结,也给了观众巨大的心灵冲击与感情洗礼。然而今天,有些创作者一谈起纪录片的故事化,就害怕把自己的纪录片说成是故事片。实际上,我们把纪录片拍的象故事片那么好看不是更好吗!纪录片与故事片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故事性,而是故事本身的“虚构还是非虚构”。如果因为保持与故事片的距离而丢弃故事性,无疑是为了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了。纪录片创作方式之二:追求戏剧化没有冲突也就无所谓戏剧化,纪录片中的故事也尽量要有戏剧化冲突。但与故事片中的冲突是不一样的。纪录片更关注的是人与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