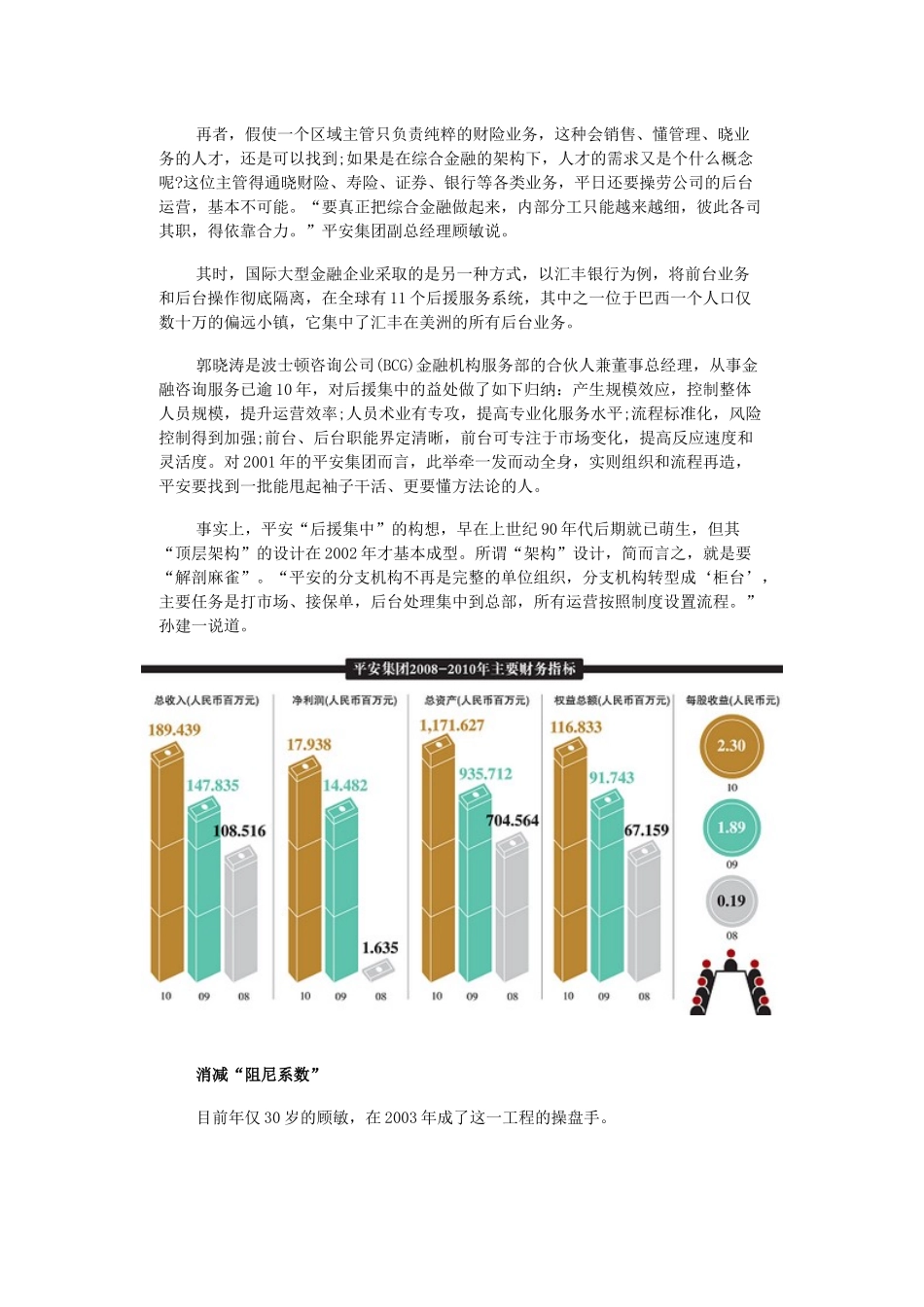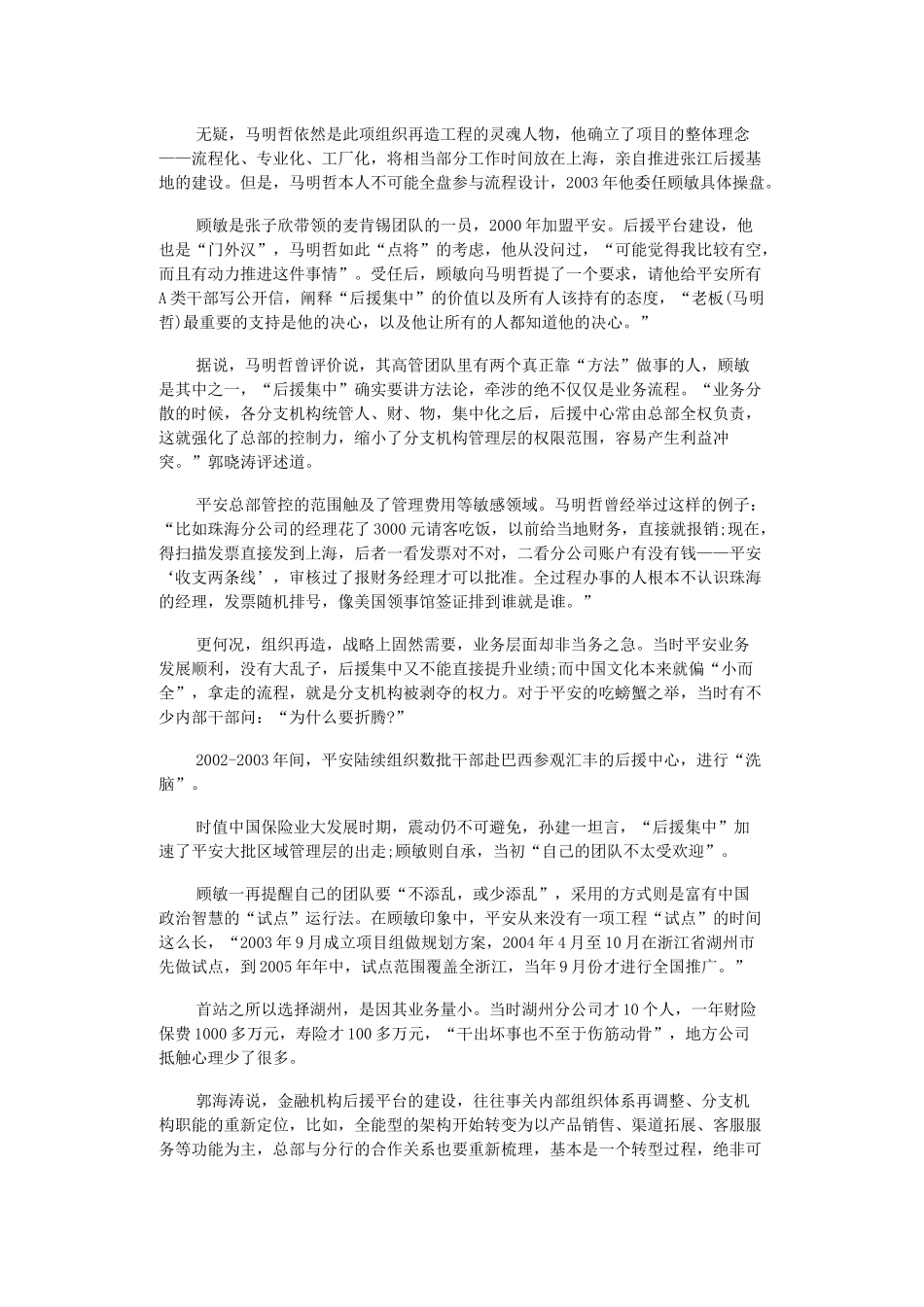在中国内地某小镇,你购买了一份中国平安的保险产品,那么,流程可能是这样的:柜台服务人员会将你的资料扫描进电脑,资料被迅速传输到位于上海张江的后援平台,在那里,文档作业部会对你的信息录入、保全;只要信息完备,资料会送去质量控制流程,保单流转到核保作业部,负责风险审核的专业人员会分析你的风险状况,出具核保意见;一旦核保部门同意,其后,会计作业部门将会登场,负责资金交割、承保事宜……全过程分工协作,实现流水线作业。平安集团就只销售一份保险给你吗?很可能不会,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它可以推测你潜在的理财需求推送其他产品,比如由其控股的深圳发展银行的某款理财类或者小额贷款产品……这是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 CEO 马明哲对于“综合金融”的一个基本构想:打造一个强大的后台系统,提供综合理财服务,提高单位客户购买率,解决各项业务融合的难题。如今,现实离梦想正越来越近。解剖麻雀后援中心平台是马明哲庞大构思的支点。2001 年 12 月,中国正式加入 WTO,平安集团管理层和中国许多企业一样,要思考如何“与狼共舞”。“当时,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金融企业如何应对国际金融集团多元化的经营优势,以低成本、高效率、高品质的服务抵御这股冲击。”平安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孙建一说。外在竞争环境与内在变革需求,推动了中国平安后援集中的进程。当时,多数金融企业采取分散的运营作业模式——分支机构各自建有独立运营的后台。以平安为例,分支机构遍布全国 300 多个城市,全部是“五脏俱全”的“麻雀”,职能涵盖从保单销售到核保、理赔等整个业务链条,自主权力大。随着业务做大,机构层级增加,管理制度执行的“折扣率”同样在放大。孙建一不讳言,当时平安流程上漏洞不少,“比如,我在保险公司,跟你很熟,你的车或者企业本来没有上保险,出事了来跟我商量,我偷偷给你补一个保单再给你赔付,这种事情在基层机构时有发生”。长此以往,平安不可承受“制度漏损”之重。“诸侯自治”式的管控架构,在服务标准、运营效率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运营和服务标准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内部流传的一个经典段子是,同样“被狗咬伤”,全国范围平安理赔规则有数十种,赔偿额度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投保人在哪里被狗咬。各地区专业技能与资源无法有效共享,各地业务量有波动,理赔核保人员无从调剂余缺;服务和纯后台功能混杂,分支机构领导层忙于应付各类事务,对客户服务关注不足。管控模式的变革,绝不仅仅关系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