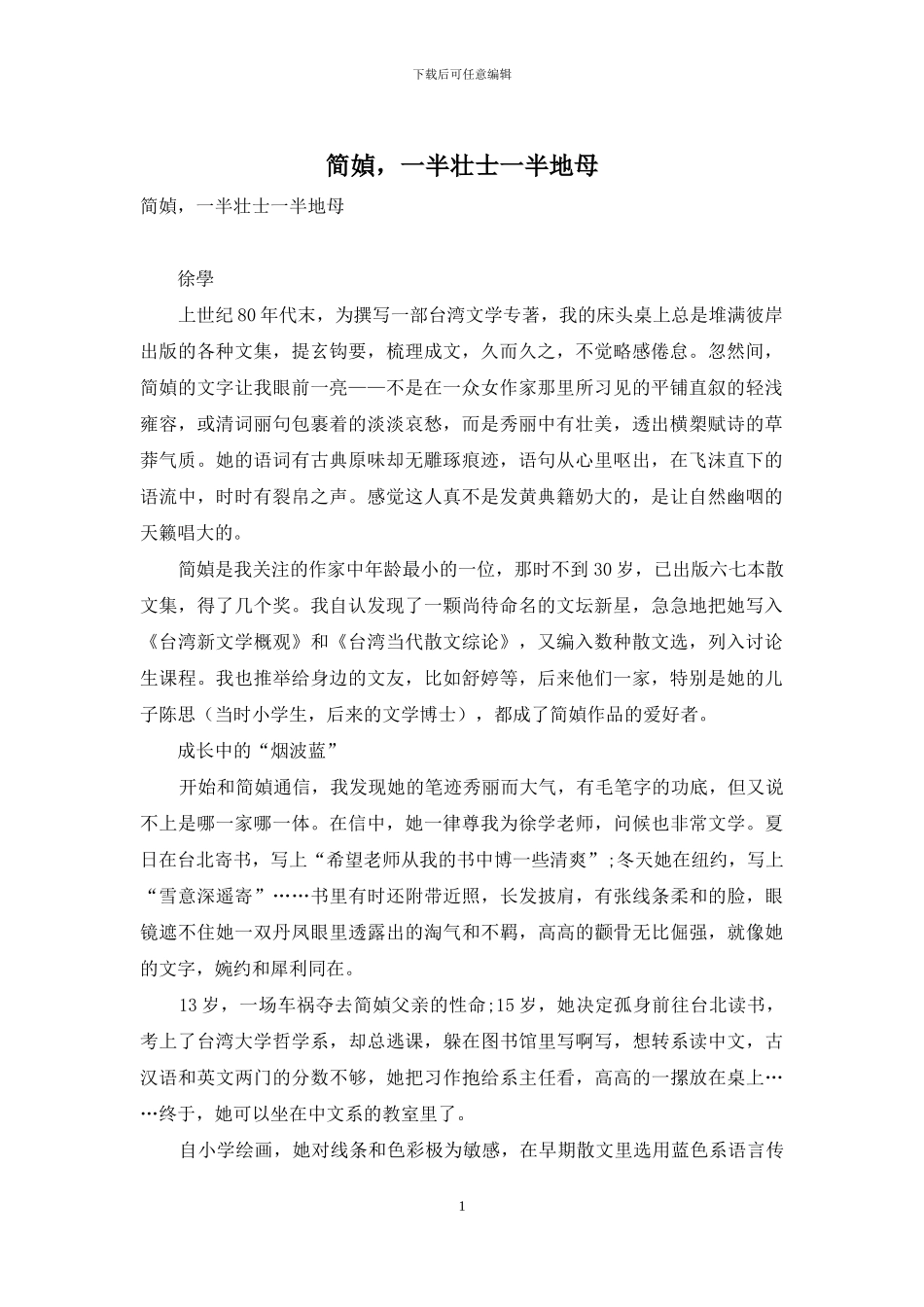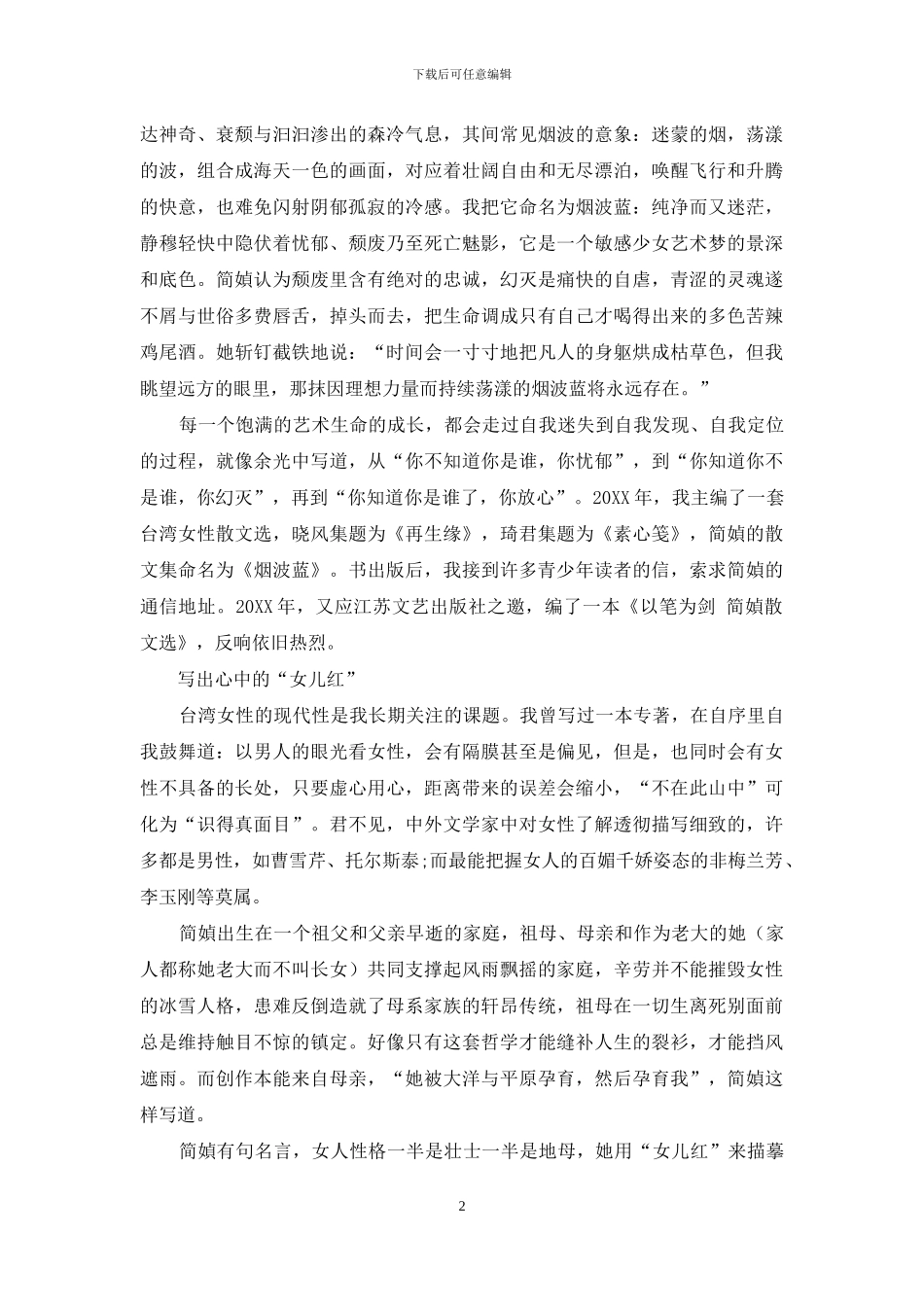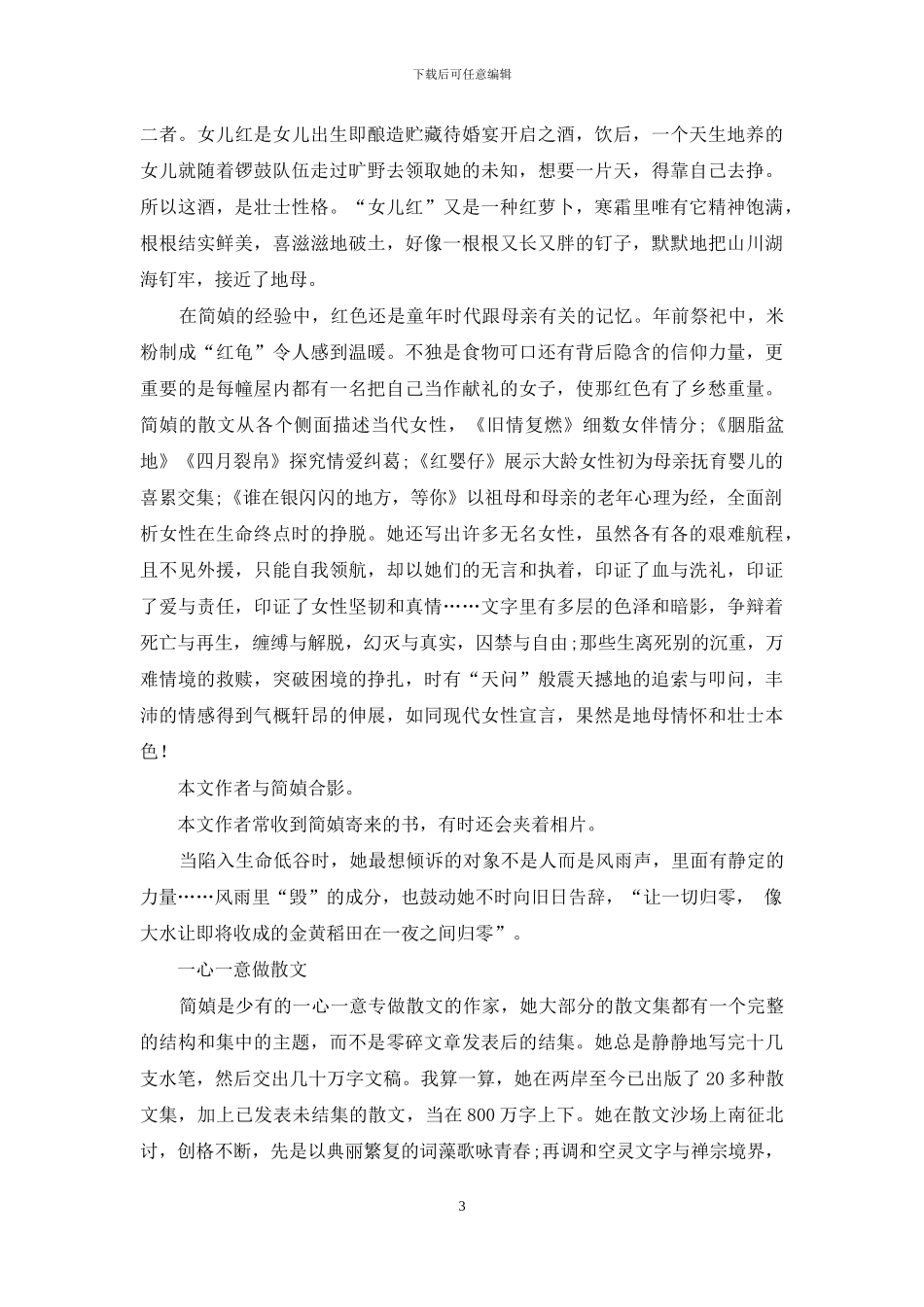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简媜,一半壮士一半地母简媜,一半壮士一半地母 徐學 上世纪 80 年代末,为撰写一部台湾文学专著,我的床头桌上总是堆满彼岸出版的各种文集,提玄钩要,梳理成文,久而久之,不觉略感倦怠。忽然间,简媜的文字让我眼前一亮——不是在一众女作家那里所习见的平铺直叙的轻浅雍容,或清词丽句包裹着的淡淡哀愁,而是秀丽中有壮美,透出横槊赋诗的草莽气质。她的语词有古典原味却无雕琢痕迹,语句从心里呕出,在飞沫直下的语流中,时时有裂帛之声。感觉这人真不是发黄典籍奶大的,是让自然幽咽的天籁唱大的。 简媜是我关注的作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那时不到 30 岁,已出版六七本散文集,得了几个奖。我自认发现了一颗尚待命名的文坛新星,急急地把她写入《台湾新文学概观》和《台湾当代散文综论》,又编入数种散文选,列入讨论生课程。我也推举给身边的文友,比如舒婷等,后来他们一家,特别是她的儿子陈思(当时小学生,后来的文学博士),都成了简媜作品的爱好者。 成长中的“烟波蓝” 开始和简媜通信,我发现她的笔迹秀丽而大气,有毛笔字的功底,但又说不上是哪一家哪一体。在信中,她一律尊我为徐学老师,问候也非常文学。夏日在台北寄书,写上“希望老师从我的书中博一些清爽”;冬天她在纽约,写上“雪意深遥寄”……书里有时还附带近照,长发披肩,有张线条柔和的脸,眼镜遮不住她一双丹凤眼里透露出的淘气和不羁,高高的颧骨无比倔强,就像她的文字,婉约和犀利同在。 13 岁,一场车祸夺去简媜父亲的性命;15 岁,她决定孤身前往台北读书,考上了台湾大学哲学系,却总逃课,躲在图书馆里写啊写,想转系读中文,古汉语和英文两门的分数不够,她把习作抱给系主任看,高高的一摞放在桌上……终于,她可以坐在中文系的教室里了。 自小学绘画,她对线条和色彩极为敏感,在早期散文里选用蓝色系语言传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达神奇、衰颓与汩汩渗出的森冷气息,其间常见烟波的意象:迷蒙的烟,荡漾的波,组合成海天一色的画面,对应着壮阔自由和无尽漂泊,唤醒飞行和升腾的快意,也难免闪射阴郁孤寂的冷感。我把它命名为烟波蓝:纯净而又迷茫,静穆轻快中隐伏着忧郁、颓废乃至死亡魅影,它是一个敏感少女艺术梦的景深和底色。简媜认为颓废里含有绝对的忠诚,幻灭是痛快的自虐,青涩的灵魂遂不屑与世俗多费唇舌,掉头而去,把生命调成只有自己才喝得出来的多色苦辣鸡尾酒。她斩钉截铁地说:“时间会一寸寸地把凡人的身躯烘成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