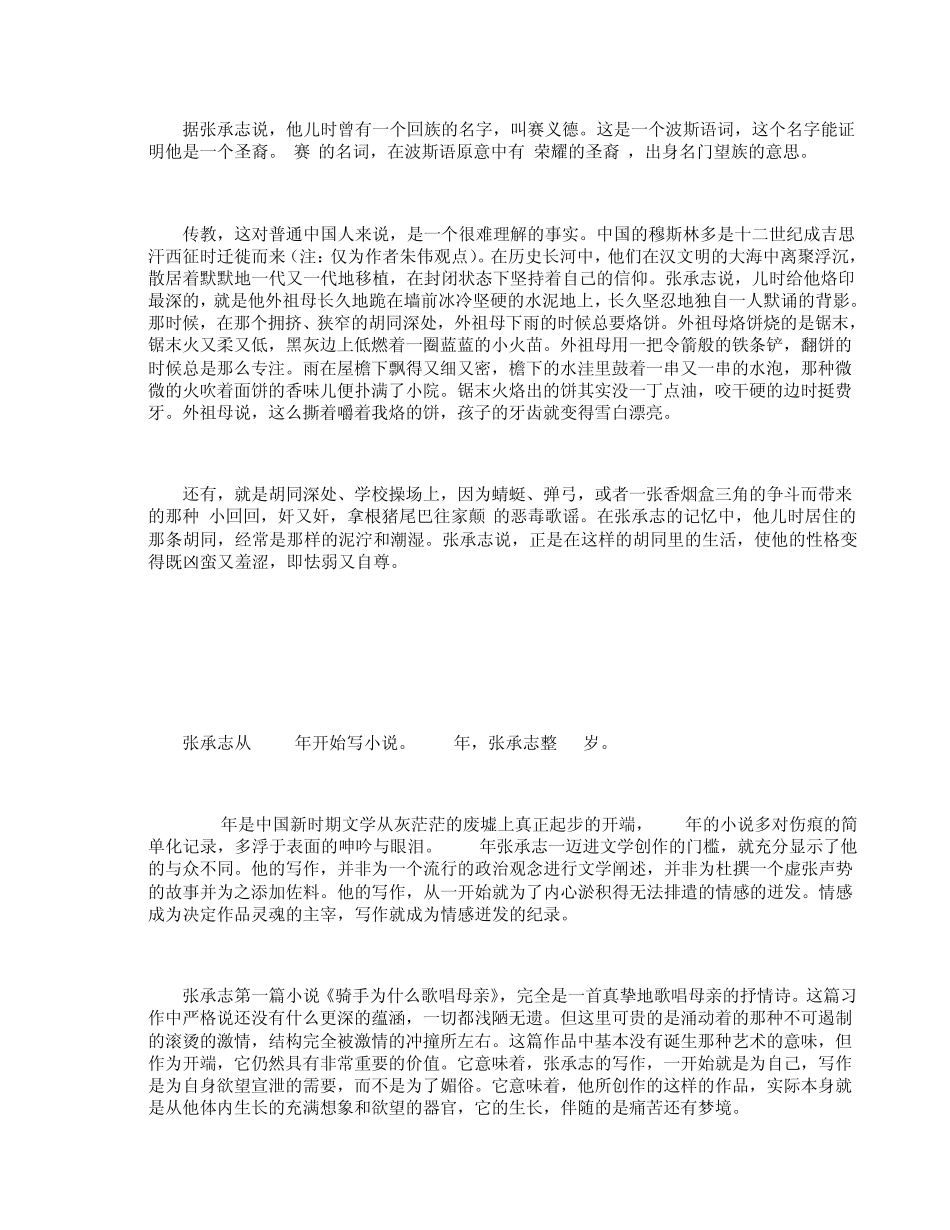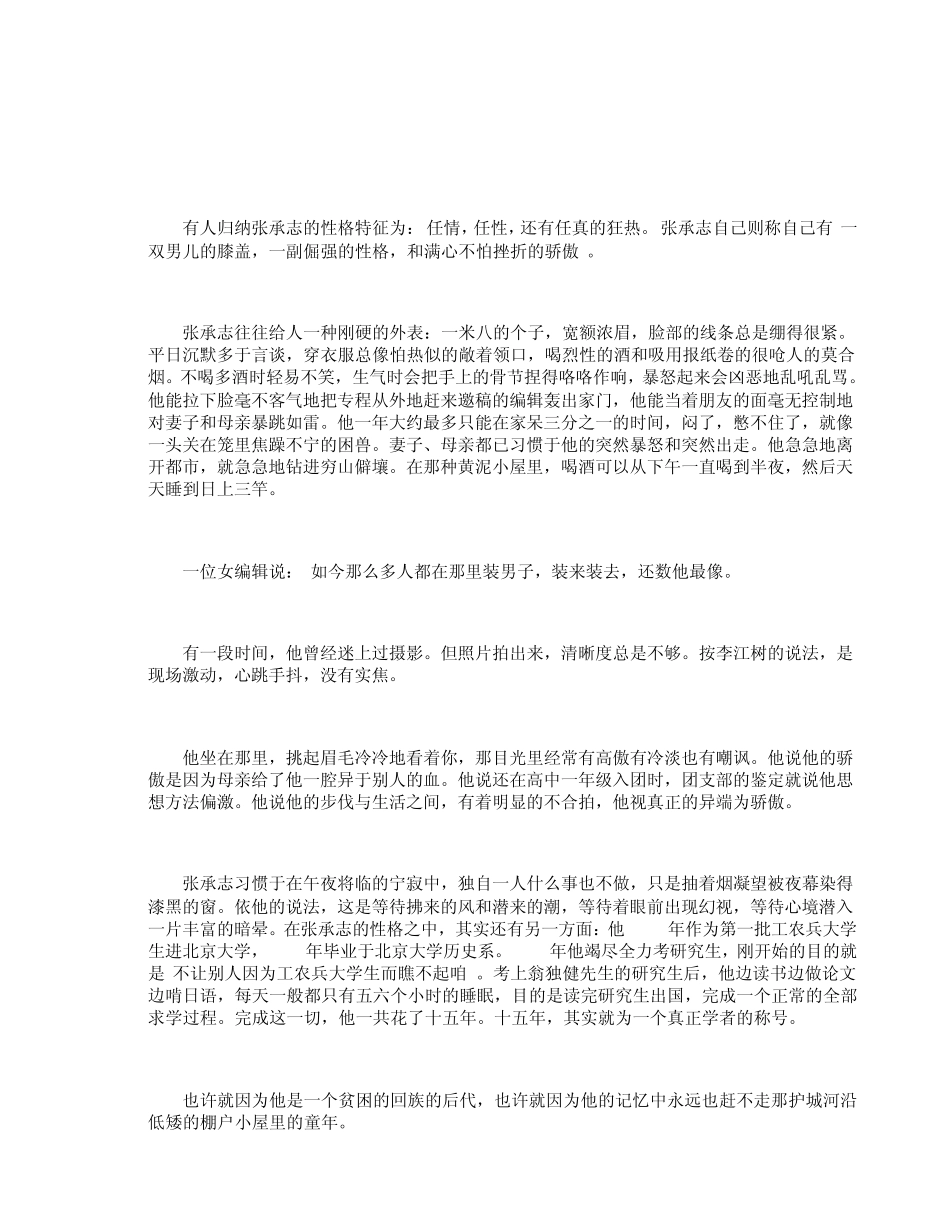张承志记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中,张承志无疑极鲜明地扮演了属于自己的角色。在十多年的潮涨潮落中,他是少数始终坚持自己鲜明个性的小说家之一。个性,意味着他的作品完全是他赤裸裸情感的燃烧;意味着他的语言,完全是他对自己理想的赤诚膜拜;意味着他的艺术,完全是对自身及真实处境的真挚内省。当然,也意味着极端的偏激。在张承志与他的作品之间,没有一个叙述者。读张承志的小说,令人想起很稠很稠,半凝固的,鼓着暗红色气泡,一堆一堆向前涌动的岩浆;想起夏日裹挟着泥沙,焦躁地反复鼓荡着漩涡的浑浊的河水。没有一泻千里的奔腾,只有沉重的郁结的涌动。张承志小说的基调,是一种介于暗黄与酱红之间的颜色。没有疯狂的像爆炸一般喷溅出来的金黄,也没有像火焰一般跳荡的朱红。在得不到充分燃烧的暗黄与酱红之间,偶尔有绿,是那种缓缓熔开的,灼人眼目的绿的膏浆。张承志写小说,不像是用笔,而像是用刀在那里刻凿。他的稿纸上,到处是被坚硬的笔尖拉破的痕迹。那些痕迹,就像一道道割破的、流血的伤口。许多人因此而不喜欢张承志。因为张承志的作品中找不到正常而明亮的阳光。因为张承志习惯于把一切的一切都推向极致。2张承志写过一份这样的简历:张承志,原藉山东济南,回族,1948年秋生于北京。曾在内蒙牧区插队,放牧四年,后来又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回族区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多以上述三块大陆为倚托。喜爱骑马、孤身长旅、学习民族语言和民谣。迷醉于北方诸族底层大众的坚忍不屈。信仰伊斯兰教。崇拜为保卫内心世界而不惜殉命的回族气质。据张承志说,他儿时曾有一个回族的名字,叫赛义德。这是一个波斯语词,这个名字能证明他是一个圣裔。“赛”的名词,在波斯语原意中有“荣耀的圣裔”,出身名门望族的意思。传教,这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实。中国的穆斯林多是十二世纪成吉思汗西征时迁徙而来(注:仅为作者朱伟观点)。在历史长河中,他们在汉文明的大海中离聚浮沉,散居着默默地一代又一代地移植,在封闭状态下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张承志说,儿时给他烙印最深的,就是他外祖母长久地跪在墙前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长久坚忍地独自一人默诵的背影。那时候,在那个拥挤、狭窄的胡同深处,外祖母下雨的时候总要烙饼。外祖母烙饼烧的是锯末,锯末火又柔又低,黑灰边上低燃着一圈蓝蓝的小火苗。外祖母用一把令箭般的铁条铲,翻饼的时候总是那么专注。雨在屋檐下飘得又细又密,檐下的水洼里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