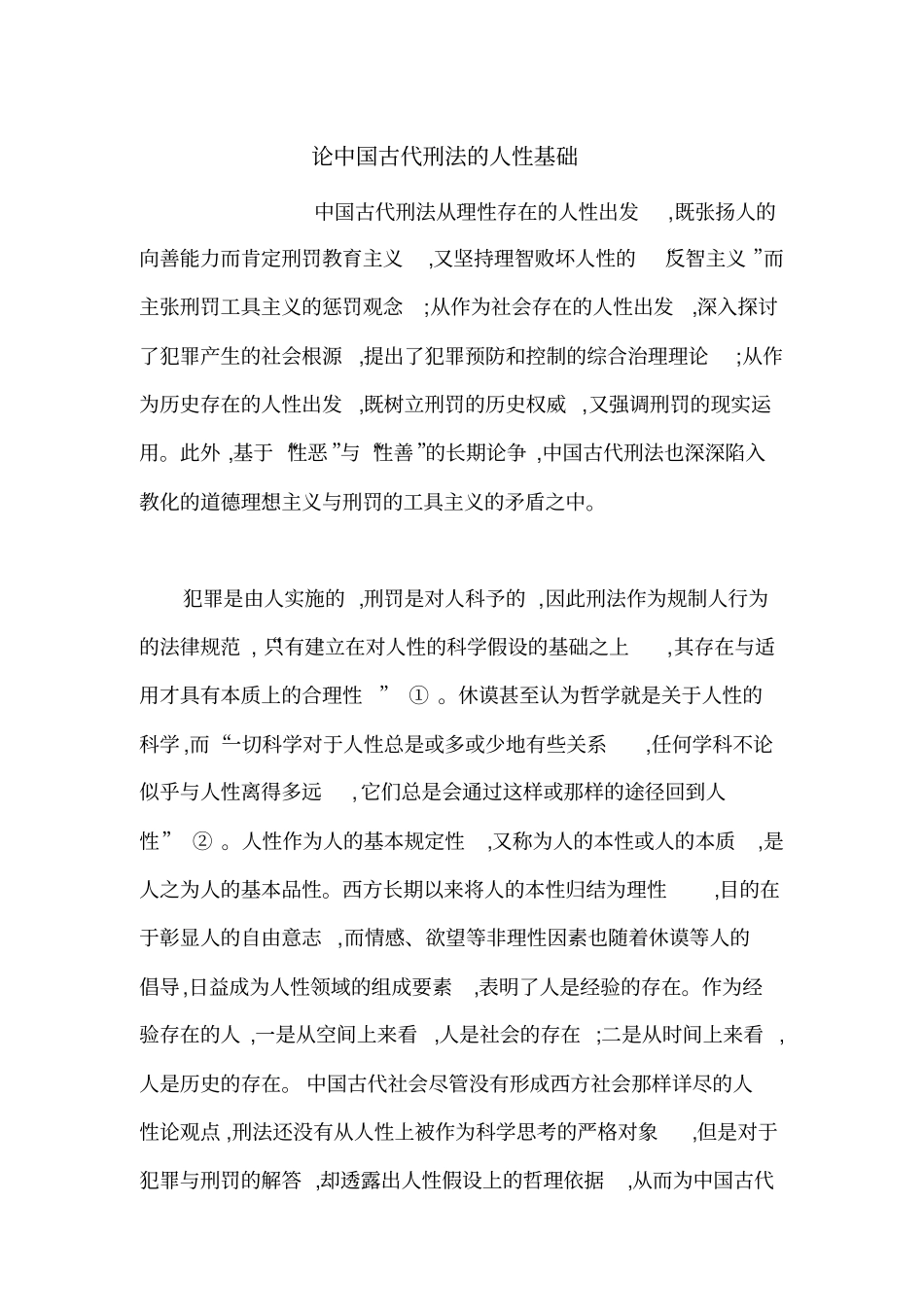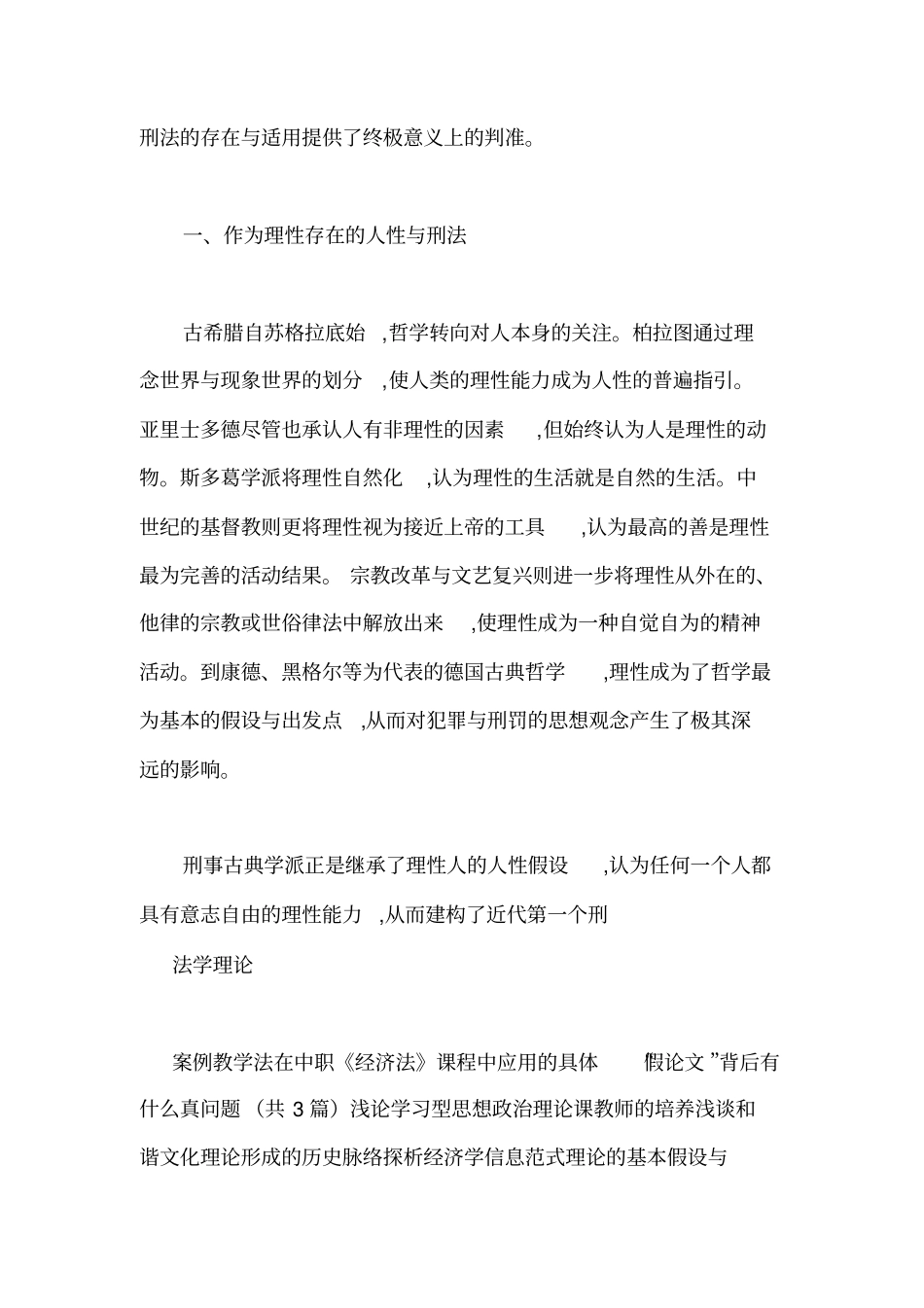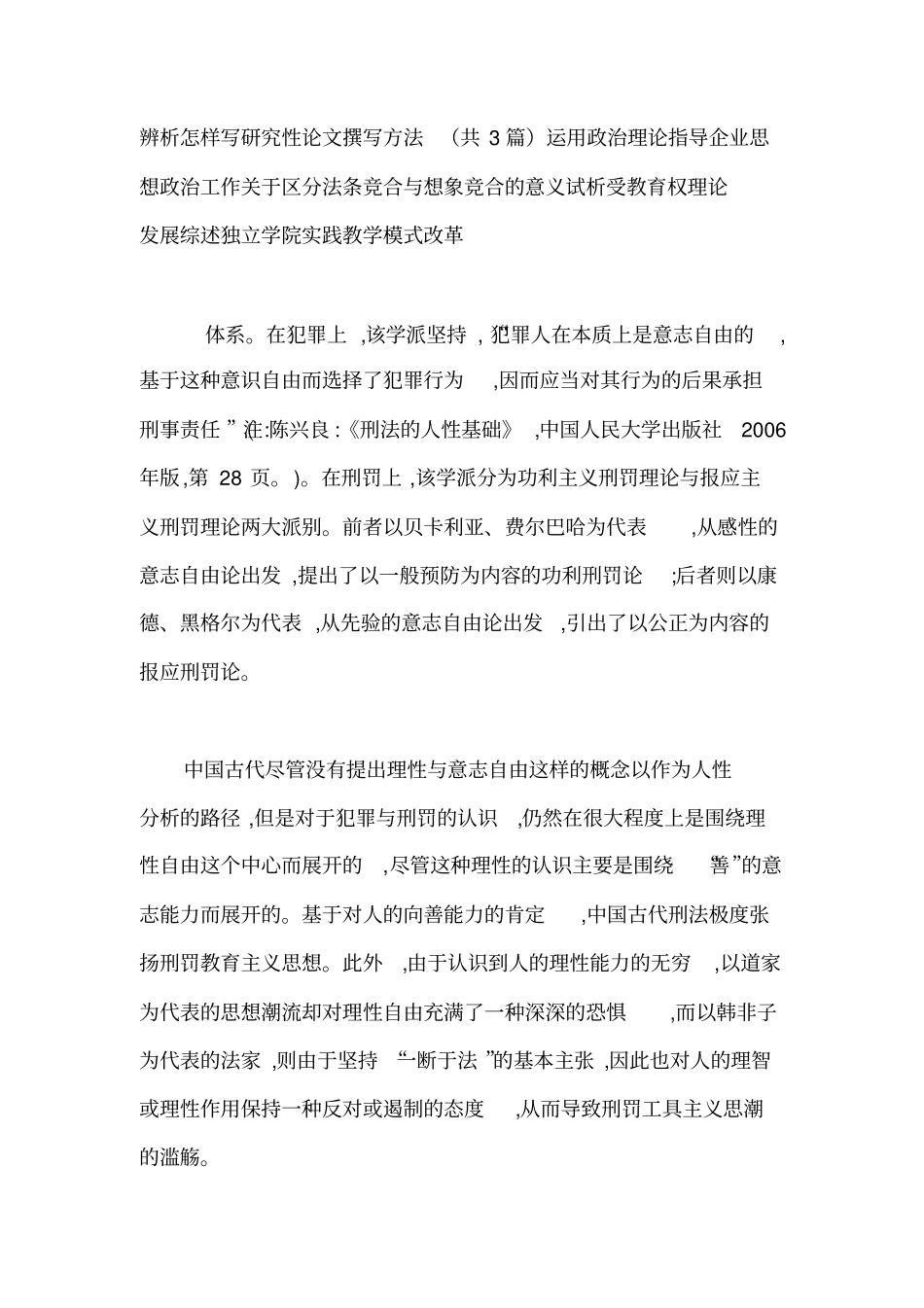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古代刑法从理性存在的人性出发,既张扬人的向善能力而肯定刑罚教育主义,又坚持理智败坏人性的“反智主义 ”而主张刑罚工具主义的惩罚观念;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性出发,深入探讨了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综合治理理论;从作为历史存在的人性出发,既树立刑罚的历史权威 ,又强调刑罚的现实运用。此外 ,基于 “性恶 ”与“性善”的长期论争 ,中国古代刑法也深深陷入教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刑罚的工具主义的矛盾之中。犯罪是由人实施的 ,刑罚是对人科予的 ,因此刑法作为规制人行为的法律规范 , “只有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假设的基础之上,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 ① 。休谟甚至认为哲学就是关于人性的科学 ,而“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 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② 。人性作为人的基本规定性,又称为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性。西方长期以来将人的本性归结为理性,目的在于彰显人的自由意志 ,而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因素也随着休谟等人的倡导,日益成为人性领域的组成要素,表明了人是经验的存在。作为经验存在的人 ,一是从空间上来看,人是社会的存在 ;二是从时间上来看 ,人是历史的存在。 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没有形成西方社会那样详尽的人性论观点 ,刑法还没有从人性上被作为科学思考的严格对象,但是对于犯罪与刑罚的解答 ,却透露出人性假设上的哲理依据,从而为中国古代刑法的存在与适用提供了终极意义上的判准。一、作为理性存在的人性与刑法古希腊自苏格拉底始,哲学转向对人本身的关注。柏拉图通过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划分,使人类的理性能力成为人性的普遍指引。亚里士多德尽管也承认人有非理性的因素,但始终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斯多葛学派将理性自然化,认为理性的生活就是自然的生活。中世纪的基督教则更将理性视为接近上帝的工具,认为最高的善是理性最为完善的活动结果。 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则进一步将理性从外在的、他律的宗教或世俗律法中解放出来,使理性成为一种自觉自为的精神活动。到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理性成为了哲学最为基本的假设与出发点,从而对犯罪与刑罚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刑事古典学派正是继承了理性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意志自由的理性能力,从而建构了近代第一个刑法学理论案例教学法在中职《经济法》课程中应用的具体“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