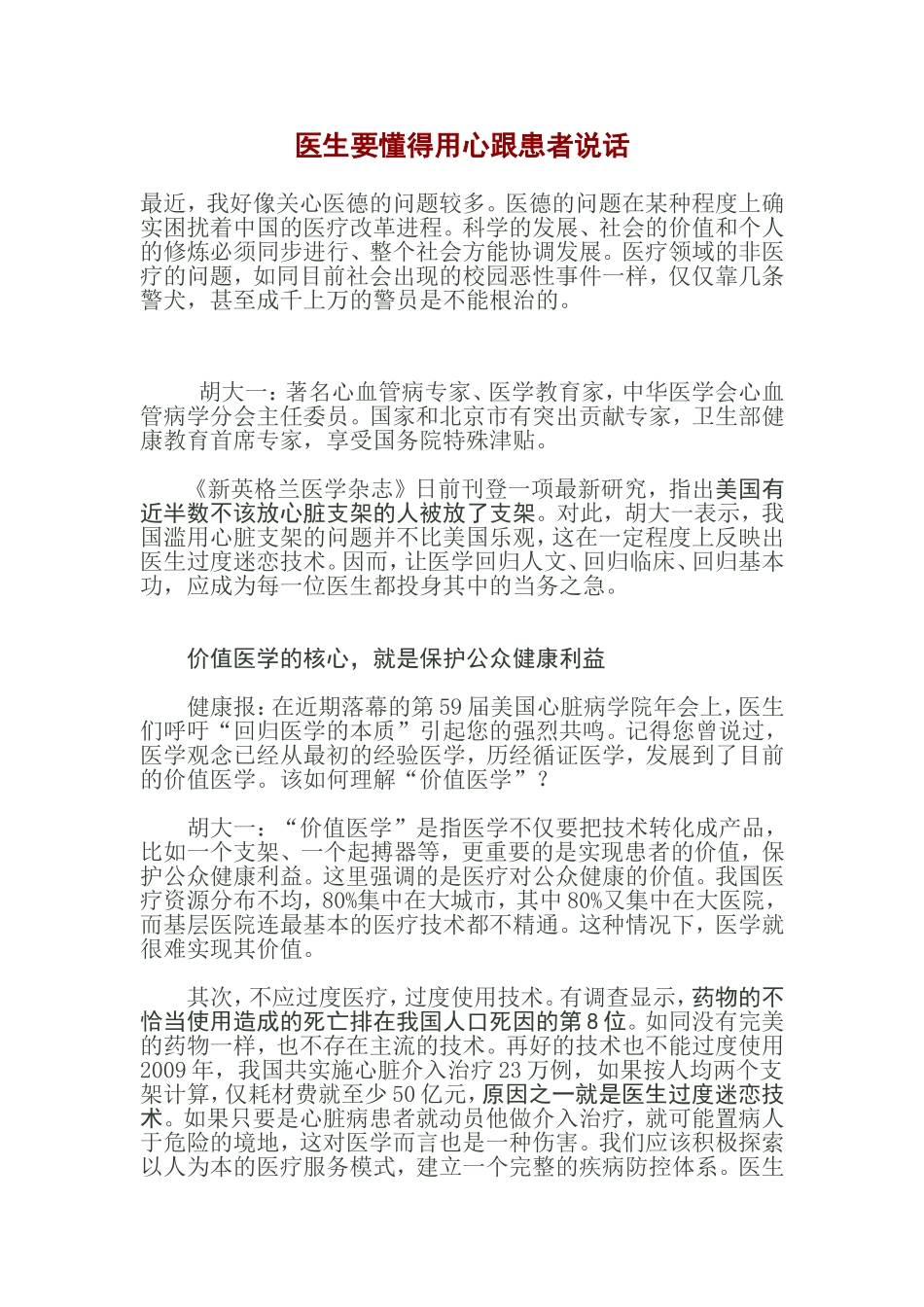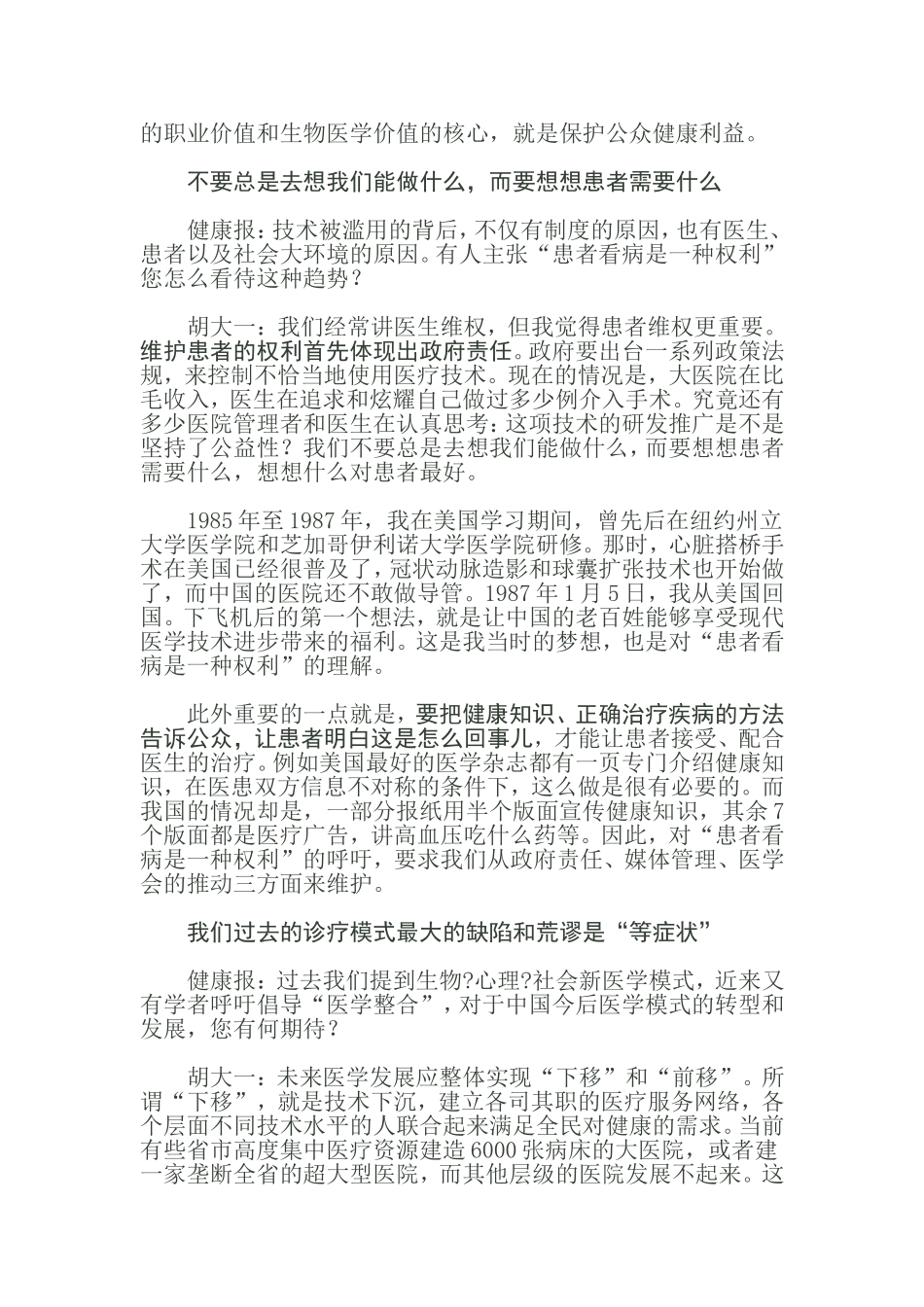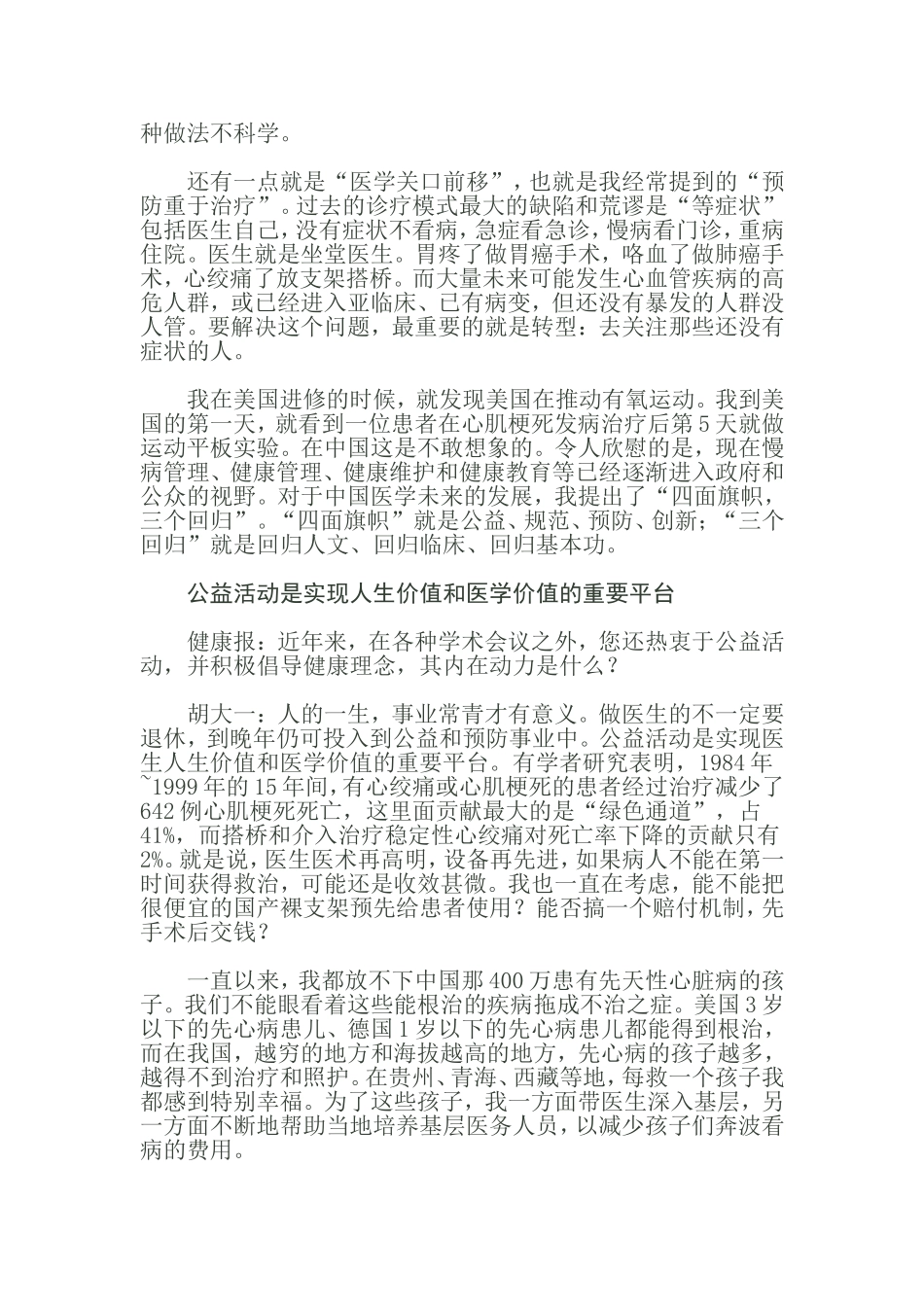医生要懂得用心跟患者说话最近,我好像关心医德的问题较多。医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困扰着中国的医疗改革进程。科学的发展、社会的价值和个人的修炼必须同步进行、整个社会方能协调发展。医疗领域的非医疗的问题,如同目前社会出现的校园恶性事件一样,仅仅靠几条警犬,甚至成千上万的警员是不能根治的。胡大一: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和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日前刊登一项最新研究,指出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心脏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对此,胡大一表示,我国滥用心脏支架的问题并不比美国乐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生过度迷恋技术。因而,让医学回归人文、回归临床、回归基本功,应成为每一位医生都投身其中的当务之急。价值医学的核心,就是保护公众健康利益健康报:在近期落幕的第59届美国心脏病学院年会上,医生们呼吁“回归医学的本质”引起您的强烈共鸣。记得您曾说过,医学观念已经从最初的经验医学,历经循证医学,发展到了目前的价值医学。该如何理解“价值医学”?胡大一:“价值医学”是指医学不仅要把技术转化成产品,比如一个支架、一个起搏器等,更重要的是实现患者的价值,保护公众健康利益。这里强调的是医疗对公众健康的价值。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80%集中在大城市,其中80%又集中在大医院,而基层医院连最基本的医疗技术都不精通。这种情况下,医学就很难实现其价值。其次,不应过度医疗,过度使用技术。有调查显示,药物的不恰当使用造成的死亡排在我国人口死因的第8位。如同没有完美的药物一样,也不存在主流的技术。再好的技术也不能过度使用2009年,我国共实施心脏介入治疗23万例,如果按人均两个支架计算,仅耗材费就至少50亿元,原因之一就是医生过度迷恋技术。如果只要是心脏病患者就动员他做介入治疗,就可能置病人于危险的境地,这对医学而言也是一种伤害。我们应该积极探索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模式,建立一个完整的疾病防控体系。医生的职业价值和生物医学价值的核心,就是保护公众健康利益。不要总是去想我们能做什么,而要想想患者需要什么健康报:技术被滥用的背后,不仅有制度的原因,也有医生、患者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原因。有人主张“患者看病是一种权利”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胡大一:我们经常讲医生维权,但我觉得患者维权更重要。维护患者的权利首先体现出政府责任。政府要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控制不恰当地使用医疗技术。现在的情况是,大医院在比毛收入,医生在追求和炫耀自己做过多少例介入手术。究竟还有多少医院管理者和医生在认真思考:这项技术的研发推广是不是坚持了公益性?我们不要总是去想我们能做什么,而要想想患者需要什么,想想什么对患者最好。1985年至1987年,我在美国学习期间,曾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和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医学院研修。那时,心脏搭桥手术在美国已经很普及了,冠状动脉造影和球囊扩张技术也开始做了,而中国的医院还不敢做导管。1987年1月5日,我从美国回国。下飞机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享受现代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这是我当时的梦想,也是对“患者看病是一种权利”的理解。此外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健康知识、正确治疗疾病的方法告诉公众,让患者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才能让患者接受、配合医生的治疗。例如美国最好的医学杂志都有一页专门介绍健康知识,在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而我国的情况却是,一部分报纸用半个版面宣传健康知识,其余7个版面都是医疗广告,讲高血压吃什么药等。因此,对“患者看病是一种权利”的呼吁,要求我们从政府责任、媒体管理、医学会的推动三方面来维护。我们过去的诊疗模式最大的缺陷和荒谬是“等症状”健康报:过去我们提到生物?心理?社会新医学模式,近来又有学者呼吁倡导“医学整合”,对于中国今后医学模式的转型和发展,您有何期待?胡大一:未来医学发展应整体实现“下移”和“前移”。所谓“下移”,就是技术下沉,建立各司其职的医疗服务网络,各个层面不同技术水平的人联合起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