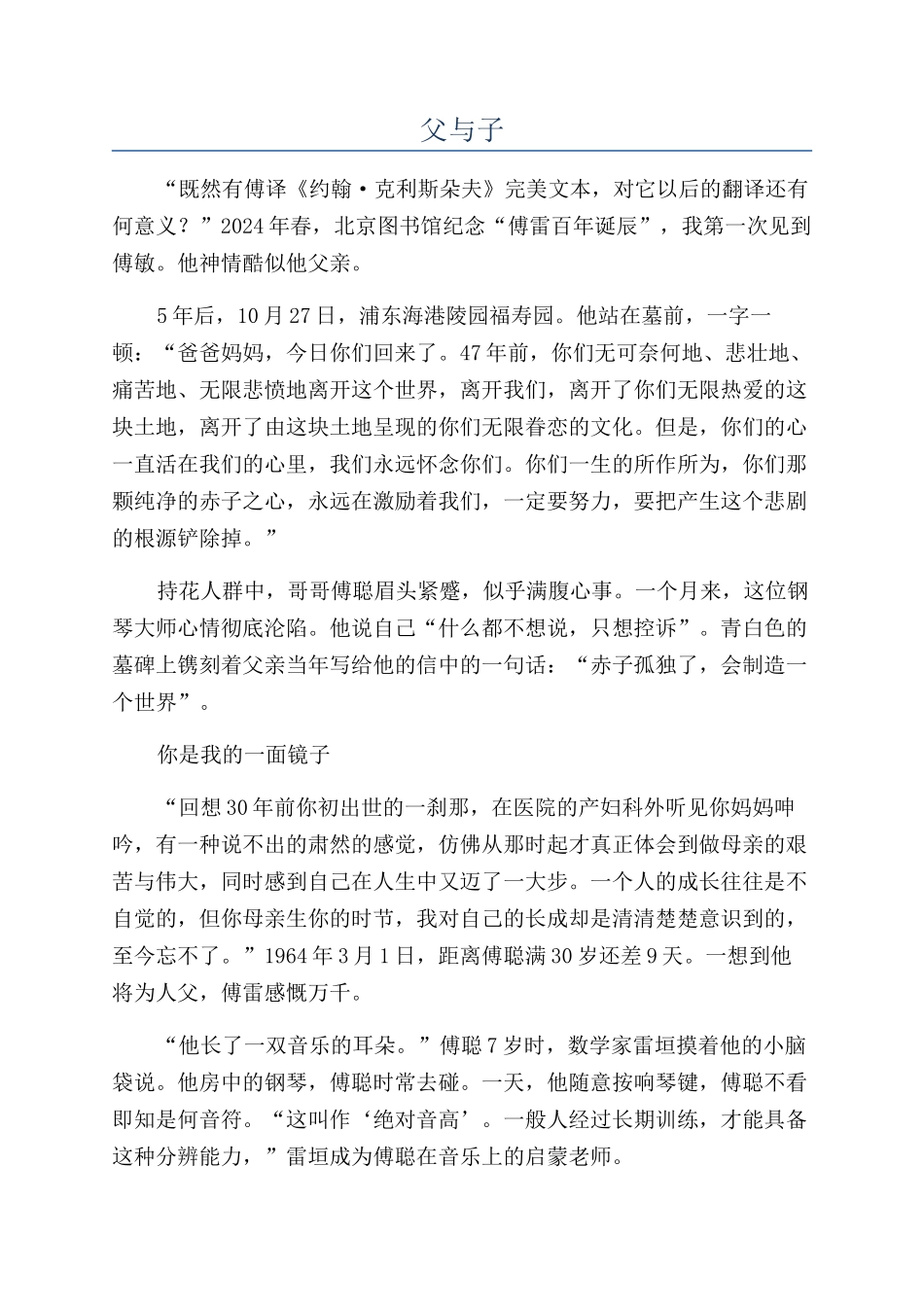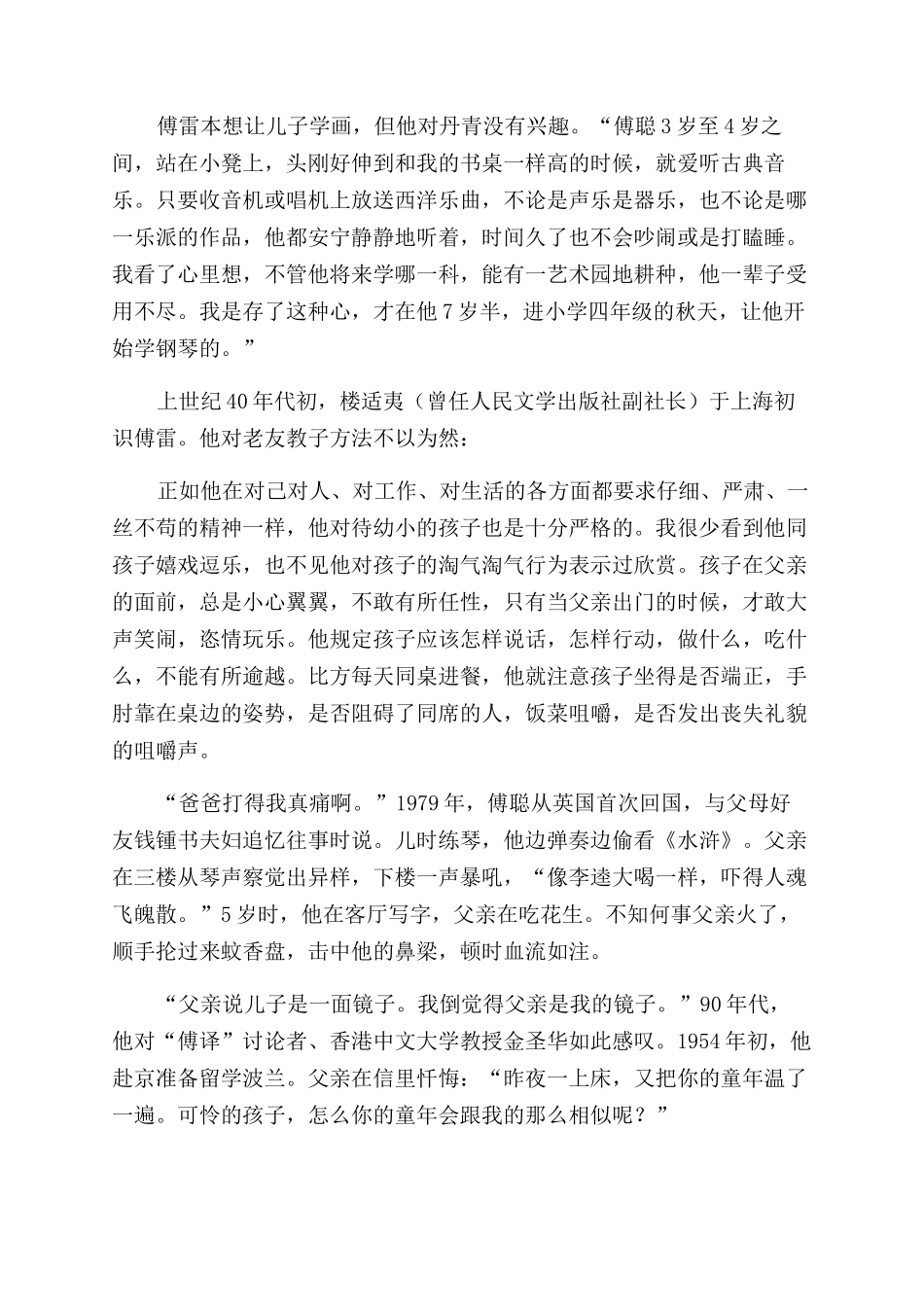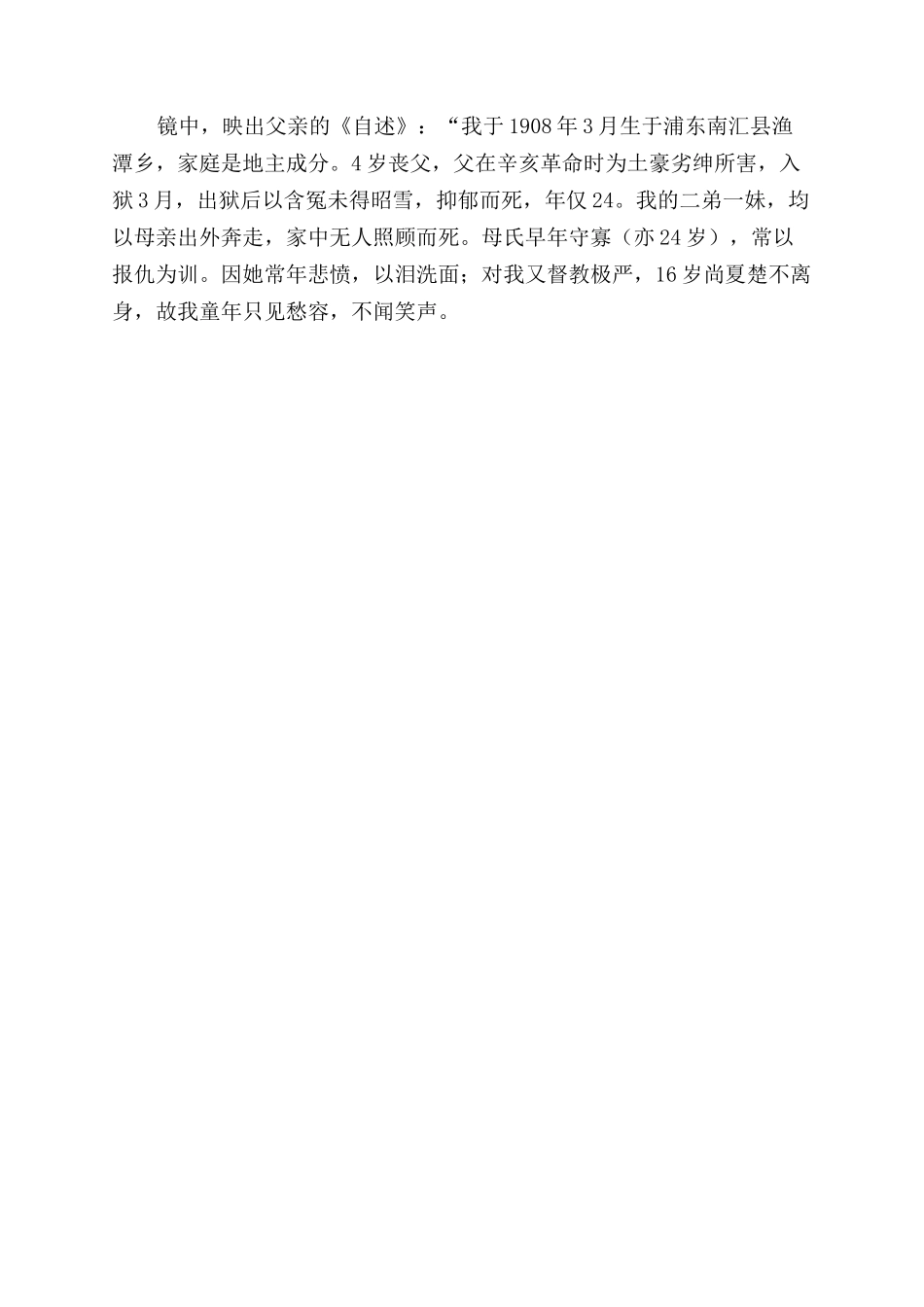父与子“既然有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完美文本,对它以后的翻译还有何意义?”2024 年春,北京图书馆纪念“傅雷百年诞辰”,我第一次见到傅敏。他神情酷似他父亲。5 年后,10 月 27 日,浦东海港陵园福寿园。他站在墓前,一字一顿:“爸爸妈妈,今日你们回来了。47 年前,你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们,离开了你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离开了由这块土地呈现的你们无限眷恋的文化。但是,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在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努力,要把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持花人群中,哥哥傅聪眉头紧蹙,似乎满腹心事。一个月来,这位钢琴大师心情彻底沦陷。他说自己“什么都不想说,只想控诉”。青白色的墓碑上镌刻着父亲当年写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制造一个世界”。你是我的一面镜子“回想 30 年前你初出世的一刹那,在医院的产妇科外听见你妈妈呻吟,有一种说不出的肃然的感觉,仿佛从那时起才真正体会到做母亲的艰苦与伟大,同时感到自己在人生中又迈了一大步。一个人的成长往往是不自觉的,但你母亲生你的时节,我对自己的长成却是清清楚楚意识到的,至今忘不了。”1964 年 3 月 1 日,距离傅聪满 30 岁还差 9 天。一想到他将为人父,傅雷感慨万千。“他长了一双音乐的耳朵。”傅聪 7 岁时,数学家雷垣摸着他的小脑袋说。他房中的钢琴,傅聪时常去碰。一天,他随意按响琴键,傅聪不看即知是何音符。“这叫作‘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具备这种分辨能力,”雷垣成为傅聪在音乐上的启蒙老师。傅雷本想让儿子学画,但他对丹青没有兴趣。“傅聪 3 岁至 4 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宁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 7 岁半,进小学四年级的秋天,让他开始学钢琴的。”上世纪 40 年代初,楼适夷(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于上海初识傅雷。他对老友教子方法不以为然:正如他在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仔细、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