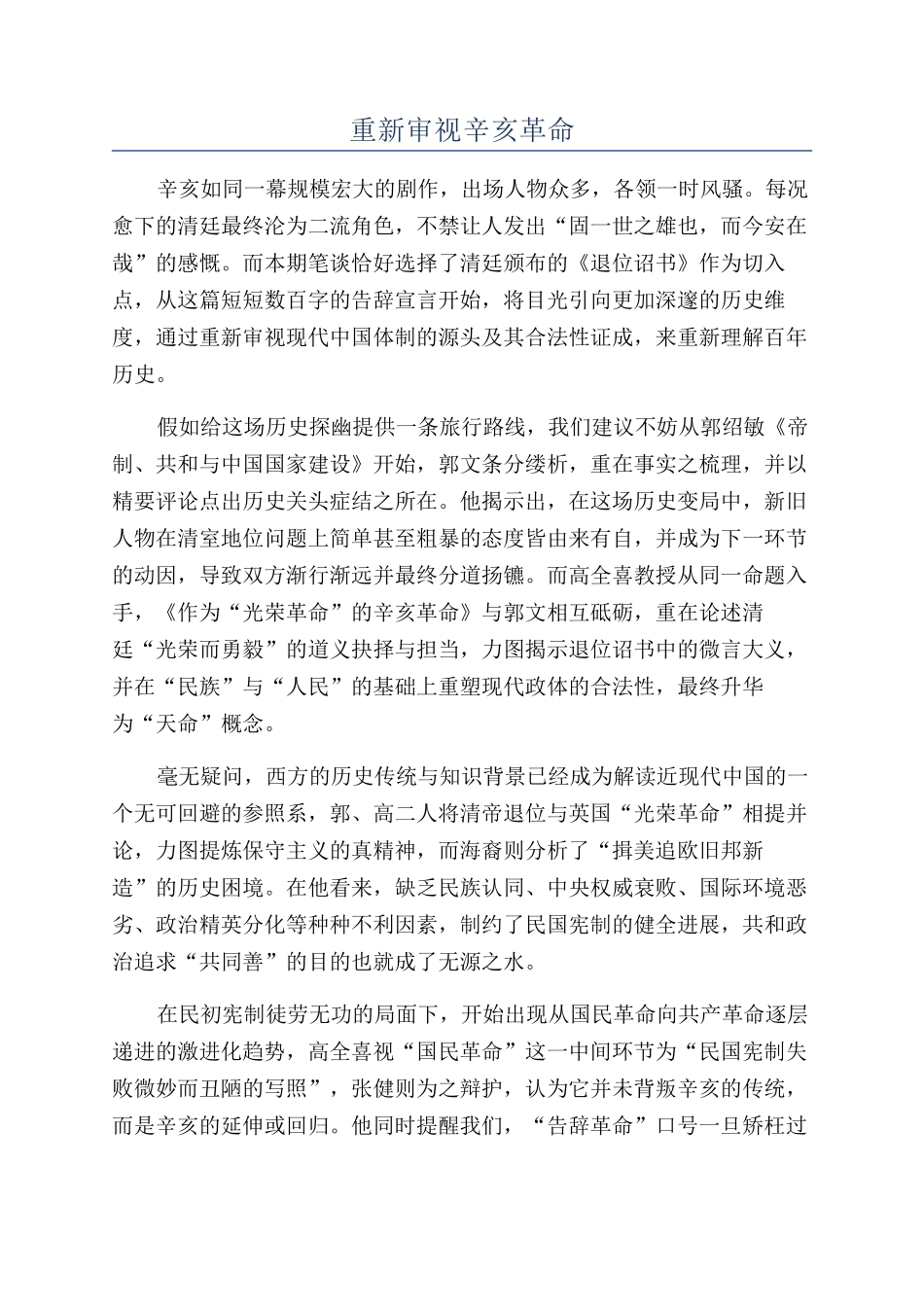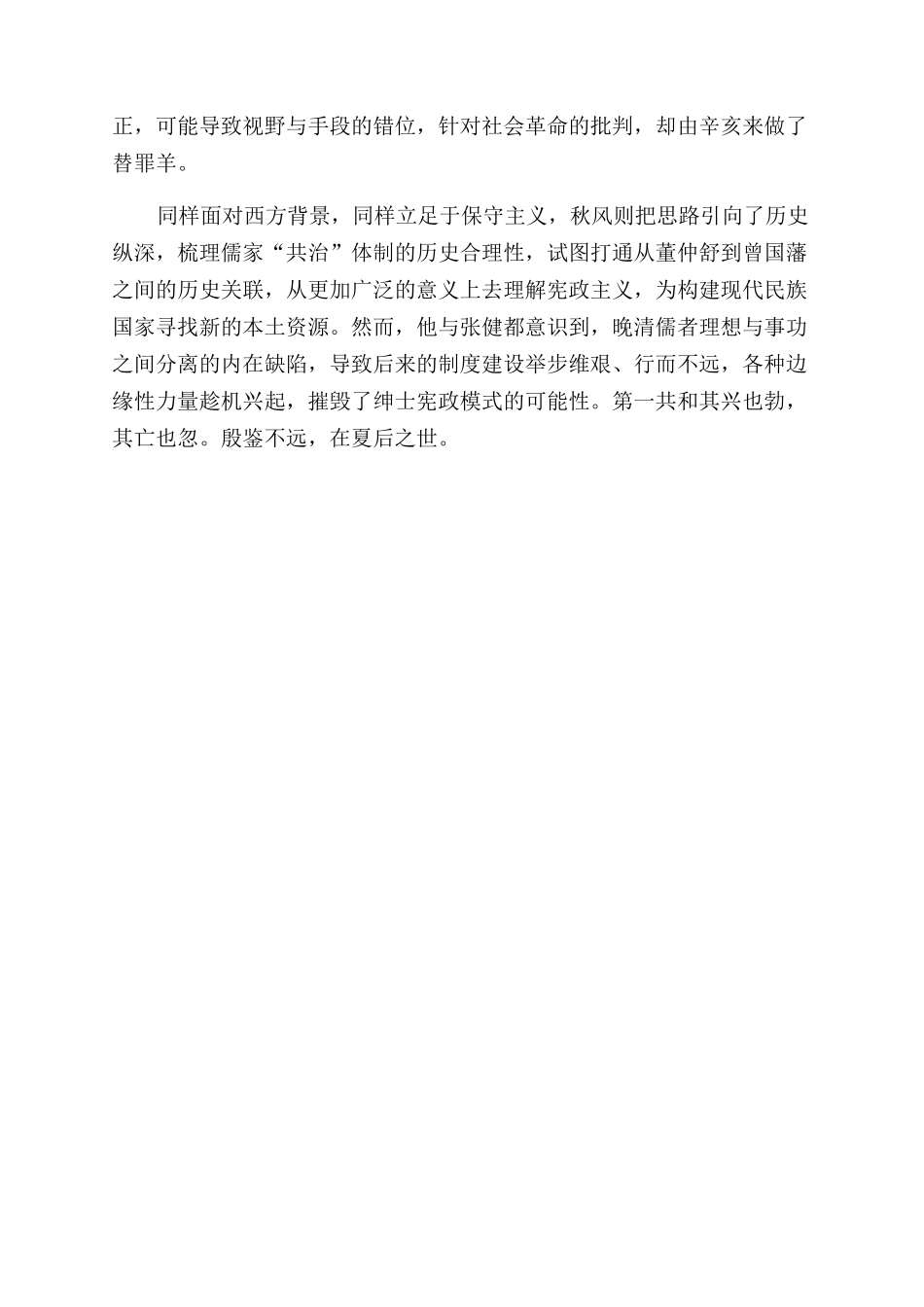重新审视辛亥革命辛亥如同一幕规模宏大的剧作,出场人物众多,各领一时风骚。每况愈下的清廷最终沦为二流角色,不禁让人发出“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感慨。而本期笔谈恰好选择了清廷颁布的《退位诏书》作为切入点,从这篇短短数百字的告辞宣言开始,将目光引向更加深邃的历史维度,通过重新审视现代中国体制的源头及其合法性证成,来重新理解百年历史。假如给这场历史探幽提供一条旅行路线,我们建议不妨从郭绍敏《帝制、共和与中国国家建设》开始,郭文条分缕析,重在事实之梳理,并以精要评论点出历史关头症结之所在。他揭示出,在这场历史变局中,新旧人物在清室地位问题上简单甚至粗暴的态度皆由来有自,并成为下一环节的动因,导致双方渐行渐远并最终分道扬镳。而高全喜教授从同一命题入手,《作为“光荣革命”的辛亥革命》与郭文相互砥砺,重在论述清廷“光荣而勇毅”的道义抉择与担当,力图揭示退位诏书中的微言大义,并在“民族”与“人民”的基础上重塑现代政体的合法性,最终升华为“天命”概念。毫无疑问,西方的历史传统与知识背景已经成为解读近现代中国的一个无可回避的参照系,郭、高二人将清帝退位与英国“光荣革命”相提并论,力图提炼保守主义的真精神,而海裔则分析了“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的历史困境。在他看来,缺乏民族认同、中央权威衰败、国际环境恶劣、政治精英分化等种种不利因素,制约了民国宪制的健全进展,共和政治追求“共同善”的目的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在民初宪制徒劳无功的局面下,开始出现从国民革命向共产革命逐层递进的激进化趋势,高全喜视“国民革命”这一中间环节为“民国宪制失败微妙而丑陋的写照”,张健则为之辩护,认为它并未背叛辛亥的传统,而是辛亥的延伸或回归。他同时提醒我们,“告辞革命”口号一旦矫枉过正,可能导致视野与手段的错位,针对社会革命的批判,却由辛亥来做了替罪羊。同样面对西方背景,同样立足于保守主义,秋风则把思路引向了历史纵深,梳理儒家“共治”体制的历史合理性,试图打通从董仲舒到曾国藩之间的历史关联,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宪政主义,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寻找新的本土资源。然而,他与张健都意识到,晚清儒者理想与事功之间分离的内在缺陷,导致后来的制度建设举步维艰、行而不远,各种边缘性力量趁机兴起,摧毁了绅士宪政模式的可能性。第一共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