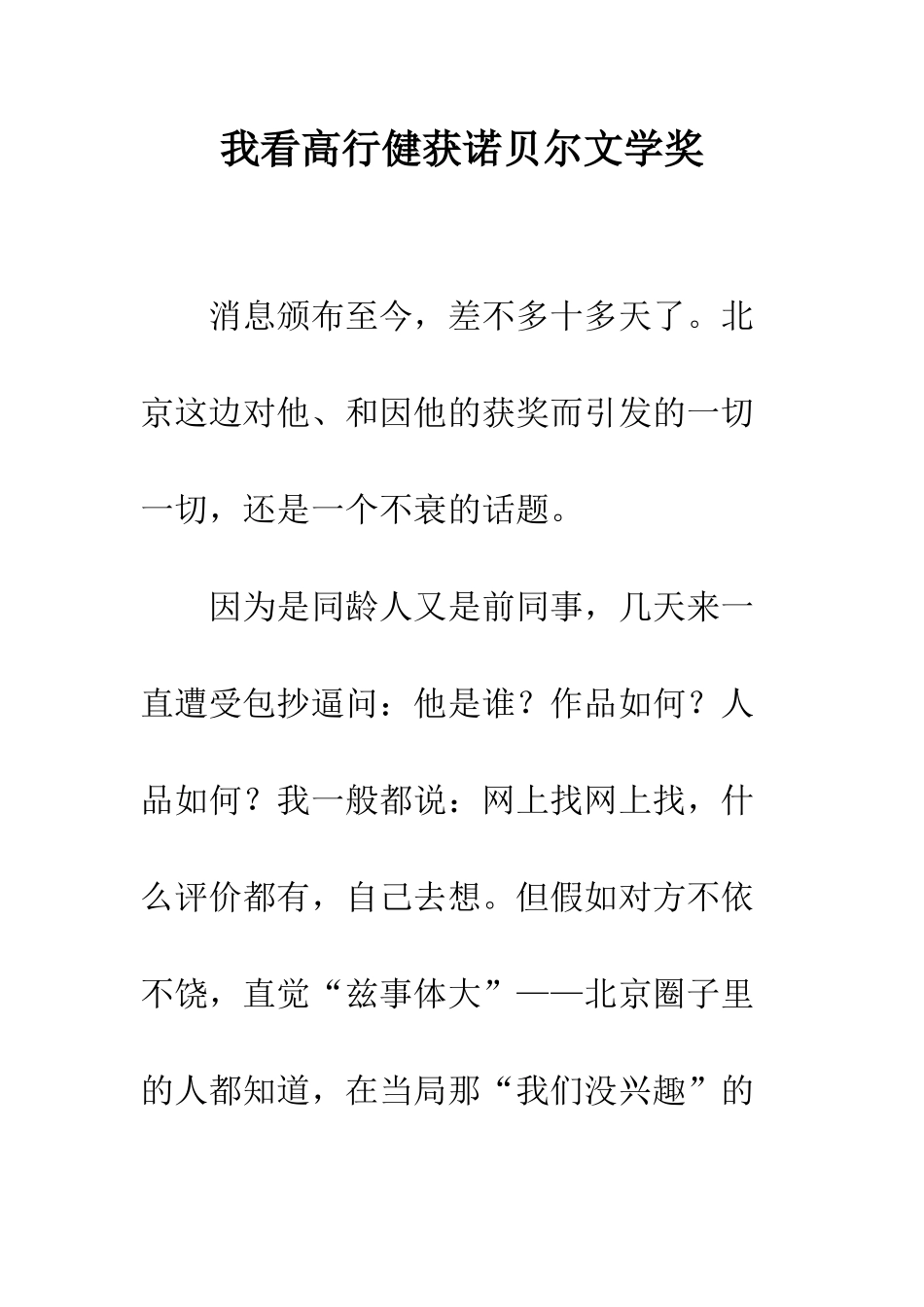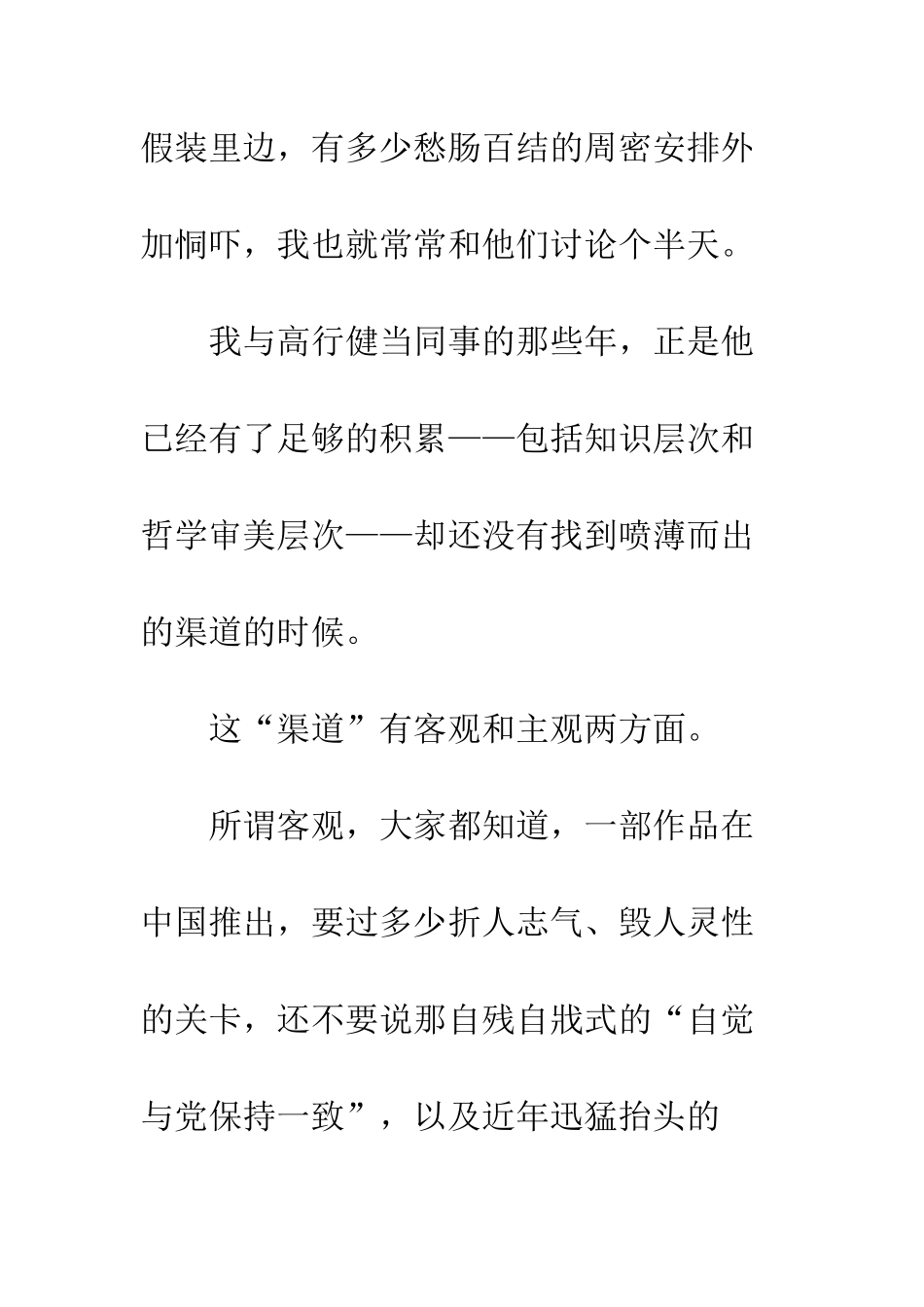我看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 消息颁布至今,差不多十多天了。北京这边对他、和因他的获奖而引发的一切一切,还是一个不衰的话题。 因为是同龄人又是前同事,几天来一直遭受包抄逼问:他是谁?作品如何?人品如何?我一般都说:网上找网上找,什么评价都有,自己去想。但假如对方不依不饶,直觉“兹事体大”——北京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在当局那“我们没兴趣”的假装里边,有多少愁肠百结的周密安排外加恫吓,我也就常常和他们讨论个半天。 我与高行健当同事的那些年,正是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包括知识层次和哲学审美层次——却还没有找到喷薄而出的渠道的时候。 这“渠道”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 所谓客观,大家都知道,一部作品在中国推出,要过多少折人志气、毁人灵性的关卡,还不要说那自残自戕式的“自觉与党保持一致”,以及近年迅猛抬头的“看在丰厚酬劳”面上的媚俗。高行健与政治非常疏离。这疏离不是出于清高,也说不上恐惧,他根本就没活在那个情境之中。不在此情境却须时时折回头上下左右打点,这并不比鲁迅形容的“侧着身子战斗”轻松。 不错,他曾经申请入党,或许也发过“为党的事业献身”之类的豪言。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无法与坚贞纯洁的沈从文相比。但这正是他要探询的“人性软弱”的一面,而且他毕竟挣扎出来,从那个调动全部社会资源将人变为机器零件环境中。 假如没有对像他这样疏离的人都不放过的挤压,外加那则肺癌误诊,他或许还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忍耐着、苟且着、相当克制地抗争着……但它们不由分说地轰然而至,惊破了人性中常有的消极、怠惰。还等什么呢?高行健决定以“有限的时间”做他最想做的事:探询生命的原意、体验生命的真髓,然后——假如“时尚我待”,说出想说的话。他出发了,什么文坛、剧坛纷争,什么绊羁着我们俗人的种种牵挂、纠葛,已经全不相干。他轻松上路,活一天算一天,而且只活在自己“赤裸裸无须掩盖的真实里。” 更值得庆幸的是,在精神获得自由的同时,他所有知识与文化积累、包括语言技巧,都活起来了。 至于主观,以我的从旁观察,从他 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到他离开中国的那十年间,还不十分清楚究竟什么形态是他表达感受的最好渠道——各种艺术形态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说,他从来不甘心自身感受的表达要拘泥于人为规定的框框。他的开始画画也是出于偶然:先是请人替他画几幅作礼品,后来想想何不自己画呢?有丰富的内心感受、有开拓性的鉴赏力,学院式训练几乎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