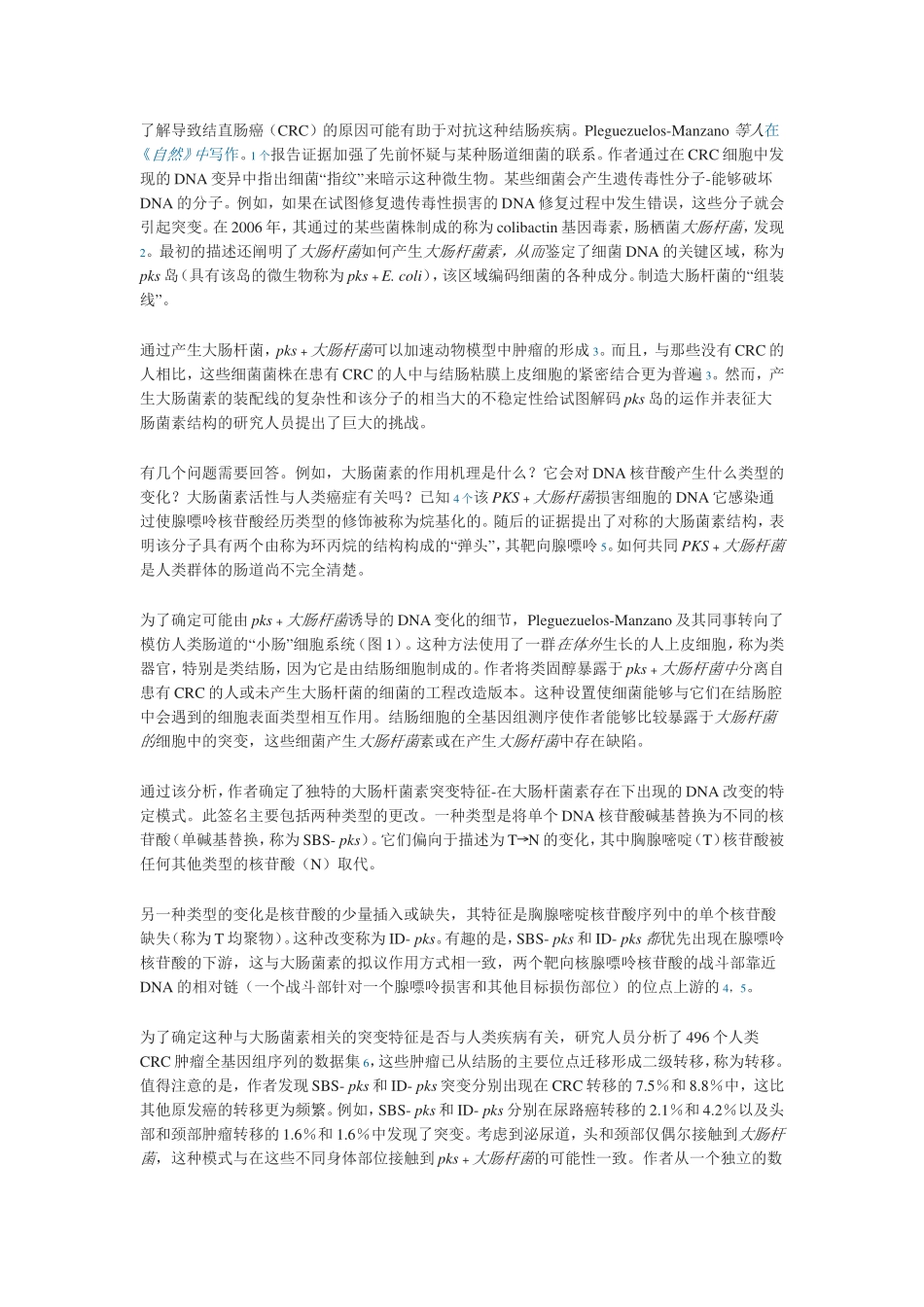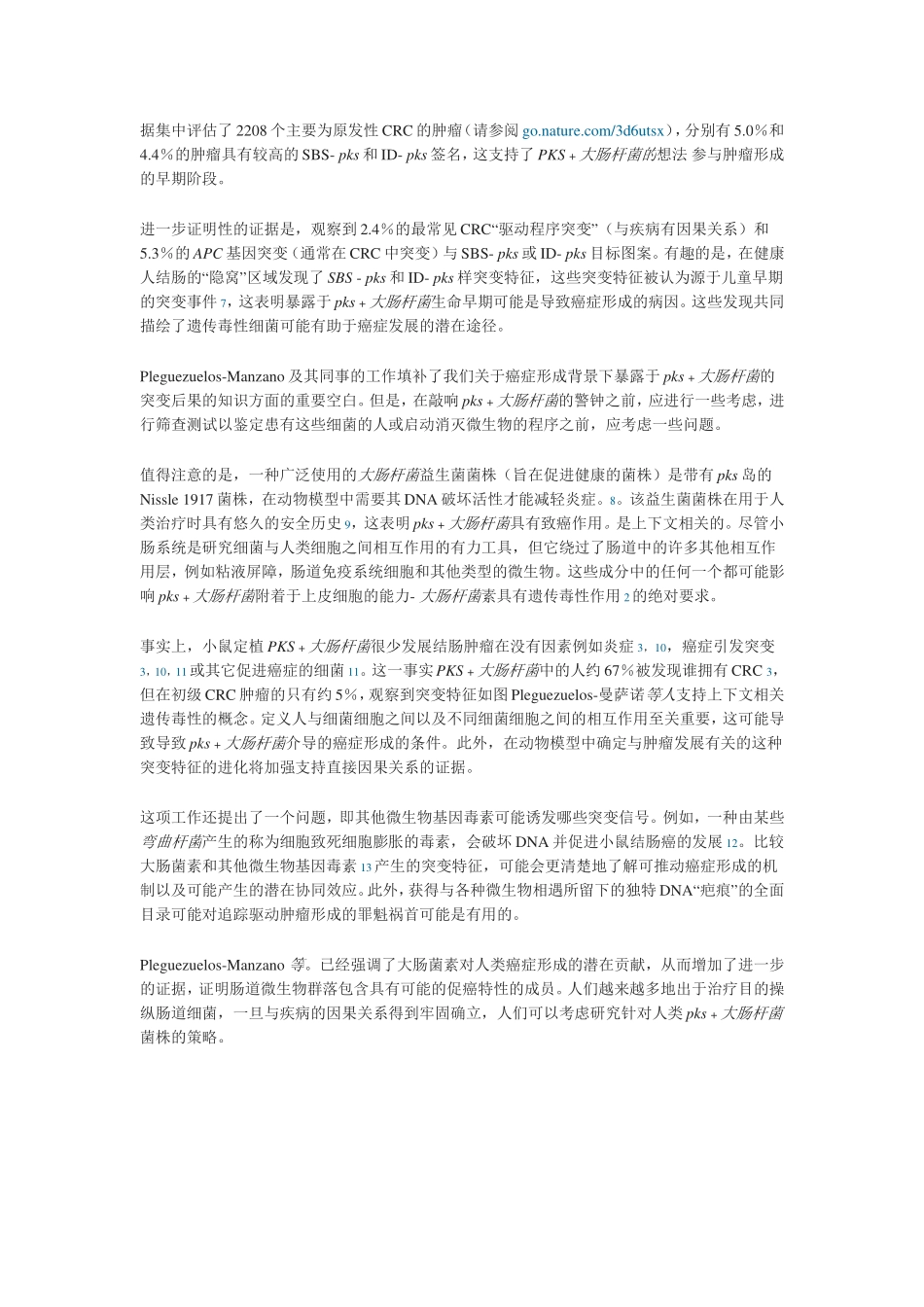了解导致结直肠癌(CRC)的原因可能有助于对抗这种结肠疾病。Pleguezuelos-Manzano等人在《自然》中写作。1个报告证据加强了先前怀疑与某种肠道细菌的联系。作者通过在CRC细胞中发现的DNA“”变异中指出细菌指纹来暗示这种微生物。某些细菌会产生遗传毒性分子-能够破坏DNA的分子。例如,如果在试图修复遗传毒性损害的DNA修复过程中发生错误,这些分子就会引起突变。在2006年,其通过的某些菌株制成的称为colibactin基因毒素,肠栖菌大肠杆菌,发现2。最初的描述还阐明了大肠杆菌如何产生大肠杆菌素,从而鉴定了细菌DNA的关键区域,称为pks岛(具有该岛的微生物称为pks+E.coli“),该区域编码细菌的各种成分。制造大肠杆菌的组装”线。通过产生大肠杆菌,pks+大肠杆菌可以加速动物模型中肿瘤的形成3。而且,与那些没有CRC的人相比,这些细菌菌株在患有CRC的人中与结肠粘膜上皮细胞的紧密结合更为普遍3。然而,产生大肠菌素的装配线的复杂性和该分子的相当大的不稳定性给试图解码pks岛的运作并表征大肠菌素结构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例如,大肠菌素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它会对DNA核苷酸产生什么类型的变化?大肠菌素活性与人类癌症有关吗?已知4个该PKS+大肠杆菌损害细胞的DNA它感染通过使腺嘌呤核苷酸经历类型的修饰被称为烷基化的。随后的证据提出了对称的大肠菌素结构,表“”明该分子具有两个由称为环丙烷的结构构成的弹头,其靶向腺嘌呤5。如何共同PKS+大肠杆菌是人类群体的肠道尚不完全清楚。为了确定可能由pks+大肠杆菌诱导的DNA变化的细节,Pleguezuelos-Manzano及其同事转向了“”模仿人类肠道的小肠细胞系统(图1)。这种方法使用了一群在体外生长的人上皮细胞,称为类器官,特别是类结肠,因为它是由结肠细胞制成的。作者将类固醇暴露于pks+大肠杆菌中分离自患有CRC的人或未产生大肠杆菌的细菌的工程改造版本。这种设置使细菌能够与它们在结肠腔中会遇到的细胞表面类型相互作用。结肠细胞的全基因组测序使作者能够比较暴露于大肠杆菌的细胞中的突变,这些细菌产生大肠杆菌素或在产生大肠杆菌中存在缺陷。通过该分析,作者确定了独特的大肠杆菌素突变特征-在大肠杆菌素存在下出现的DNA改变的特定模式。此签名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更改。一种类型是将单个DNA核苷酸碱基替换为不同的核苷酸(单碱基替换,称为SBS-pks)。它们偏向于描述为T→N的变化,其中胸腺嘧啶(T)核苷酸被任何其他类型的核苷酸(N)取代。另一种类型的变化是核苷酸的少量插入或缺失,其特征是胸腺嘧啶核苷酸序列中的单个核苷酸缺失(称为T均聚物)。这种改变称为ID-pks。有趣的是,SBS-pks和ID-pks都优先出现在腺嘌呤核苷酸的下游,这与大肠菌素的拟议作用方式相一致,两个靶向核腺嘌呤核苷酸的战斗部靠近DNA的相对链(一个战斗部针对一个腺嘌呤损害和其他目标损伤部位)的位点上游的4,5。为了确定这种与大肠菌素相关的突变特征是否与人类疾病有关,研究人员分析了496个人类CRC肿瘤全基因组序列的数据集6,这些肿瘤已从结肠的主要位点迁移形成二级转移,称为转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发现SBS-pks和ID-pks突变分别出现在CRC转移的7.5%和8.8%中,这比其他原发癌的转移更为频繁。例如,SBS-pks和ID-pks分别在尿路癌转移的2.1%和4.2%以及头部和颈部肿瘤转移的1.6%和1.6%中发现了突变。考虑到泌尿道,头和颈部仅偶尔接触到大肠杆菌,这种模式与在这些不同身体部位接触到pks+大肠杆菌的可能性一致。作者从一个独立的数据集中评估了2208个主要为原发性CRC的肿瘤(请参阅go.nature.com/3d6utsx),分别有5.0%和4.4%的肿瘤具有较高的SBS-pks和ID-pks签名,这支持了PKS+大肠杆菌的想法参与肿瘤形成的早期阶段。进一步证明性的证据是,观察到2.4%的最常见CRC“”驱动程序突变(与疾病有因果关系)和5.3%的APC基因突变(通常在CRC中突变)与SBS-pks或ID-pks目标图案。有趣的是,在健康“”人结肠的隐窝区域发现了SBS-pks和ID-pks样突变特征,这些突变特征被认为源于儿童早期的突变事件7,这表明暴露于pks+大肠杆菌生命早期可能是导致癌症形成的病因。这些发现共同描绘了遗传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