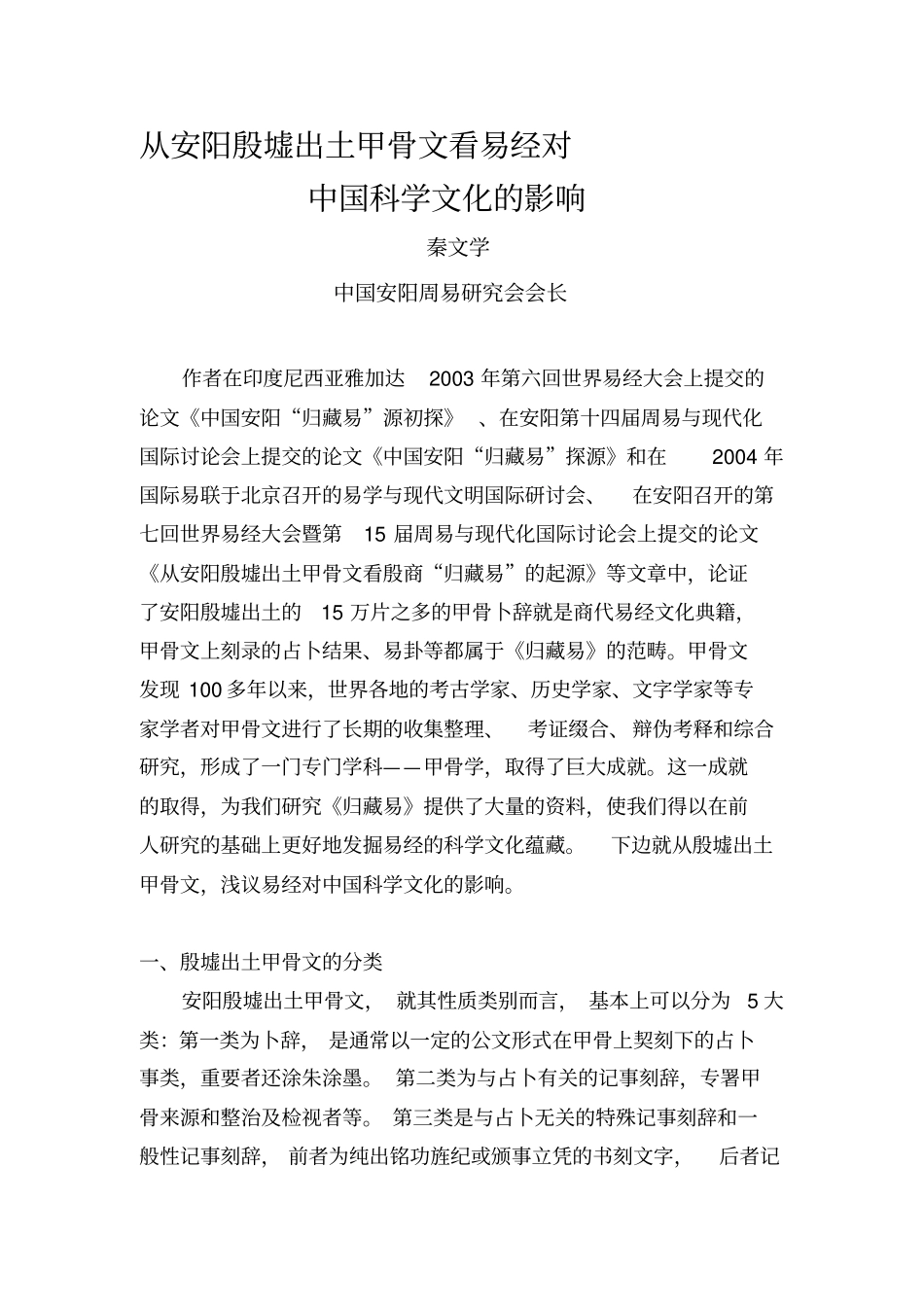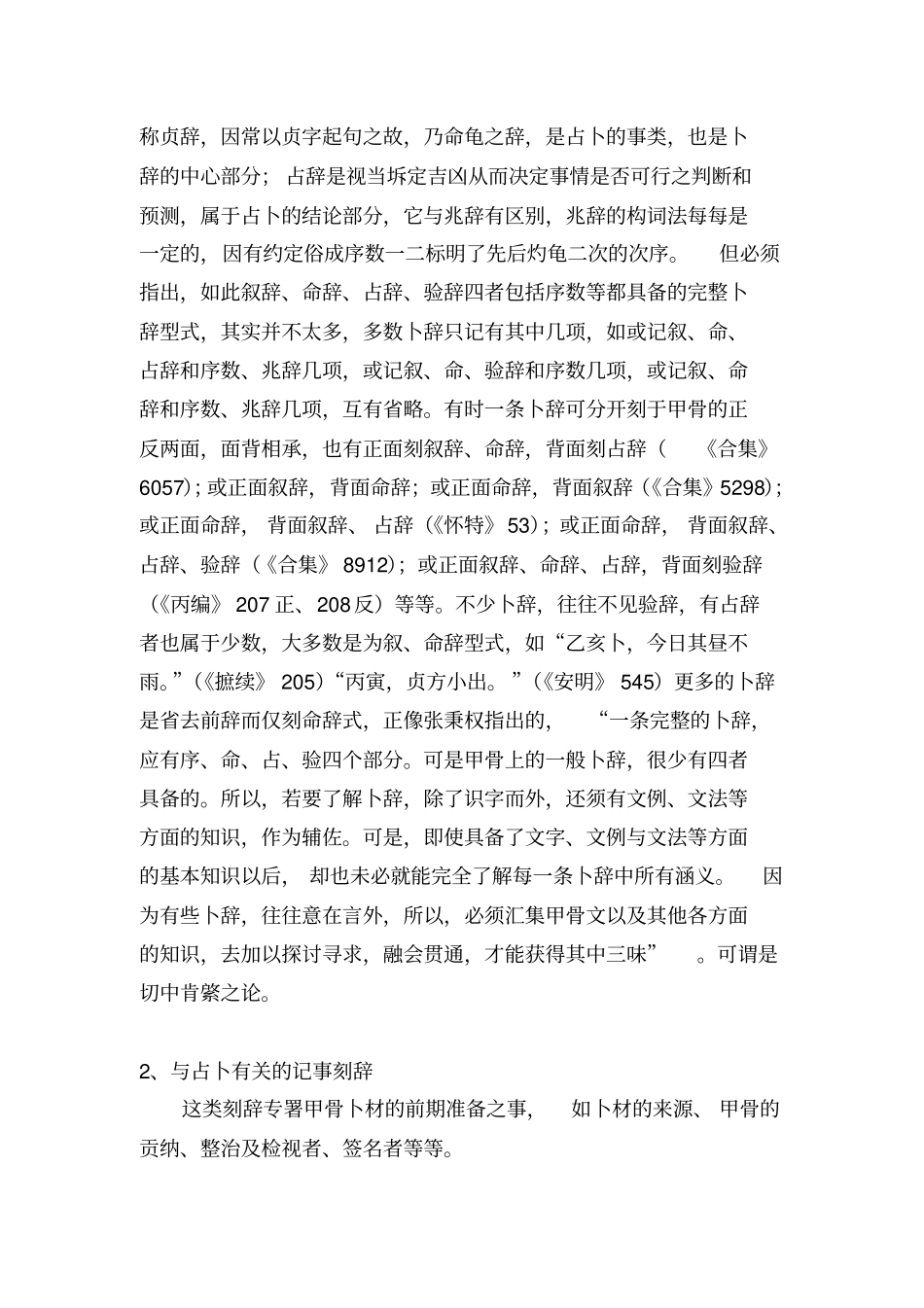从安阳殷墟出土甲骨文看易经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影响秦文学中国安阳周易研究会会长作者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2003年第六回世界易经大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国安阳“归藏易”源初探》、在安阳第十四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国安阳“归藏易”探源》和在2004年国际易联于北京召开的易学与现代文明国际研讨会、在安阳召开的第七回世界易经大会暨第15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从安阳殷墟出土甲骨文看殷商“归藏易”的起源》等文章中,论证了安阳殷墟出土的15万片之多的甲骨卜辞就是商代易经文化典籍,甲骨文上刻录的占卜结果、易卦等都属于《归藏易》的范畴。甲骨文发现100多年以来,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等专家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长期的收集整理、考证缀合、辩伪考释和综合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学科——甲骨学,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为我们研究《归藏易》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使我们得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掘易经的科学文化蕴藏。下边就从殷墟出土甲骨文,浅议易经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影响。一、殷墟出土甲骨文的分类安阳殷墟出土甲骨文,就其性质类别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5大类:第一类为卜辞,是通常以一定的公文形式在甲骨上契刻下的占卜事类,重要者还涂朱涂墨。第二类为与占卜有关的记事刻辞,专署甲骨来源和整治及检视者等。第三类是与占卜无关的特殊记事刻辞和一般性记事刻辞,前者为纯出铭功旌纪或颁事立凭的书刻文字,后者记日常生活行事。第四类是表谱刻辞,如干支表,家谱刻辞等,备览之用。第五类是习刻之作,为仿刻习作。1、甲骨卜辞主要是指从安阳殷墟出土的在卜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所刻写的占卜记录,文字内容大都以殷商王朝武丁以来下至商末各时王的占卜行事为主体,也包括数量不等的其他贵族家支的占卜记录。甲骨卜辞通常是在贞人灼龟命卜后,以一定的公文形式在甲骨上刻写下的相关文辞。一条完整的卜辞,可以包含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通常情况下还包含序数(或卜数)和兆辞。但应注意者,序数一般是先于卜辞契刻的,当灼龟命卜之际,每灼一兆,便要刻一序数字,以标明灼龟见兆的次序,故也称兆序,凡兆坼向左者,序数通常刻在卜兆的左上端,反之则刻于右上端,也有刻于纵兆顶端的;而卜辞则是占卜完成后才契刻的。甲骨上常发现有的序数刻后,因占了卜辞位置而被刮去,有的还重刻于别的空处,即是兆序先刻于卜辞的证明。兆序虽与卜辞关系密切,却又相对独立,有序数而无卜辞的甲骨甚多。兆序在龟甲上的排列形式,通常情况下是自上而下,一行至数行直下不等,或自内(中缝)向外(边缘),或自外(边缘)向内(中缝)。在胛骨上的序数或卜数,则一般以自下而上排列为多,也有自下而上再折而向下排列的,如《合集》23988、《粹》1328+《遗珠》948,但不多见。兆辞则是灼龟命卜视兆象定吉凶的简单断语,也是卜辞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占卜事类单看序数、卜数和兆辞是不可能了解的,唯有看卜辞的主体部分叙辞、命辞乃至于占辞、验辞方能知晓。叙辞也称前辞,指整条卜辞前面记卜日和贞人名的文辞;命辞也称贞辞,因常以贞字起句之故,乃命龟之辞,是占卜的事类,也是卜辞的中心部分;占辞是视当坼定吉凶从而决定事情是否可行之判断和预测,属于占卜的结论部分,它与兆辞有区别,兆辞的构词法每每是一定的,因有约定俗成序数一二标明了先后灼龟二次的次序。但必须指出,如此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者包括序数等都具备的完整卜辞型式,其实并不太多,多数卜辞只记有其中几项,如或记叙、命、占辞和序数、兆辞几项,或记叙、命、验辞和序数几项,或记叙、命辞和序数、兆辞几项,互有省略。有时一条卜辞可分开刻于甲骨的正反两面,面背相承,也有正面刻叙辞、命辞,背面刻占辞(《合集》6057);或正面叙辞,背面命辞;或正面命辞,背面叙辞(《合集》5298);或正面命辞,背面叙辞、占辞(《怀特》53);或正面命辞,背面叙辞、占辞、验辞(《合集》8912);或正面叙辞、命辞、占辞,背面刻验辞(《丙编》207正、208反)等等。不少卜辞,往往不见验辞,有占辞者也属于少数,大多数是为叙、命辞型式,如“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