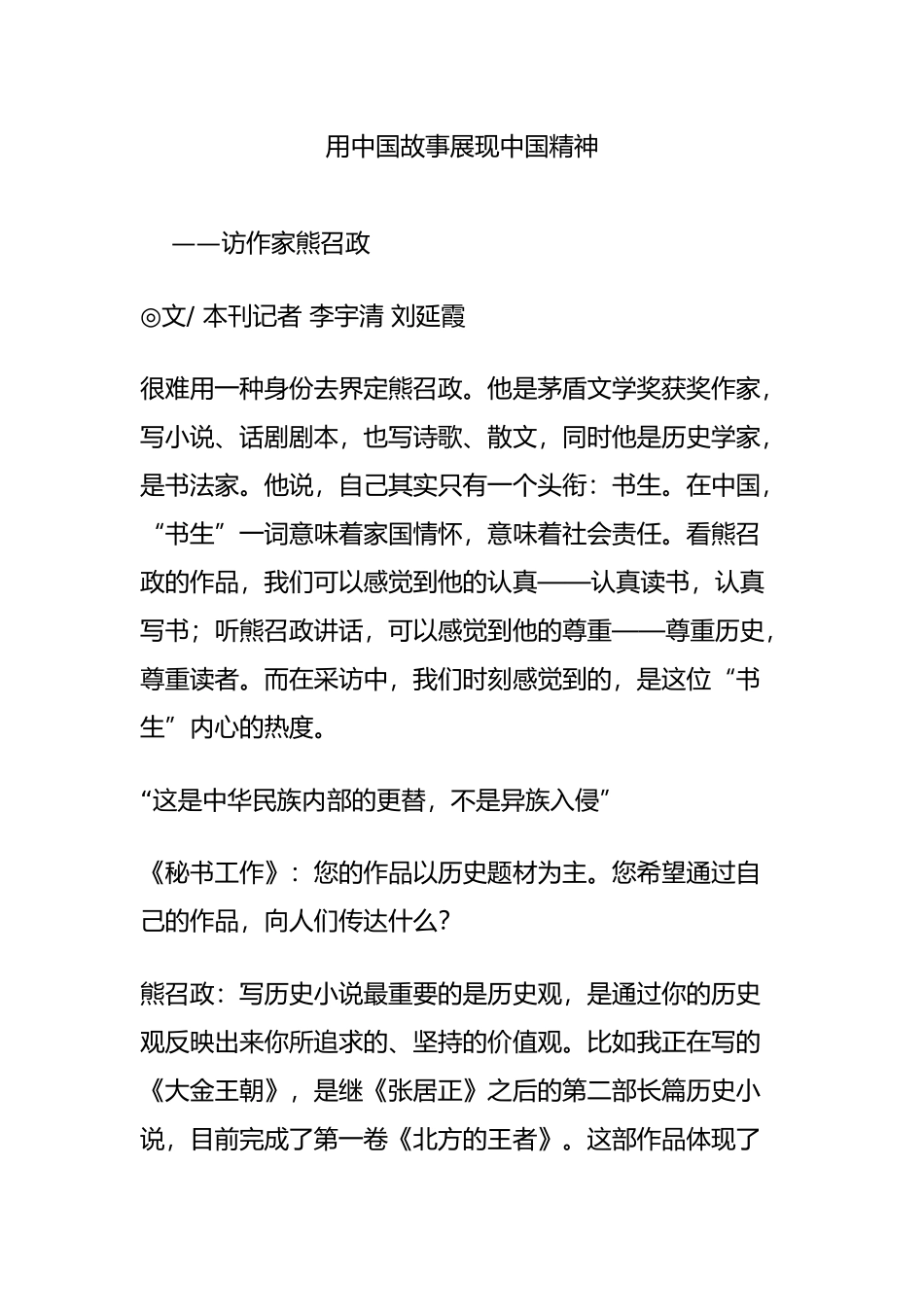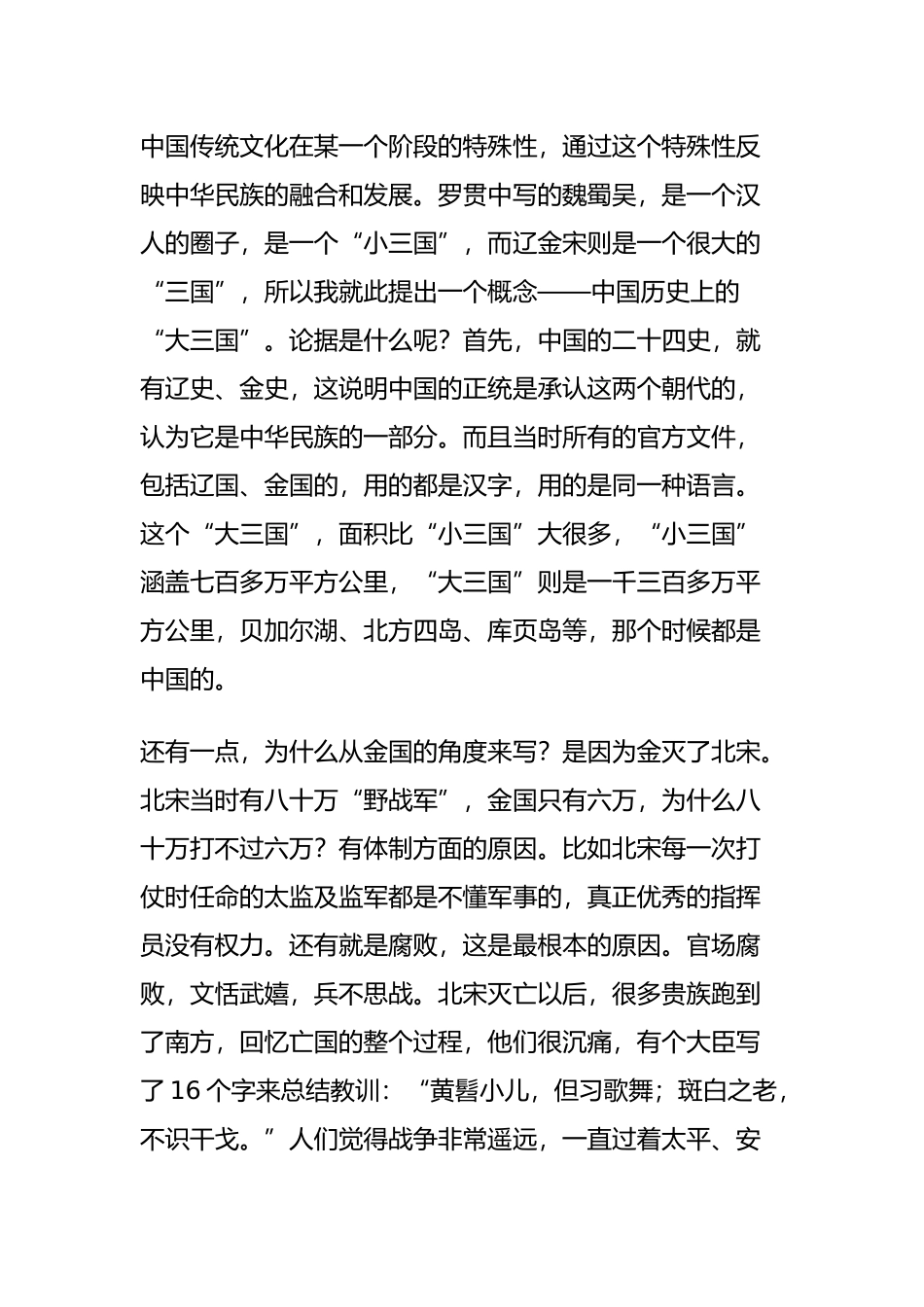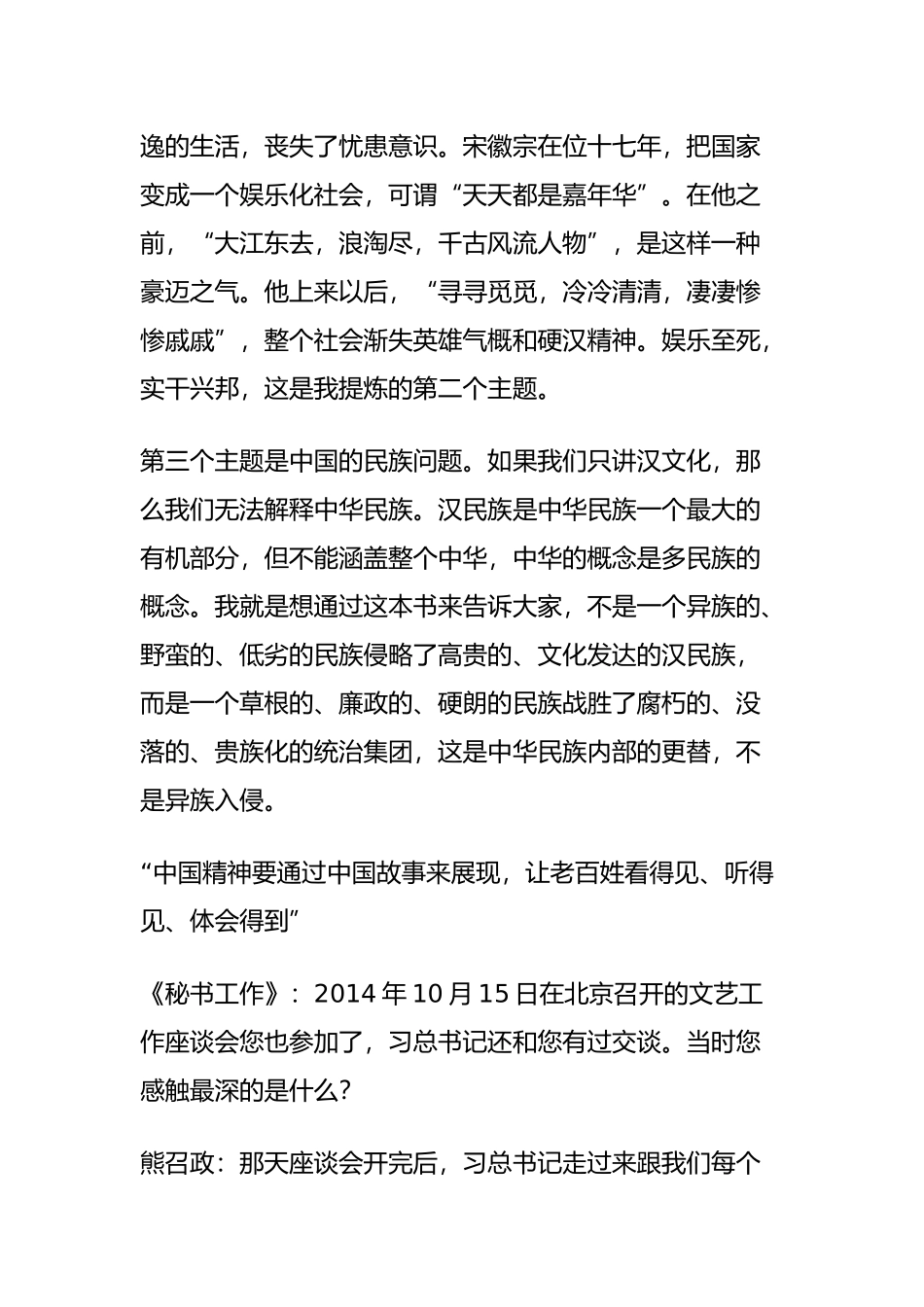用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访作家熊召政◎文/本刊记者李宇清刘延霞很难用一种身份去界定熊召政。他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写小说、话剧剧本,也写诗歌、散文,同时他是历史学家,是书法家。他说,自己其实只有一个头衔:书生。在中国,“书生”一词意味着家国情怀,意味着社会责任。看熊召政的作品,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认真——认真读书,认真写书;听熊召政讲话,可以感觉到他的尊重——尊重历史,尊重读者。而在采访中,我们时刻感觉到的,是这位“书生”内心的热度。“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更替,不是异族入侵”《秘书工作》:您的作品以历史题材为主。您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传达什么?熊召政:写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历史观,是通过你的历史观反映出来你所追求的、坚持的价值观。比如我正在写的《大金王朝》,是继《张居正》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目前完成了第一卷《北方的王者》。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一个阶段的特殊性,通过这个特殊性反映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罗贯中写的魏蜀吴,是一个汉人的圈子,是一个“小三国”,而辽金宋则是一个很大的“三国”,所以我就此提出一个概念——中国历史上的“大三国”。论据是什么呢?首先,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有辽史、金史,这说明中国的正统是承认这两个朝代的,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且当时所有的官方文件,包括辽国、金国的,用的都是汉字,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这个“大三国”,面积比“小三国”大很多,“小三国”涵盖七百多万平方公里,“大三国”则是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贝加尔湖、北方四岛、库页岛等,那个时候都是中国的。还有一点,为什么从金国的角度来写?是因为金灭了北宋。北宋当时有八十万“野战军”,金国只有六万,为什么八十万打不过六万?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比如北宋每一次打仗时任命的太监及监军都是不懂军事的,真正优秀的指挥员没有权力。还有就是腐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官场腐败,文恬武嬉,兵不思战。北宋灭亡以后,很多贵族跑到了南方,回忆亡国的整个过程,他们很沉痛,有个大臣写了16个字来总结教训:“黄髫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人们觉得战争非常遥远,一直过着太平、安逸的生活,丧失了忧患意识。宋徽宗在位十七年,把国家变成一个娱乐化社会,可谓“天天都是嘉年华”。在他之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这样一种豪迈之气。他上来以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整个社会渐失英雄气概和硬汉精神。娱乐至死,实干兴邦,这是我提炼的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我们只讲汉文化,那么我们无法解释中华民族。汉民族是中华民族一个最大的有机部分,但不能涵盖整个中华,中华的概念是多民族的概念。我就是想通过这本书来告诉大家,不是一个异族的、野蛮的、低劣的民族侵略了高贵的、文化发达的汉民族,而是一个草根的、廉政的、硬朗的民族战胜了腐朽的、没落的、贵族化的统治集团,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更替,不是异族入侵。“中国精神要通过中国故事来展现,让老百姓看得见、听得见、体会得到”《秘书工作》: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您也参加了,习总书记还和您有过交谈。当时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熊召政:那天座谈会开完后,习总书记走过来跟我们每个人握手。轮到我的时候,总书记说:“我知道你,《张居正》就是你写的。这书写得很好,我看完了。”会上总书记的讲话,最触动我的还是关于民族文化的追求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我想,中国故事既是五千年的故事,也是当下的故事;既是历史的故事,也是现实的故事。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怎样用一种唯物主义的健康的历史观、价值观来梳理我们的历史,让它对我们的国民、对我们的改革有借鉴和启示意义,需要去认真思考。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对某些现象作出了一些批评,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文艺创作有浮躁的问题,文艺不要当市场的奴隶,不要以洋为尊、以洋为美,等等。我想,中国精神要通过中国故事来展现,让老百姓看得见、听得见、体会得到,那么文学作品有不可忽视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