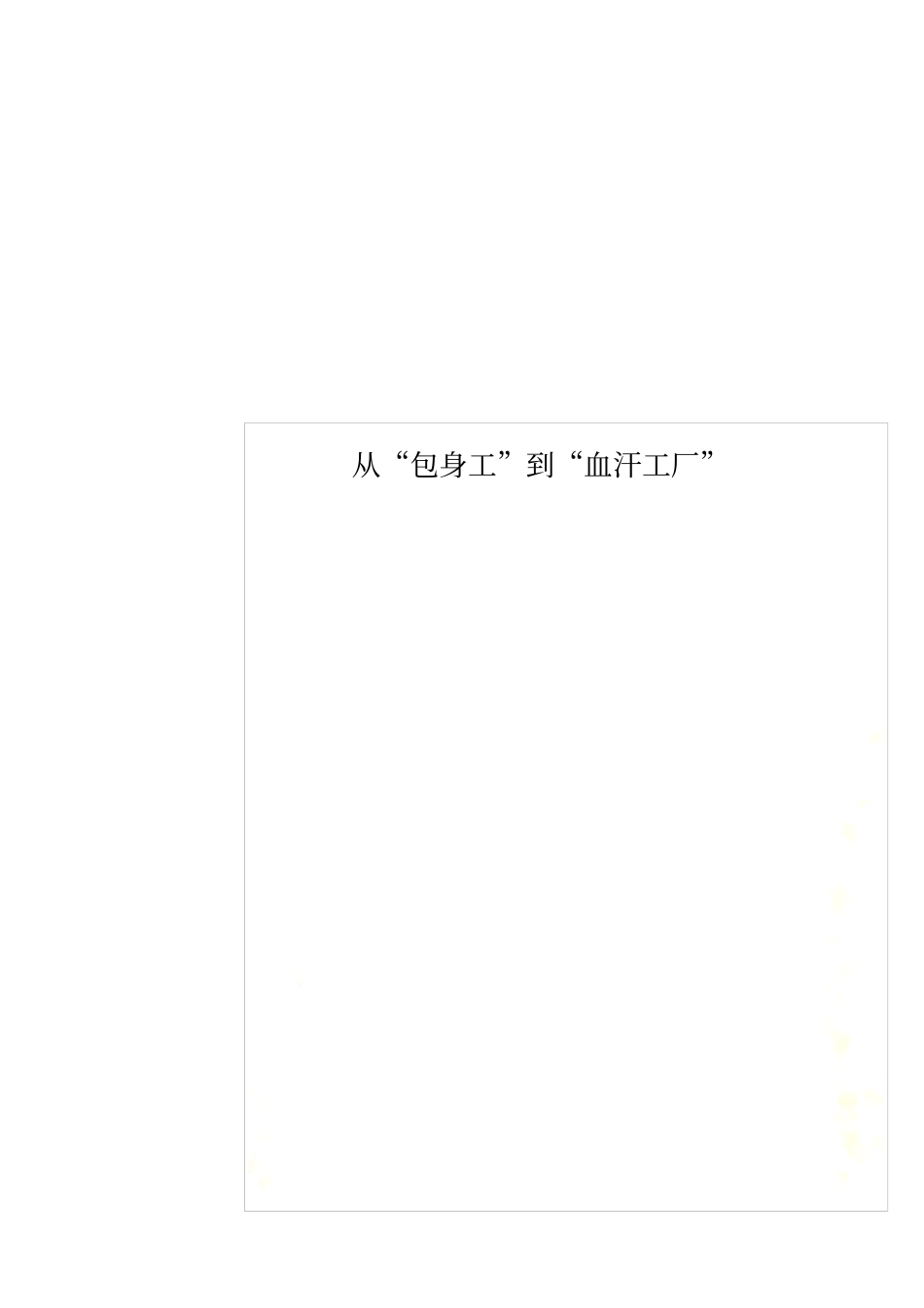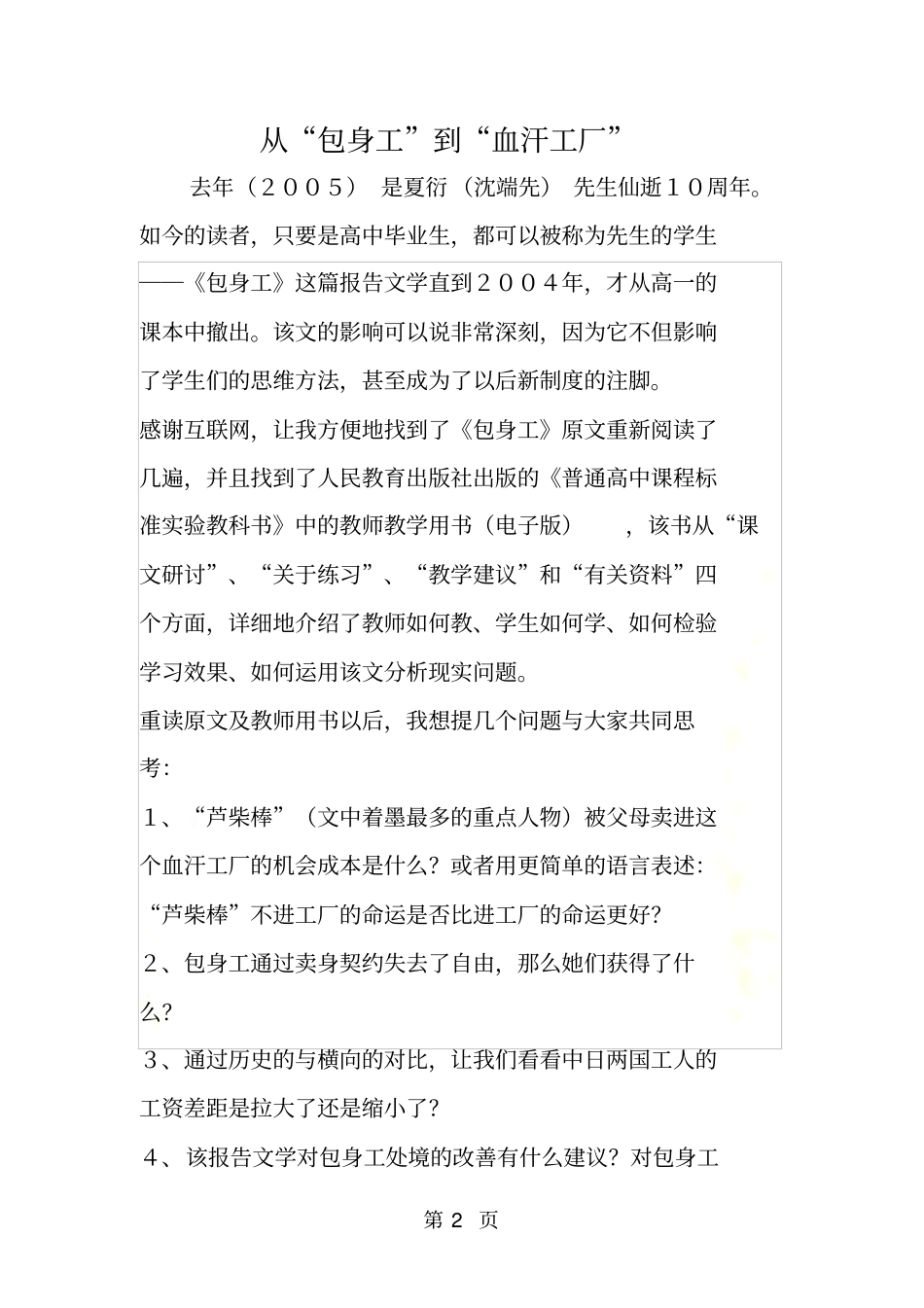从“包身工”到“血汗工厂”第2页从“包身工”到“血汗工厂”去年(2005)是夏衍(沈端先)先生仙逝10周年。如今的读者,只要是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被称为先生的学生──《包身工》这篇报告文学直到2004年,才从高一的课本中撤出。该文的影响可以说非常深刻,因为它不但影响了学生们的思维方法,甚至成为了以后新制度的注脚。感谢互联网,让我方便地找到了《包身工》原文重新阅读了几遍,并且找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的教师教学用书(电子版),该书从“课文研讨”、“关于练习”、“教学建议”和“有关资料”四个方面,详细地介绍了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如何检验学习效果、如何运用该文分析现实问题。重读原文及教师用书以后,我想提几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思考:1、“芦柴棒”(文中着墨最多的重点人物)被父母卖进这个血汗工厂的机会成本是什么?或者用更简单的语言表述:“芦柴棒”不进工厂的命运是否比进工厂的命运更好?2、包身工通过卖身契约失去了自由,那么她们获得了什么?3、通过历史的与横向的对比,让我们看看中日两国工人的工资差距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4、该报告文学对包身工处境的改善有什么建议?对包身工第4页包身工的工资到底有多低?夏衍先生在文中介绍说,“芦柴棒”作为生工,“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第一年的平均工钱是每天三角二分,第二年的平均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相当于每月10块大洋。这个“十块大洋”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看看1933年发表的叶圣陶先生在《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介绍就清楚了:对于粮食丰收的地区而言,“糙米五块,谷三块。”既十块大洋相当于在丰收地区的2担大米。她一年的收入相当于24担大米。毫无疑问,这种收入水平比她在农村从事农业,要高的多的多。问题在于,这个收入被“带工老板”买断了。包身工们通过卖身契约,获得的仅仅是一个从“生工”变成“熟工”的锻炼机会。其实她们还获得了三年后成为“自由工人”的机会和信息。从经济学上来说,该卖身契约对女工们的意义,实际上相当于上海需要招收女工的用工信息的成本。带工老板们掌握着这些信息,该信息如此昂贵,以至于包身工们为了获得它必须支付3年白干的代价。信息成本属于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越高,对达成交易的阻滞作用越大。但是,这种交易成本到底由谁支付,取决于第5页这种交易对谁更迫切。企业招收合意的员工面临的是利润的诱惑,包身工们获得该项工作机会面临的是延长生存的可能的诱惑。因此,该信息成本由包身工们支付而不是工厂支付,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种信息的利润水平如此之高,诱导了带工老板们鼓动他们“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在“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招来了“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其实推动上海由一个小渔村演变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东方巴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的地利──它在航运成为各国之间资源互补的纽带的条件下,上海成为中外各种资源进行交易和生产的中心。在整个产业链上,带工老板们扮演的是佣工信息的供应者角色。只要这种供应越短缺,那么这种信息就越值钱。道德谴责如果无助于改变这种信息短缺的状态,那么谴责也就无助于改善这些包身工的就业环境(包括吃、住、工作时间等)。可以推测,如果这种信息的利润水平能保持如此之高,那么,三年以后,将有不少包身工无须从事“自由工人”职业,而是从事“带工老板”的职业,从自己的家乡招收更多的女孩脱离农业,从事工业。我的意思是:利润水平的降低缘于竞争激烈,而不是缘于记者的道德谴责。到现在,通过分工的演化,“人才信息”已经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行业,而从事这一行业的资本却基本上只能获得平均的收益率。是这种行第6页业竞争而不是所谓的“记者的良心”才导致了信息价格的降低。我们再来看看中日两国工人的工资差距。夏衍先生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二者(两国的包身工)的差距是:“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