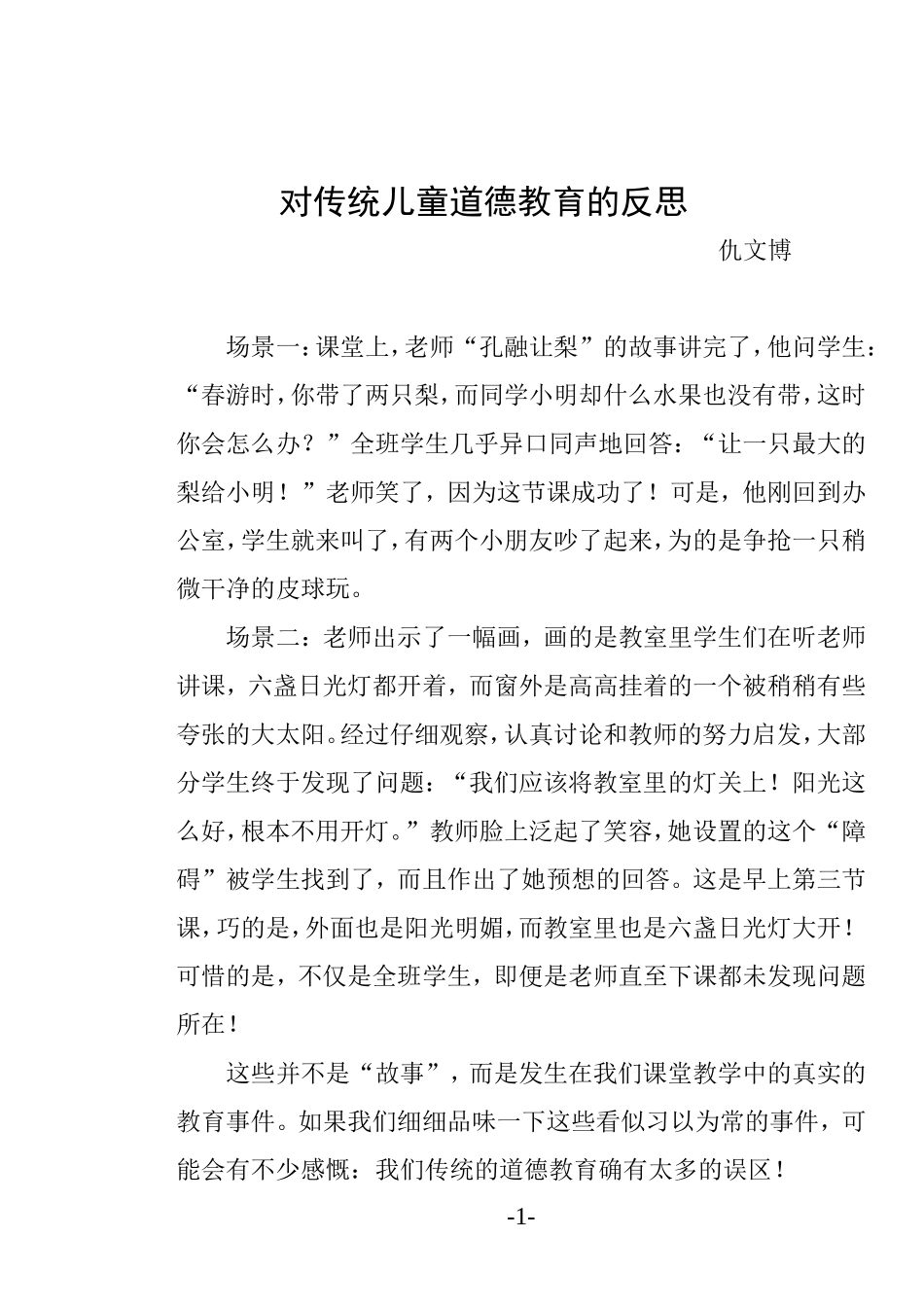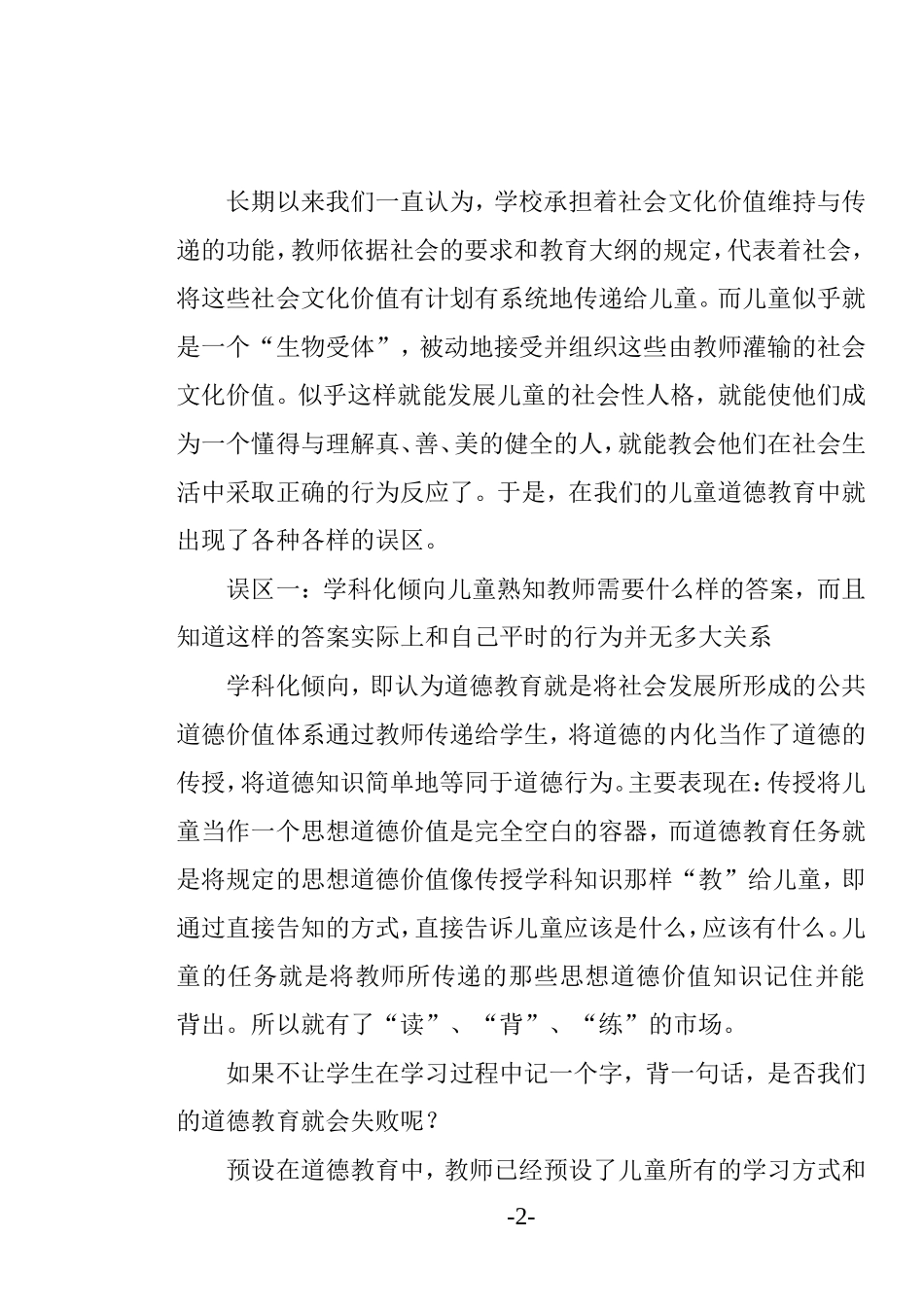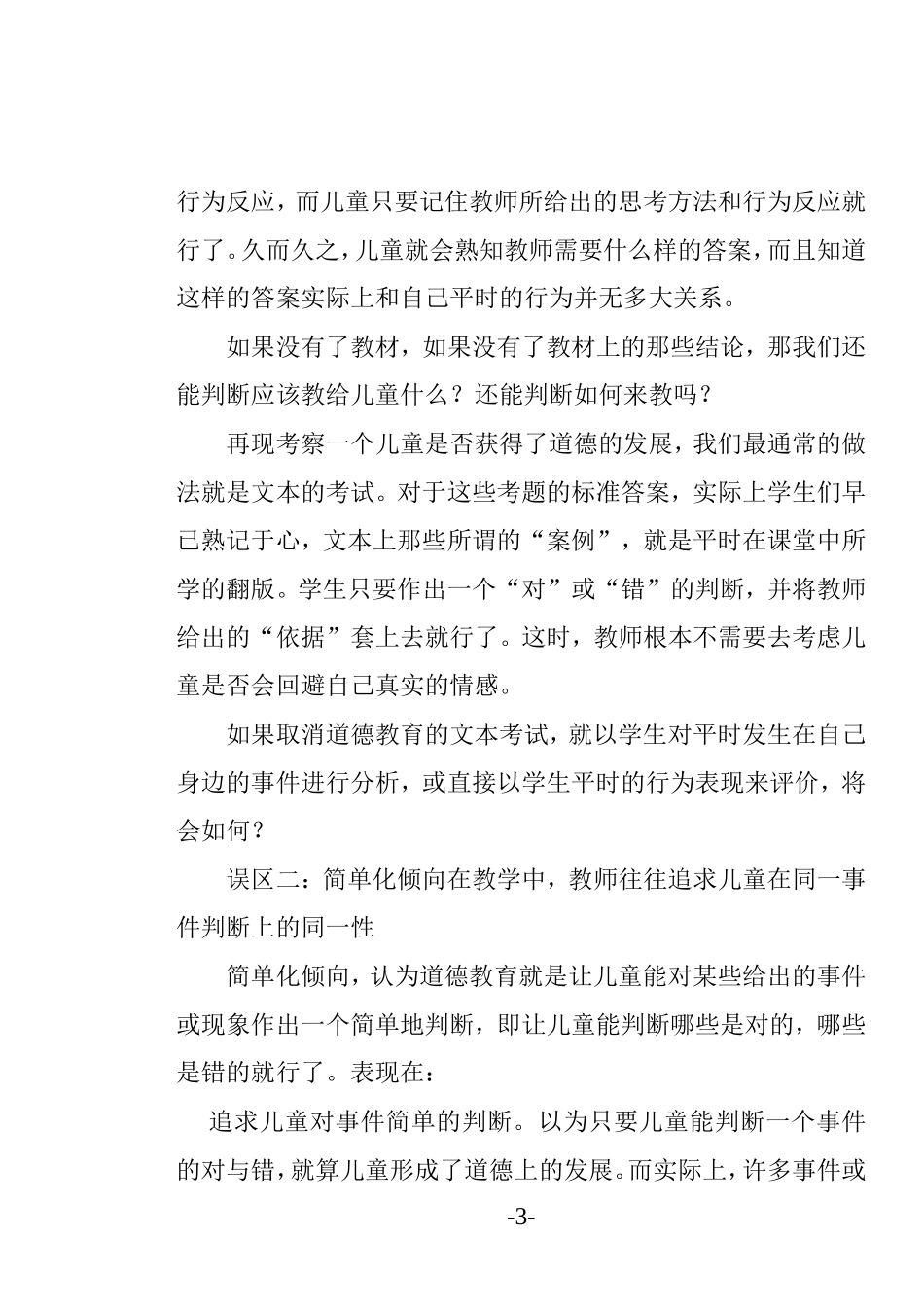对传统儿童道德教育的反思仇文博场景一:课堂上,老师“孔融让梨”的故事讲完了,他问学生:“春游时,你带了两只梨,而同学小明却什么水果也没有带,这时你会怎么办?”全班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让一只最大的梨给小明!”老师笑了,因为这节课成功了!可是,他刚回到办公室,学生就来叫了,有两个小朋友吵了起来,为的是争抢一只稍微干净的皮球玩。场景二:老师出示了一幅画,画的是教室里学生们在听老师讲课,六盏日光灯都开着,而窗外是高高挂着的一个被稍稍有些夸张的大太阳。经过仔细观察,认真讨论和教师的努力启发,大部分学生终于发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将教室里的灯关上!阳光这么好,根本不用开灯。”教师脸上泛起了笑容,她设置的这个“障碍”被学生找到了,而且作出了她预想的回答。这是早上第三节课,巧的是,外面也是阳光明媚,而教室里也是六盏日光灯大开!可惜的是,不仅是全班学生,即便是老师直至下课都未发现问题所在!这些并不是“故事”,而是发生在我们课堂教学中的真实的教育事件。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一下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事件,可能会有不少感慨:我们传统的道德教育确有太多的误区!-1-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学校承担着社会文化价值维持与传递的功能,教师依据社会的要求和教育大纲的规定,代表着社会,将这些社会文化价值有计划有系统地传递给儿童。而儿童似乎就是一个“生物受体”,被动地接受并组织这些由教师灌输的社会文化价值。似乎这样就能发展儿童的社会性人格,就能使他们成为一个懂得与理解真、善、美的健全的人,就能教会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采取正确的行为反应了。于是,在我们的儿童道德教育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误区。误区一:学科化倾向儿童熟知教师需要什么样的答案,而且知道这样的答案实际上和自己平时的行为并无多大关系学科化倾向,即认为道德教育就是将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公共道德价值体系通过教师传递给学生,将道德的内化当作了道德的传授,将道德知识简单地等同于道德行为。主要表现在:传授将儿童当作一个思想道德价值是完全空白的容器,而道德教育任务就是将规定的思想道德价值像传授学科知识那样“教”给儿童,即通过直接告知的方式,直接告诉儿童应该是什么,应该有什么。儿童的任务就是将教师所传递的那些思想道德价值知识记住并能背出。所以就有了“读”、“背”、“练”的市场。如果不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记一个字,背一句话,是否我们的道德教育就会失败呢?预设在道德教育中,教师已经预设了儿童所有的学习方式和-2-行为反应,而儿童只要记住教师所给出的思考方法和行为反应就行了。久而久之,儿童就会熟知教师需要什么样的答案,而且知道这样的答案实际上和自己平时的行为并无多大关系。如果没有了教材,如果没有了教材上的那些结论,那我们还能判断应该教给儿童什么?还能判断如何来教吗?再现考察一个儿童是否获得了道德的发展,我们最通常的做法就是文本的考试。对于这些考题的标准答案,实际上学生们早已熟记于心,文本上那些所谓的“案例”,就是平时在课堂中所学的翻版。学生只要作出一个“对”或“错”的判断,并将教师给出的“依据”套上去就行了。这时,教师根本不需要去考虑儿童是否会回避自己真实的情感。如果取消道德教育的文本考试,就以学生对平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件进行分析,或直接以学生平时的行为表现来评价,将会如何?误区二:简单化倾向在教学中,教师往往追求儿童在同一事件判断上的同一性简单化倾向,认为道德教育就是让儿童能对某些给出的事件或现象作出一个简单地判断,即让儿童能判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就行了。表现在:追求儿童对事件简单的判断。以为只要儿童能判断一个事件的对与错,就算儿童形成了道德上的发展。而实际上,许多事件或-3-现象是不能简单地以对或错来作判断的,它包含着每一个人对道德的理解和对行为的解释。果我们要求儿童对某一事件不是作出一种简单的“对”与“错”的判断,而是要作出一种解释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不是对教师给出的事件,而是对自己的某一行为作出解释时,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追求答案的求同。对道德教育的片面理解,造成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