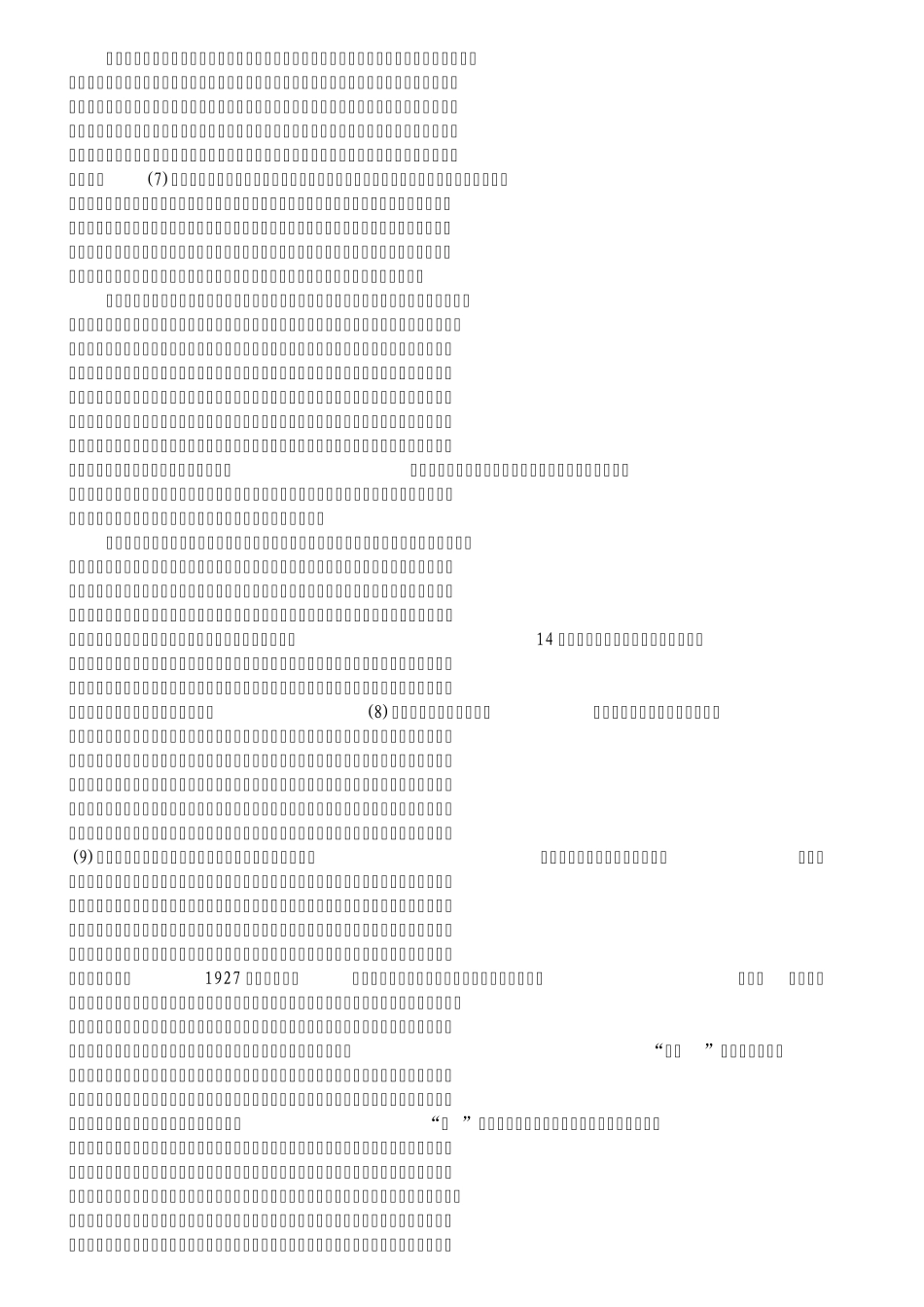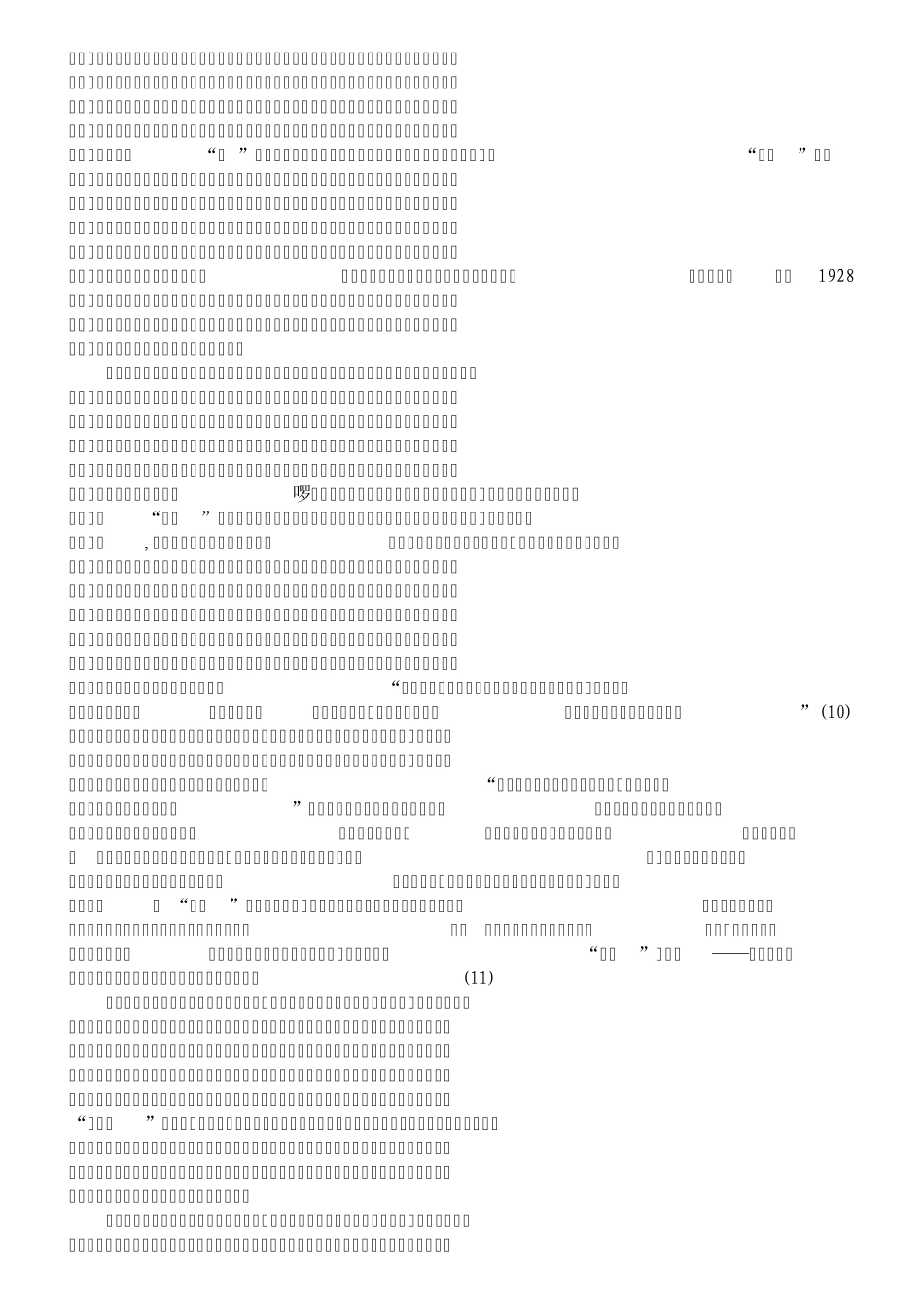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 ——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 当三十年代第一次有人称沈从文是“文体家”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暗暗地感到骄傲。他初到北京的时候连标点符号都不大会用,现在却能在文句组合上形成一种显著的特色,这是怎样迅速的进步?何况文体并不单是指一种特别的文句格式,甚至也主要不是指孕育这格式的一种特别的叙述结构:在我看来。说一个小说家创造了自己的文体,那更是指他对自己的情感记忆有了一种特别的把握。不用说,作家的这种自我把握首先是一种语言的把握,就是借助既定的语言系统去澄清那些飘忽膝陇的印象。因此,在这澄清的过程当中,对对象的把握是和这对象本身一同产生的,你甚至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这就使作家的自我把握具有厂一种双重性,它既是理智的认知,更是情感的创造。正是这种双重性决定了“文体”这个词的复杂涵义,套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来说,它不但是指一种形式,更首先是指一种内容:一个小说家能够用别人尚未试过的方式来讲故事,总是因为他已经想好了一个别人从没听过的故事。沈从文当然有理由暗自骄傲。 但我要说的是,这种骄傲是很不容易维持的。惟其出身于作家对世界的那种微妙的审美把握,文体就像是一位极端任性的公主,她要求作家对她绝对忠诚。倘若你稍有疏忽,譬如在狂热地迷醉于她的风采之后,你可能会稍稍变得迟钝,对她的某些暗示缺乏反应;或者在依旧钟情于她的同时,你可能会身不由己地对其他动人的景象也发生兴趣;甚至你仅仅是因为长时间的侍奉而感到疲劳,不知不觉就把追随的脚步放慢了一点„„她都会变了脸色拂袖而去,立刻收回她生前恩赐给你的宠幸。在我看来,这就是文体家的真实处境,能够赢得文体的青睐已属不易,要想保住这份殊荣就更加艰难。 我不禁对沈从文作为文体家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真有资格分享文体家的骄傲吗?他是如何争取到这个资格的?如果说他确曾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体,他又能在多大的程度上继续发展它?倘若他竟然做不到这一点,很快就失去了文体的青睐,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在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沈从文的笔法是相当杂乱的。他时而以一种独白的方式,诉说自己如何如何地穷愁潦倒,那文字的散漫和拖沓,似乎和郁达夫颇为相像。(1)时而又摆出一副旁观者的姿态,平静地描述绅士老爷和大学生们的丑态,那种对戏剧性场面的由衷的爱好,特别是那些漫画式的夸张描写,都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张天翼。(2)在更多的时候,他又学着一个不满十岁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