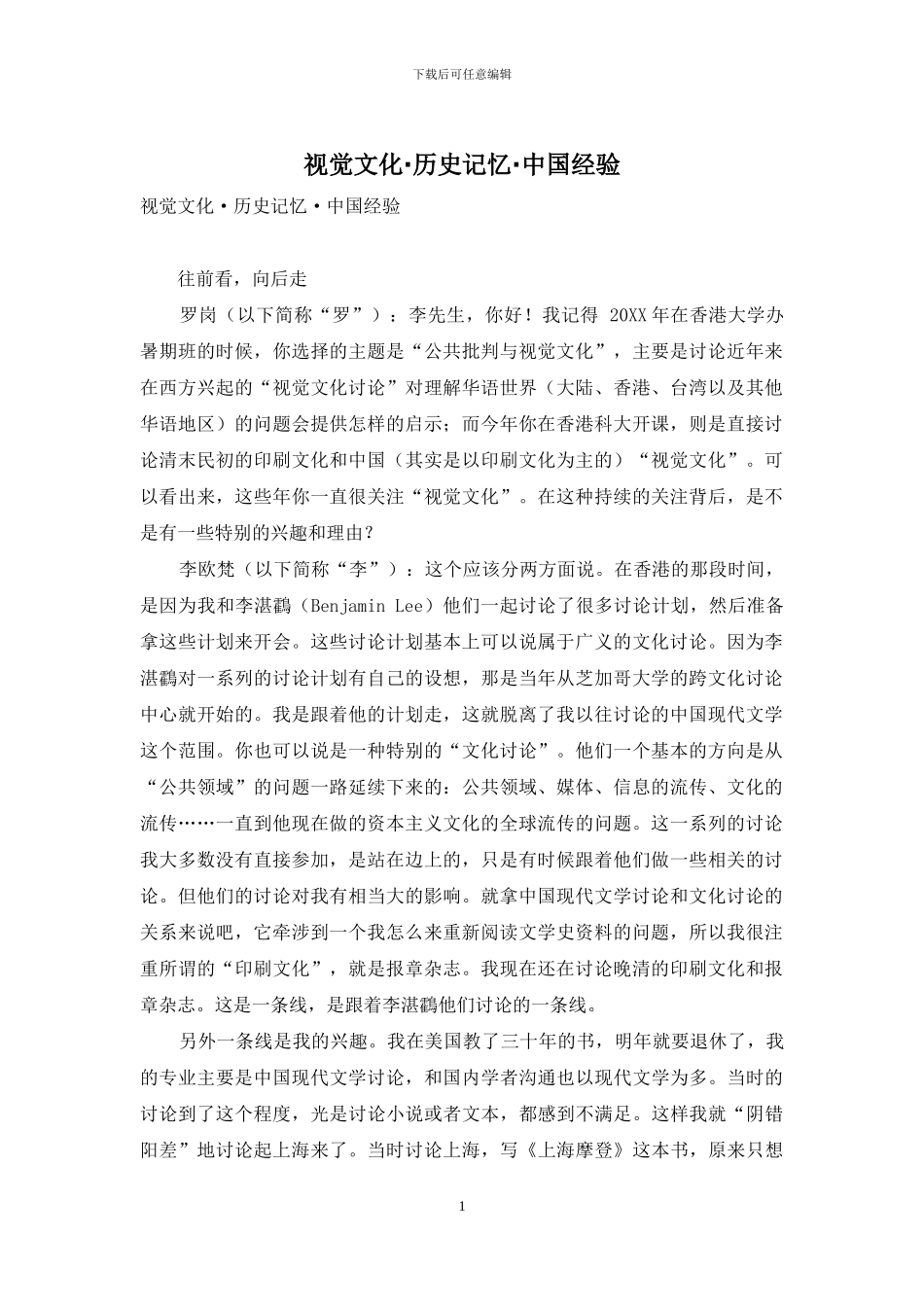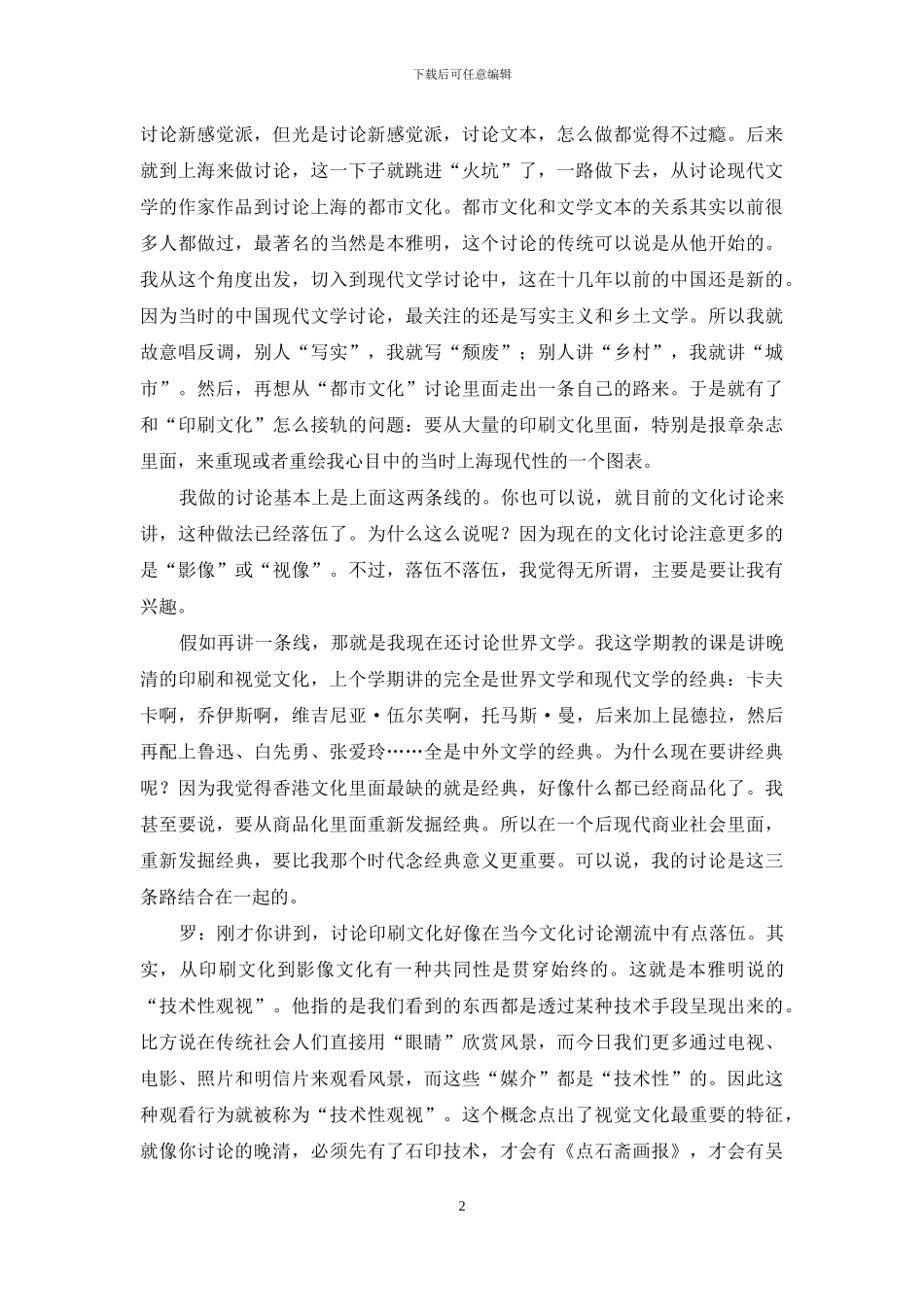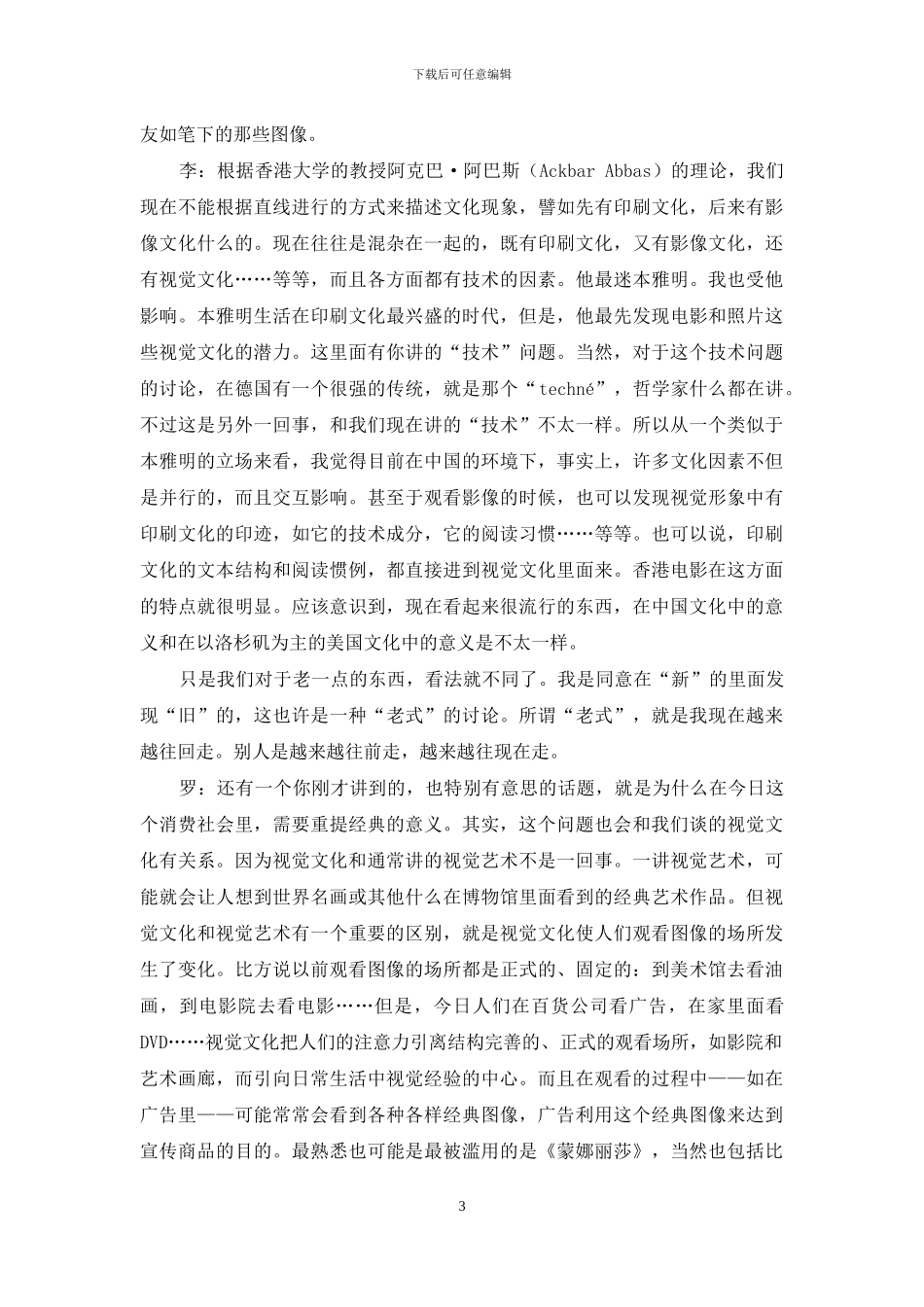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 往前看,向后走 罗岗(以下简称“罗”):李先生,你好!我记得 20XX 年在香港大学办暑期班的时候,你选择的主题是“公共批判与视觉文化”,主要是讨论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视觉文化讨论”对理解华语世界(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其他华语地区)的问题会提供怎样的启示;而今年你在香港科大开课,则是直接讨论清末民初的印刷文化和中国(其实是以印刷文化为主的)“视觉文化”。可以看出来,这些年你一直很关注“视觉文化”。在这种持续的关注背后,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兴趣和理由? 李欧梵(以下简称“李”):这个应该分两方面说。在香港的那段时间,是因为我和李湛鸖(Benjamin Lee)他们一起讨论了很多讨论计划,然后准备拿这些计划来开会。这些讨论计划基本上可以说属于广义的文化讨论。因为李湛鸖对一系列的讨论计划有自己的设想,那是当年从芝加哥大学的跨文化讨论中心就开始的。我是跟着他的计划走,这就脱离了我以往讨论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个范围。你也可以说是一种特别的“文化讨论”。他们一个基本的方向是从“公共领域”的问题一路延续下来的:公共领域、媒体、信息的流传、文化的流传……一直到他现在做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流传的问题。这一系列的讨论我大多数没有直接参加,是站在边上的,只是有时候跟着他们做一些相关的讨论。但他们的讨论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就拿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和文化讨论的关系来说吧,它牵涉到一个我怎么来重新阅读文学史资料的问题,所以我很注重所谓的“印刷文化”,就是报章杂志。我现在还在讨论晚清的印刷文化和报章杂志。这是一条线,是跟着李湛鸖他们讨论的一条线。 另外一条线是我的兴趣。我在美国教了三十年的书,明年就要退休了,我的专业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和国内学者沟通也以现代文学为多。当时的讨论到了这个程度,光是讨论小说或者文本,都感到不满足。这样我就“阴错阳差”地讨论起上海来了。当时讨论上海,写《上海摩登》这本书,原来只想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讨论新感觉派,但光是讨论新感觉派,讨论文本,怎么做都觉得不过瘾。后来就到上海来做讨论,这一下子就跳进“火坑”了,一路做下去,从讨论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到讨论上海的都市文化。都市文化和文学文本的关系其实以前很多人都做过,最著名的当然是本雅明,这个讨论的传统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我从这个角度出发,切入到现代文学讨论中,这在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