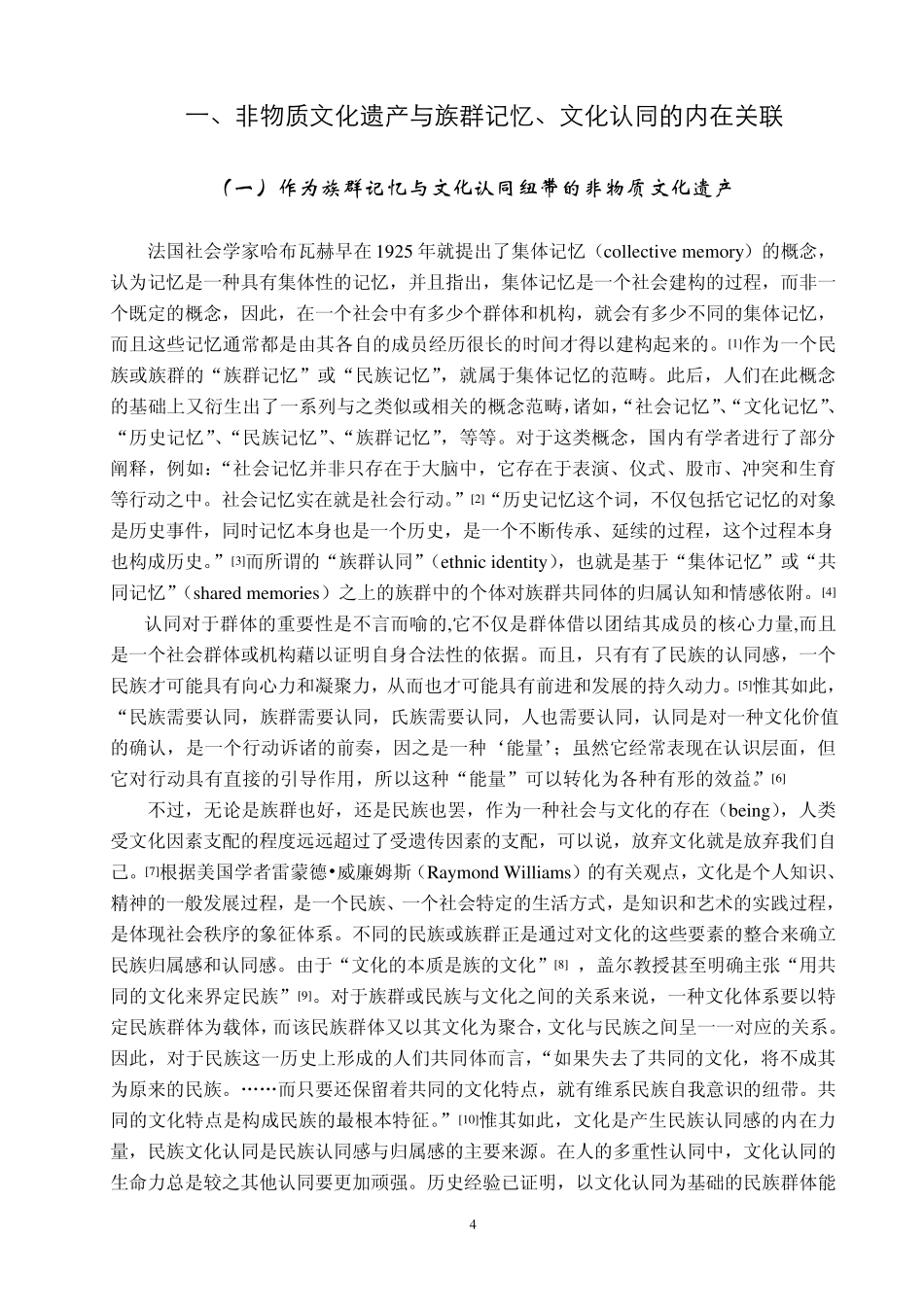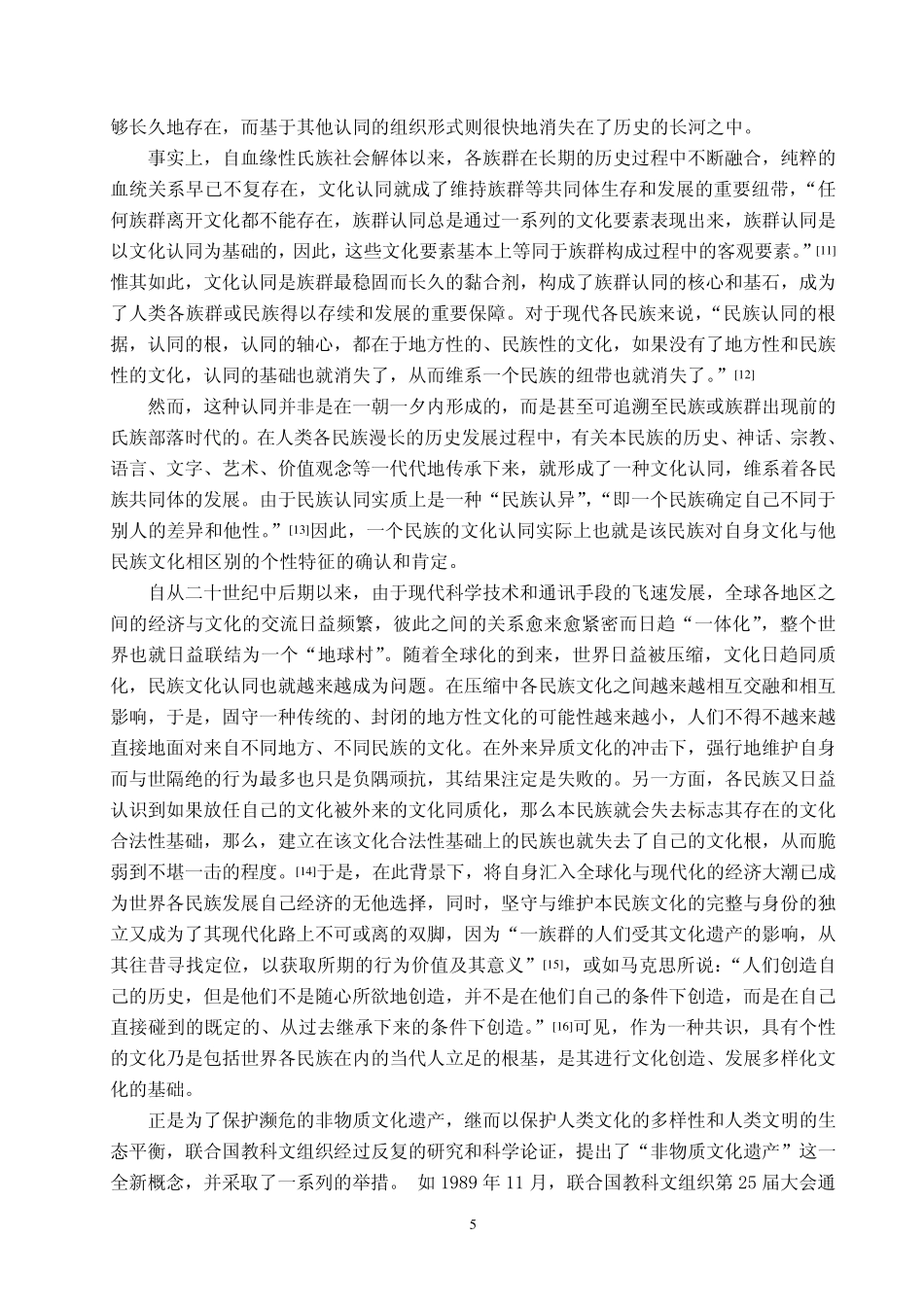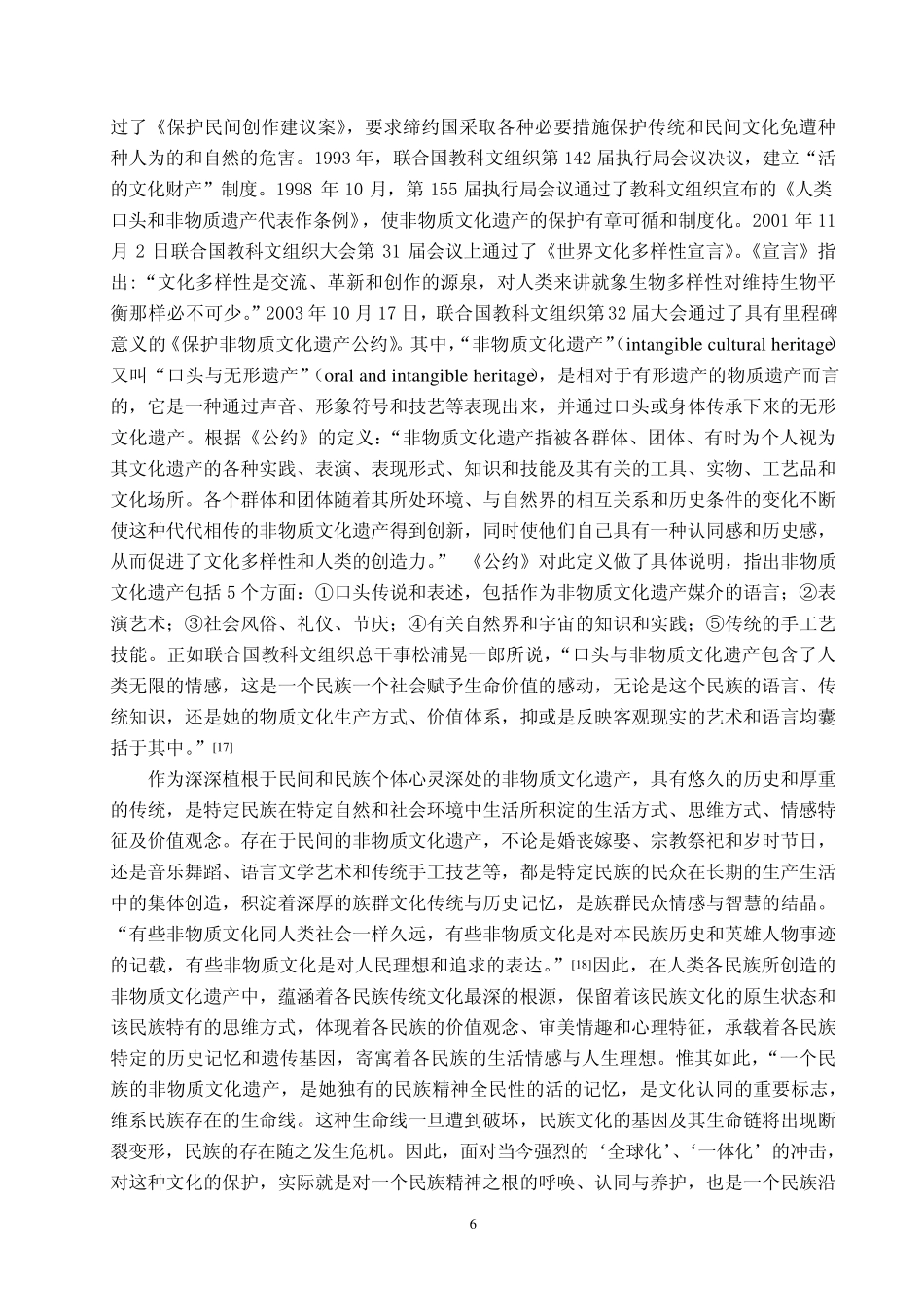4一 、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与 族 群 记 忆 、 文 化 认 同 的 内 在 关 联 ( 一 ) 作 为 族 群 记 忆 与 文 化 认 同 纽 带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早在 1925 年就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 e memory)的概念,认为记忆是一种具有集体性的记忆,并且指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而非一个既定的概念,因此,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个群体和机构,就会有多少不同的集体记忆,而且这些记忆通常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员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得以建构起来的。[1]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族群记忆”或“民族记忆”,就属于集体记忆的范畴。此后,人们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一系列与之类似或相关的概念范畴,诸如,“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民族记忆”、“族群记忆”,等等。对于这类概念,国内有学者进行了部分阐释,例如:“社会记忆并非只存在于大脑中,它存在于表演、仪式、股市、冲突和生育等行动之中。社会记忆实在就是社会行动。”[2]“历史记忆这个词,不仅包括它记忆的对象是历史事件,同时记忆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构成历史。”[3]而所谓的“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 ),也就是基于“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shared memories)之上的族群中的个体对族群共同体的归属认知和情感依附。[4] 认同对于群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是群体借以团结其成员的核心力量,而且是一个社会群体或机构藉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依据。而且,只有有了民族的认同感,一个民族才可能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也才可能具有前进和发展的持久动力。[5]惟其如此,“民族需要认同,族群需要认同,氏族需要认同,人也需要认同,认同是对一种文化价值的确认,是一个行动诉诸的前奏,因之是一种‘能量’;虽然它经常表现在认识层面,但它对行动具有直接的引导作用,所以这种“能量”可以转化为各种有形的效益。”[6] 不过,无论是族群也好,还是民族也罢,作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存在(being),人类受文化因素支配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受遗传因素的支配,可以说,放弃文化就是放弃我们自己。[7]根据美国学者雷蒙德•威 廉 姆 斯 (Ray mond Williams)的有关观 点 ,文化是个人知识、精 神 的一般 发展过程,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特 定的生活 方 式,是知识和艺 术 的实践 过程,是体现社会秩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