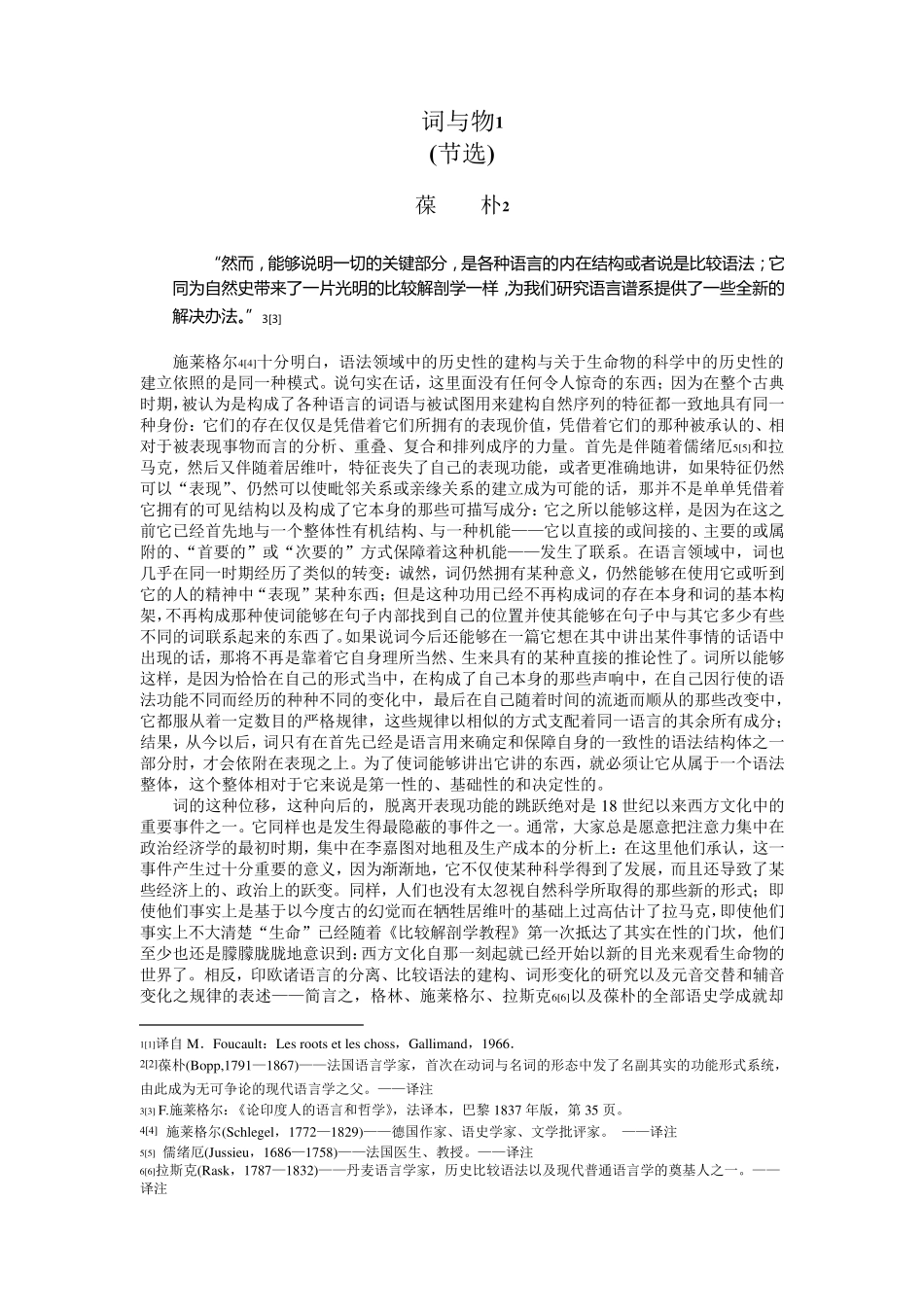词与物1 (节选) 葆 朴2 “然而,能够说明一切的关键部分,是各种语言的内在结构或者说是比较语法;它同为自然史带来了一片光明的比较解剖学一样,为我们研究语言谱系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解决办法。”3[3] 施莱格尔4[4]十分明白,语法领域中的历史性的建构与关于生命物的科学中的历史性的建立依照的是同一种模式。说句实在话,这里面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东西;因为在整个古典时期,被认为是构成了各种语言的词语与被试图用来建构自然序列的特征都一致地具有同一种身份:它们的存在仅仅是凭借着它们所拥有的表现价值,凭借着它们的那种被承认的、相对于被表现事物而言的分析、重叠、复合和排列成序的力量。首先是伴随着儒绪厄5[5]和拉马克,然后又伴随着居维叶,特征丧失了自己的表现功能,或者更准确地讲,如果特征仍然可以“表现”、仍然可以使毗邻关系或亲缘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的话,那并不是单单凭借着它拥有的可见结构以及构成了它本身的那些可描写成分:它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这之前它已经首先地与一个整体性有机结构、与一种机能——它以直接的或间接的、主要的或属附的、“首要的”或“次要的”方式保障着这种机能——发生了联系。在语言领域中,词也几乎在同一时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诚然,词仍然拥有某种意义,仍然能够在使用它或听到它的人的精神中“表现”某种东西;但是这种功用已经不再构成词的存在本身和词的基本构架,不再构成那种使词能够在句子内部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使其能够在句子中与其它多少有些不同的词联系起来的东西了。如果说词今后还能够在一篇它想在其中讲出某件事情的话语中出现的话,那将不再是靠着它自身理所当然、生来具有的某种直接的推论性了。词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恰恰在自己的形式当中,在构成了自己本身的那些声响中,在自己因行使的语法功能不同而经历的种种不同的变化中,最后在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顺从的那些改变中,它都服从着一定数目的严格规律,这些规律以相似的方式支配着同一语言的其余所有成分;结果,从今以后,词只有在首先已经是语言用来确定和保障自身的一致性的语法结构体之一部分肘,才会依附在表现之上。为了使词能够讲出它讲的东西,就必须让它从属于一个语法整体,这个整体相对于它来说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 词的这种位移,这种向后的,脱离开表现功能的跳跃绝对是 18 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它同样也是发生得最隐蔽的事件之一。通常,大家总是愿意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