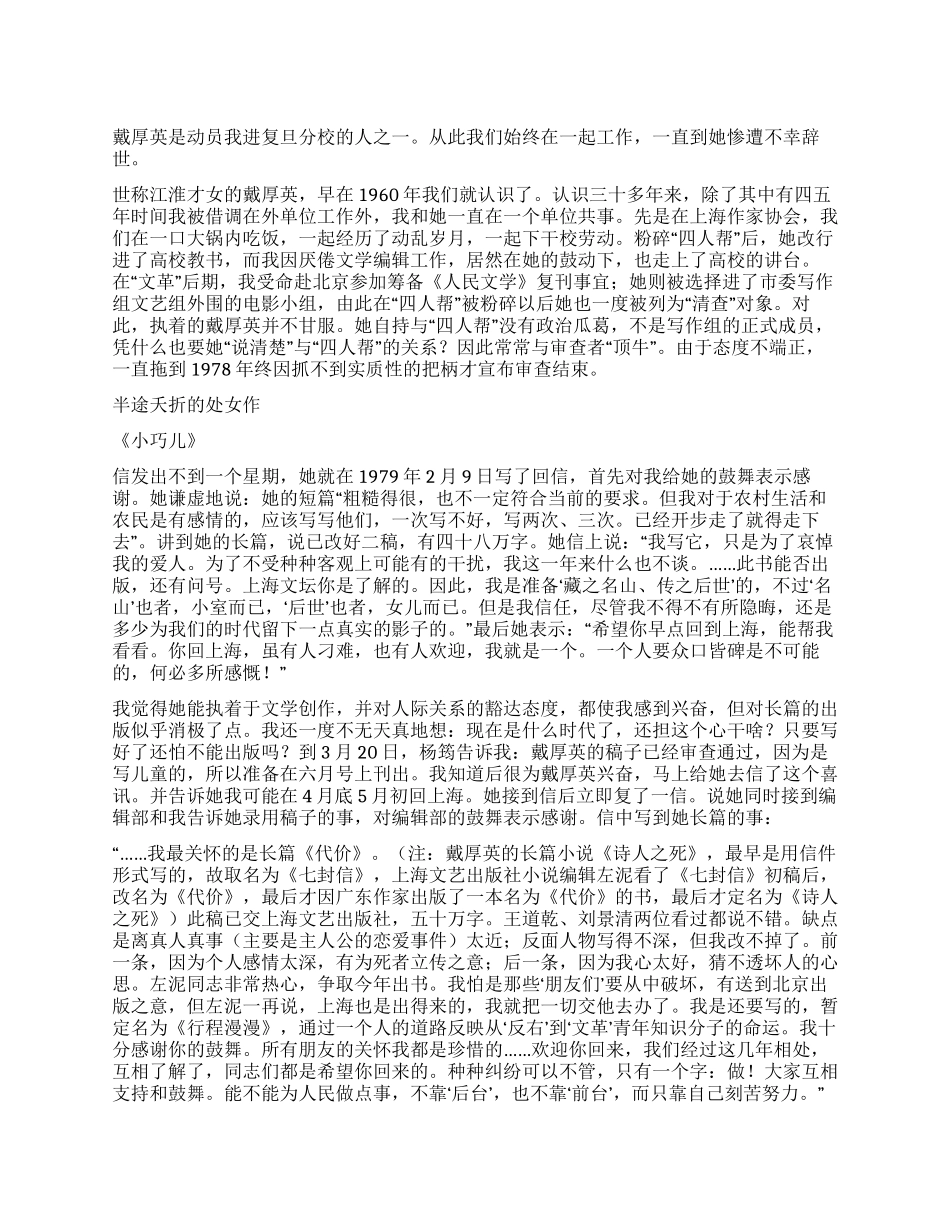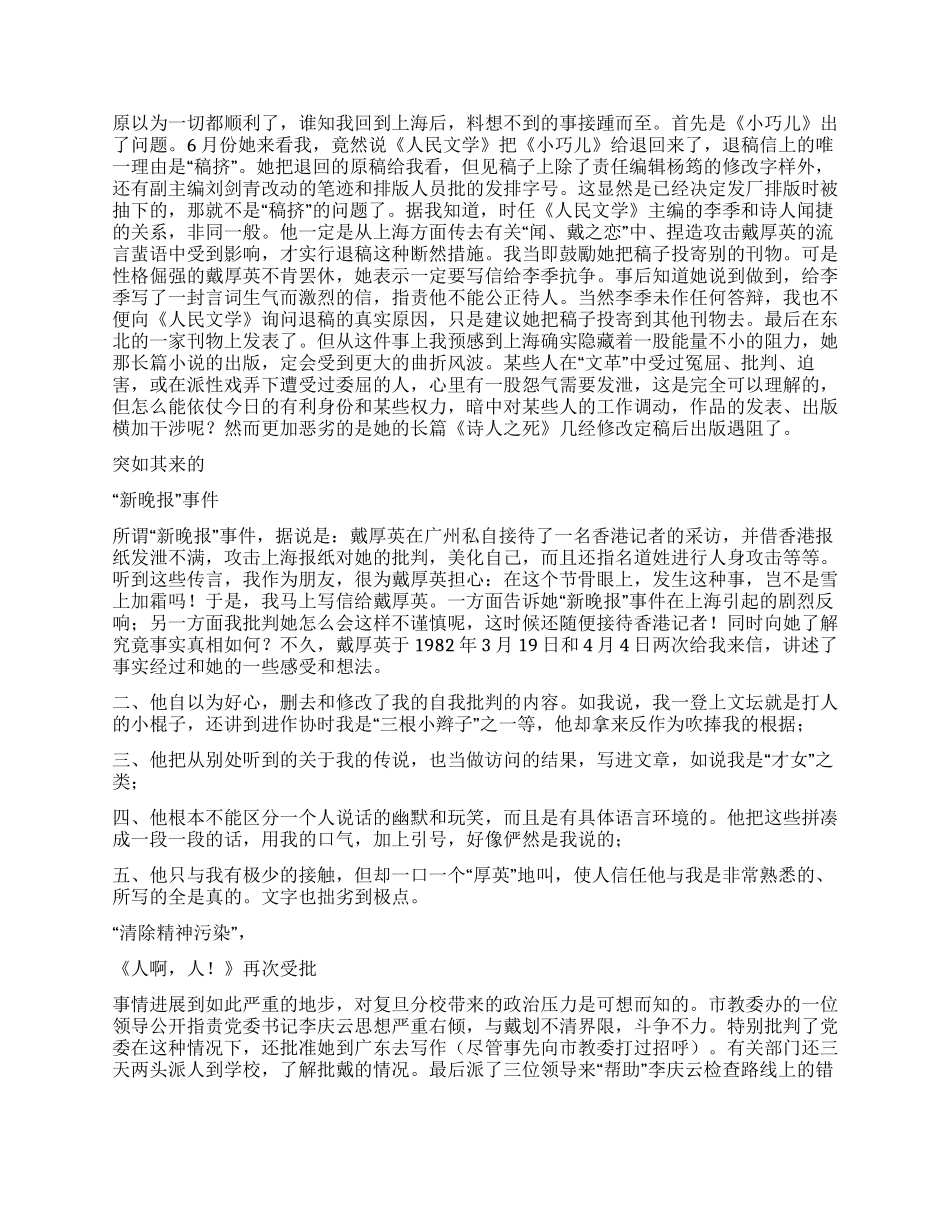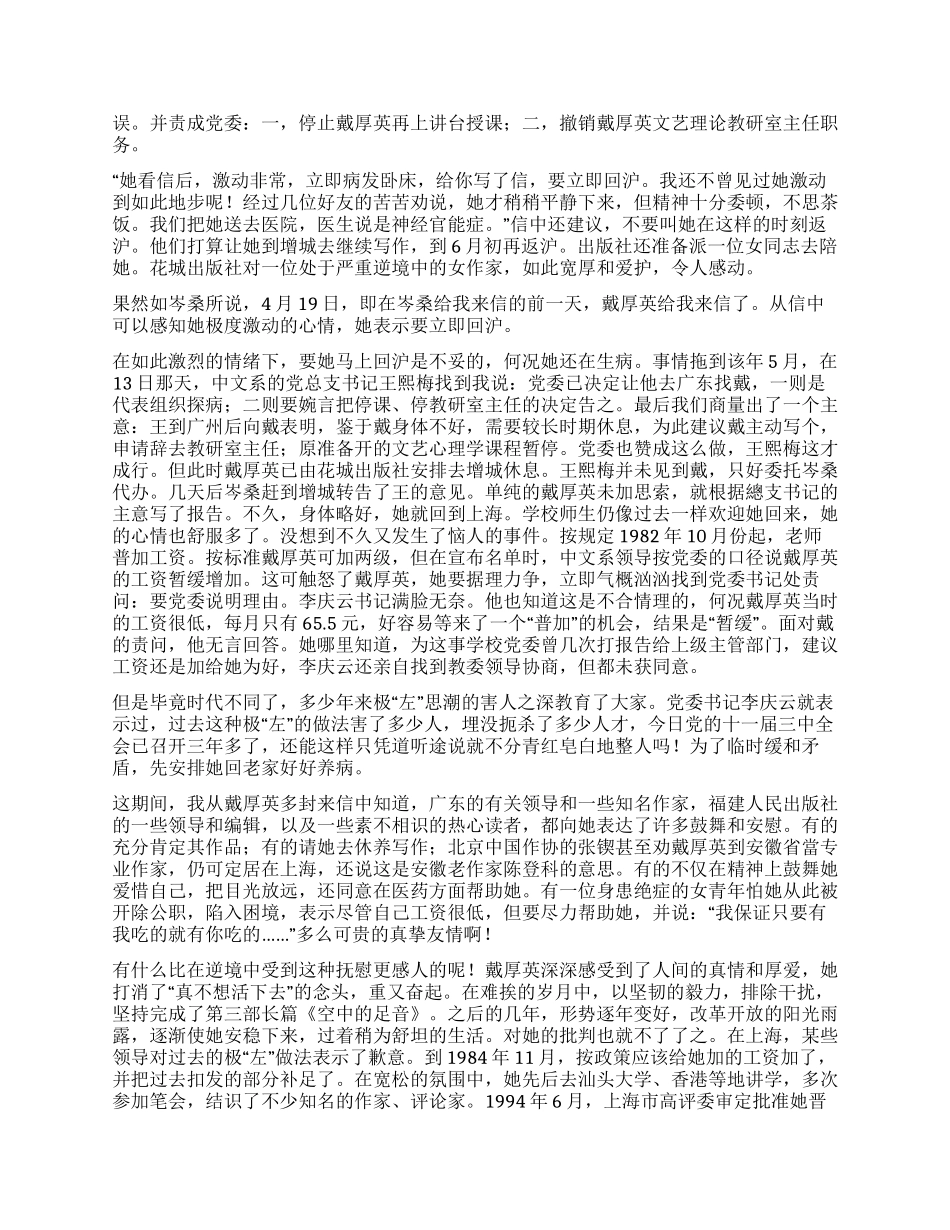戴厚英是动员我进复旦分校的人之一。从此我们始终在一起工作,一直到她惨遭不幸辞世。世称江淮才女的戴厚英,早在 1960 年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三十多年来,除了其中有四五年时间我被借调在外单位工作外,我和她一直在一个单位共事。先是在上海作家协会,我“”们在一口大锅内吃饭,一起经历了动乱岁月,一起下干校劳动。粉碎 四人帮 后,她改行进了高校教书,而我因厌倦文学编辑工作,居然在她的鼓动下,也走上了高校的讲台。“”在 文革 后期,我受命赴北京参加筹备《人民文学》复刊事宜;她则被选择进了市委写作“”“”组文艺组外围的电影小组,由此在 四人帮 被粉碎以后她也一度被列为 清查 对象。对“”此,执着的戴厚英并不甘服。她自持与 四人帮 没有政治瓜葛,不是写作组的正式成员,“”“”“”凭什么也要她 说清楚 与 四人帮 的关系?因此常常与审查者 顶牛 。由于态度不端正,一直拖到 1978 年终因抓不到实质性的把柄才宣布审查结束。半途夭折的处女作《小巧儿》信发出不到一个星期,她就在 1979 年 2 月 9 日写了回信,首先对我给她的鼓舞表示感“谢。她谦虚地说:她的短篇 粗糙得很,也不一定符合当前的要求。但我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是有感情的,应该写写他们,一次写不好,写两次、三次。已经开步走了就得走下”“去 。讲到她的长篇,说已改好二稿,有四十八万字。她信上说: 我写它,只是为了哀悼……我的爱人。为了不受种种客观上可能有的干扰,我这一年来什么也不谈。此书能否出‘’‘版,还有问号。上海文坛你是了解的。因此,我是准备 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的,不过 名’‘’山 也者,小室而已, 后世 也者,女儿而已。但是我信任,尽管我不得不有所隐晦,还是”“多少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一点真实的影子的。 最后她表示: 希望你早点回到上海,能帮我看看。你回上海,虽有人刁难,也有人欢迎,我就是一个。一个人要众口皆碑是不可能”的,何必多所感慨!我觉得她能执着于文学创作,并对人际关系的豁达态度,都使我感到兴奋,但对长篇的出版似乎消极了点。我还一度不无天真地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担这个心干啥?只要写好了还怕不能出版吗?到 3 月 20 日,杨筠告诉我:戴厚英的稿子已经审查通过,因为是写儿童的,所以准备在六月号上刊出。我知道后很为戴厚英兴奋,马上给她去信了这个喜讯。并告诉她我可能在 4 月底 5 月初回上海。她接到信后立即复了一信。说她同时接到编辑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