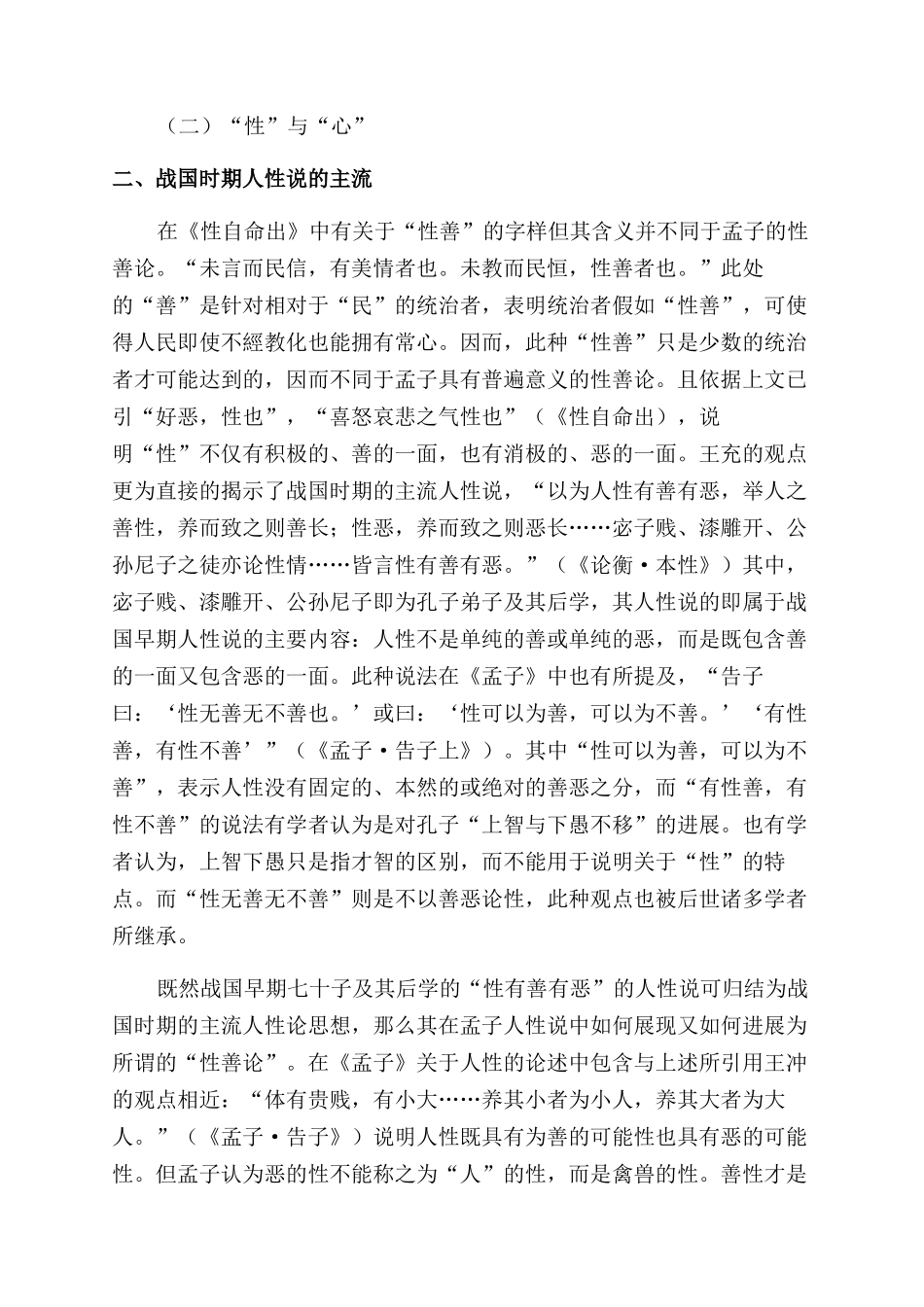郭店楚简与儒学人性论摘要:在对先秦儒学的传统讨论中,人性说的进展脉络即为: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至战国中期孟子提出性善说,战国后期荀子提出的性恶说。在获得郭店楚简这一重要史料后,我们可以解决众多历史遗留的疑难问题,弥补理论讨论中由于缺乏史料基础而产生的缺陷。本文主要讨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人性说,填补孔子与孟、荀人性说之间的空白,发掘战国时期的主流人性论思想及其在整个关于人性说的儒学思想史中的地位。关键词:人性说;《性自命出》;儒学一、郭店楚简中人性说的内容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篇集中讨论了关于战国中期儒家的人性学说。(一)“性”与“情”在先秦两汉哲学中存在将“性情”并称,将二者不加区分而混同使用的传统,因而出现以情论性的情况,将人的情感意识活动直接当作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而在《性自命出》篇中已将情与性二者进行抽象区分,提出“情生于性”。在“好恶,性也。”一句中,好恶实际指人的情感意识活动。因在“所好所恶,物也。”一句中的“好”与“恶”均是指人的情感活动。因而出现了好恶之情即为性的性与情的混同,但若在“情生于性”的前提下进行理解,即为好恶的情感是居于表层的现象,性才是内在的本质。《语丛》中对情进行了分类,将其归纳为喜、愠、惧、慈、爱、恶、欲等,在此基础之上还存在生于喜的乐、生于愠的忧、生于恶的怒、生于爱的亲等。此处并不能因派生的关系而将某类当作性,二者均应划归为情,只是乐、忧、怒、亲等情感较之喜、愠、惧、慈、爱更为强烈,若将前一组视为初级情感,则后一组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产生的次级情感。在此列举的各种情,均为性的外在表现,而性的内涵则为气。(二)“性”与“心”二、战国时期人性说的主流在《性自命出》中有关于“性善”的字样但其含义并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论。“未言而民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此处的“善”是针对相对于“民”的统治者,表明统治者假如“性善”,可使得人民即使不經教化也能拥有常心。因而,此种“性善”只是少数的统治者才可能达到的,因而不同于孟子具有普遍意义的性善论。且依据上文已引“好恶,性也”,“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性自命出),说明“性”不仅有积极的、善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恶的一面。王充的观点更为直接的揭示了战国时期的主流人性说,“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