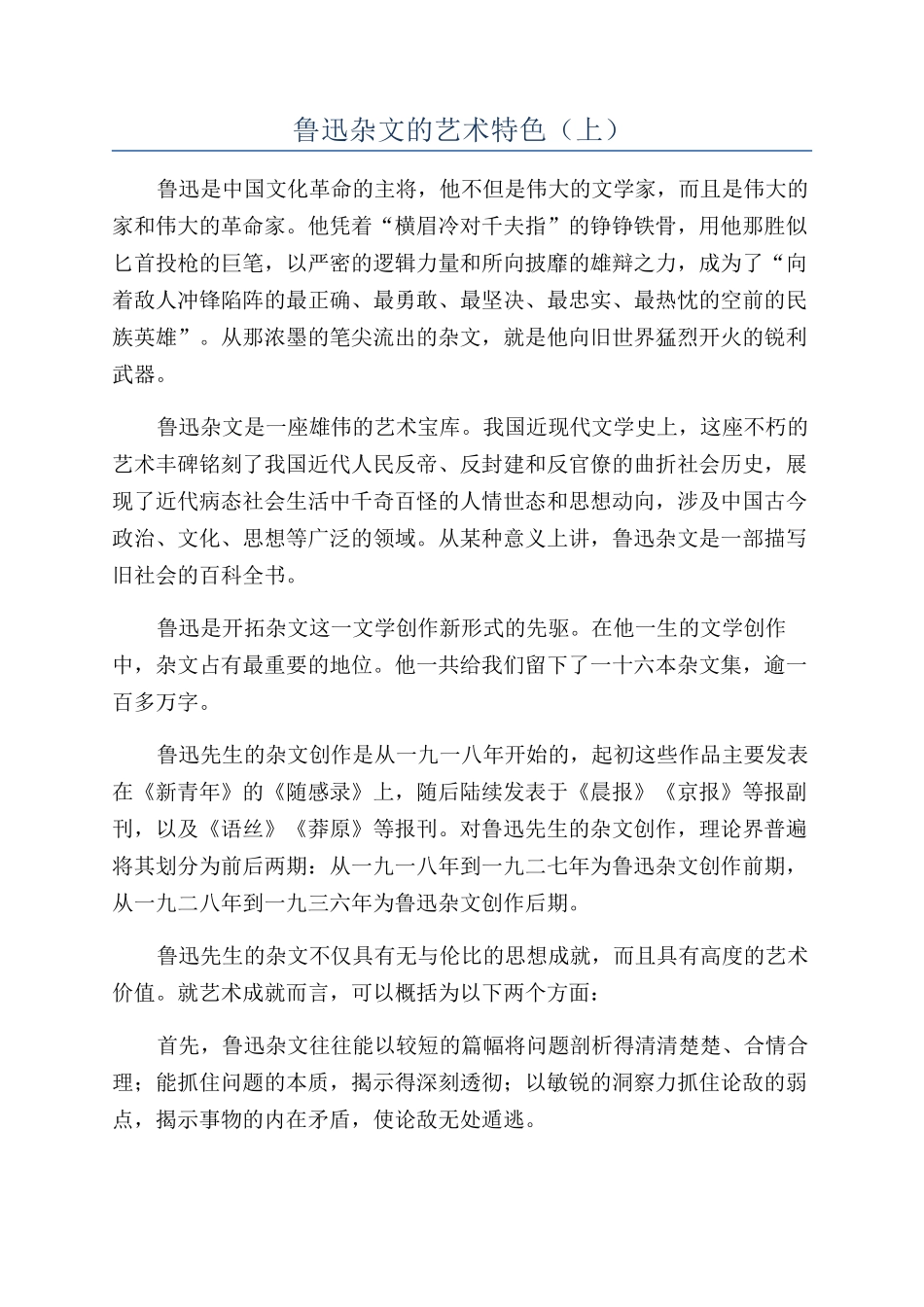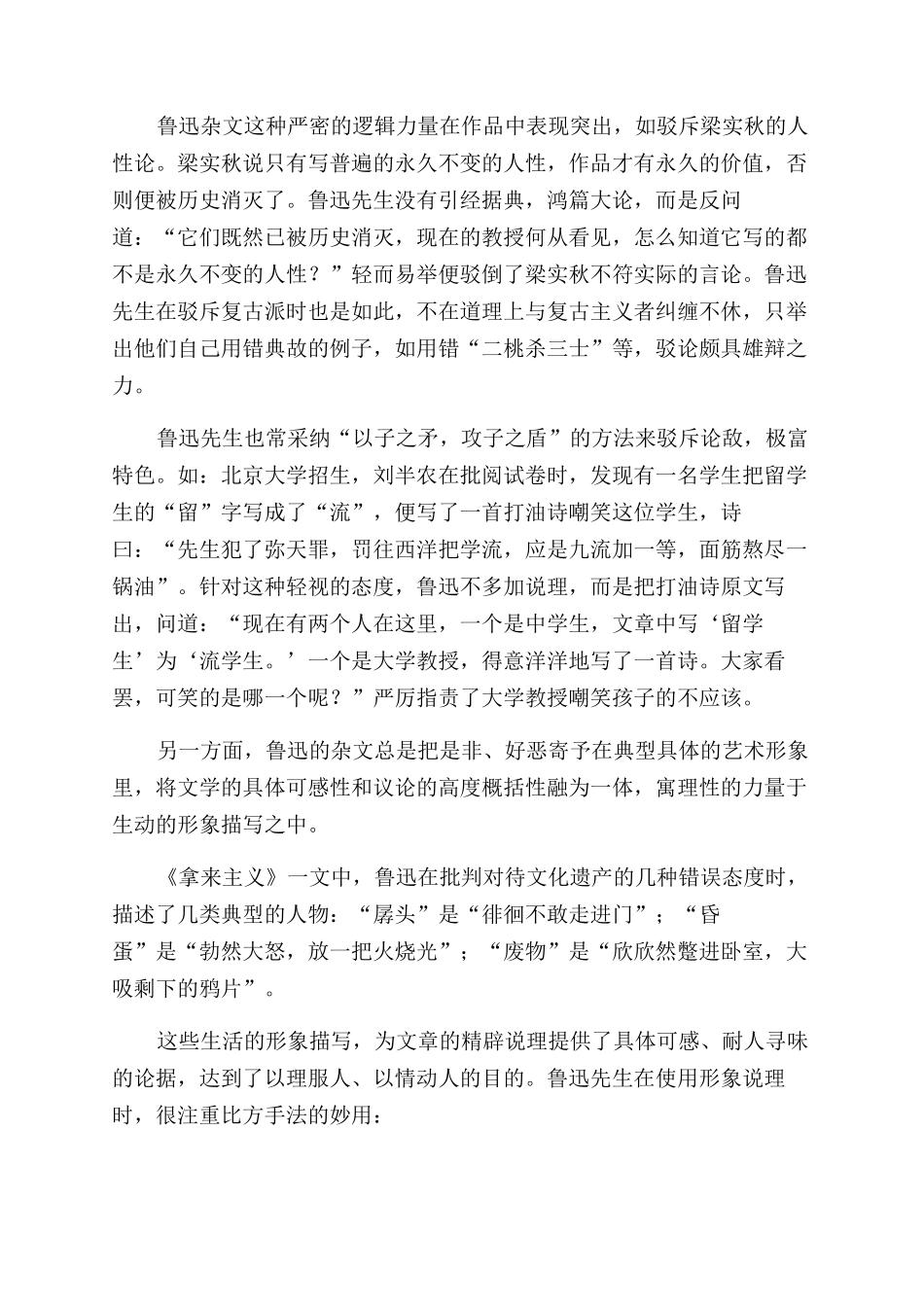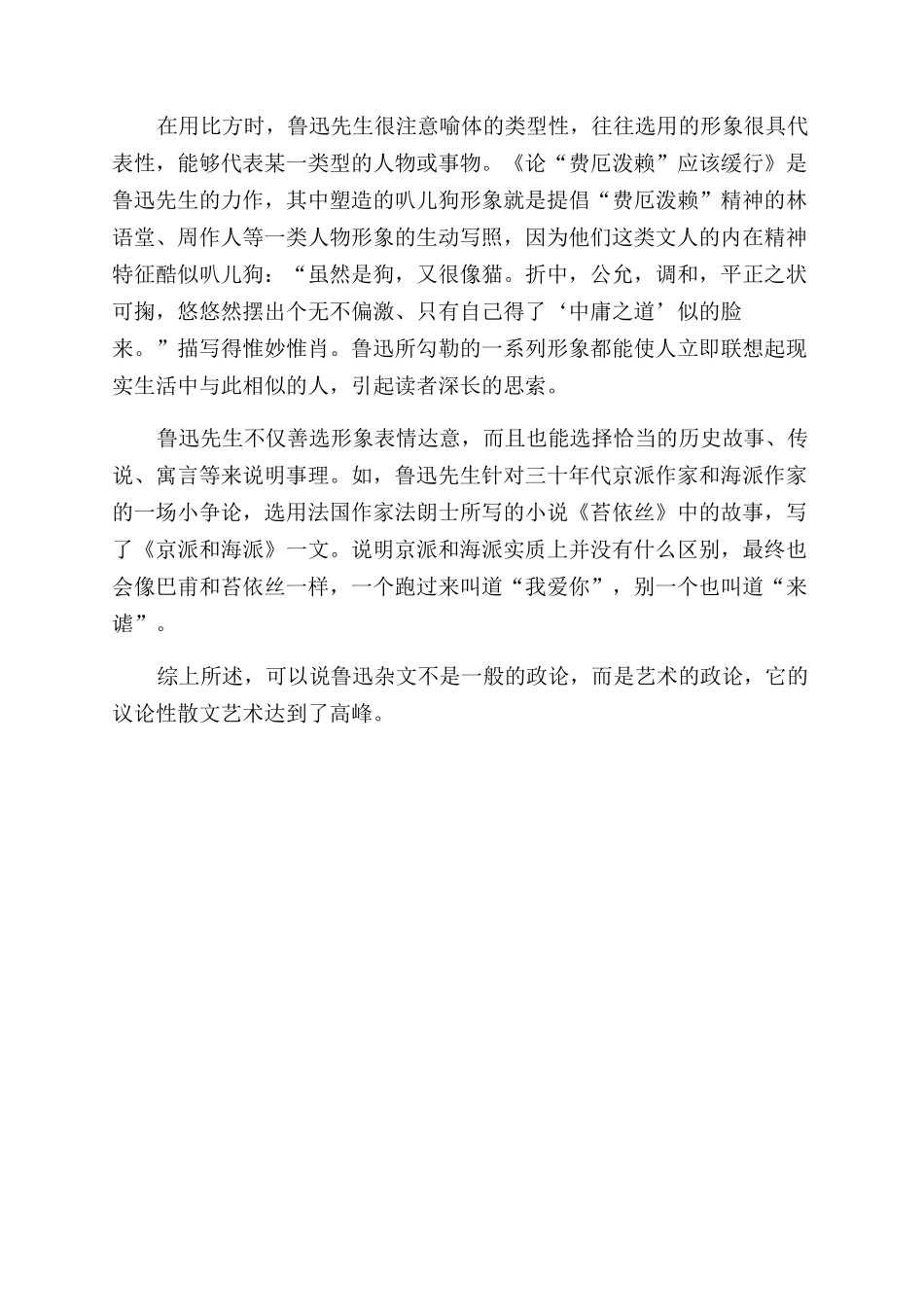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上)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凭着“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铮铮铁骨,用他那胜似匕首投枪的巨笔,以严密的逻辑力量和所向披靡的雄辩之力,成为了“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从那浓墨的笔尖流出的杂文,就是他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的锐利武器。鲁迅杂文是一座雄伟的艺术宝库。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这座不朽的艺术丰碑铭刻了我国近代人民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的曲折社会历史,展现了近代病态社会生活中千奇百怪的人情世态和思想动向,涉及中国古今政治、文化、思想等广泛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杂文是一部描写旧社会的百科全书。鲁迅是开拓杂文这一文学创作新形式的先驱。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杂文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他一共给我们留下了一十六本杂文集,逾一百多万字。鲁迅先生的杂文创作是从一九一八年开始的,起初这些作品主要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上,随后陆续发表于《晨报》《京报》等报副刊,以及《语丝》《莽原》等报刊。对鲁迅先生的杂文创作,理论界普遍将其划分为前后两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七年为鲁迅杂文创作前期,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为鲁迅杂文创作后期。鲁迅先生的杂文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思想成就,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就艺术成就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鲁迅杂文往往能以较短的篇幅将问题剖析得清清楚楚、合情合理;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揭示得深刻透彻;以敏锐的洞察力抓住论敌的弱点,揭示事物的内在矛盾,使论敌无处遁逃。鲁迅杂文这种严密的逻辑力量在作品中表现突出,如驳斥梁实秋的人性论。梁实秋说只有写普遍的永久不变的人性,作品才有永久的价值,否则便被历史消灭了。鲁迅先生没有引经据典,鸿篇大论,而是反问道:“它们既然已被历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怎么知道它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轻而易举便驳倒了梁实秋不符实际的言论。鲁迅先生在驳斥复古派时也是如此,不在道理上与复古主义者纠缠不休,只举出他们自己用错典故的例子,如用错“二桃杀三士”等,驳论颇具雄辩之力。鲁迅先生也常采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来驳斥论敌,极富特色。如:北京大学招生,刘半农在批阅试卷时,发现有一名学生把留学生的“留”字写成了“流”,便写了一首打油诗嘲笑这位学生,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