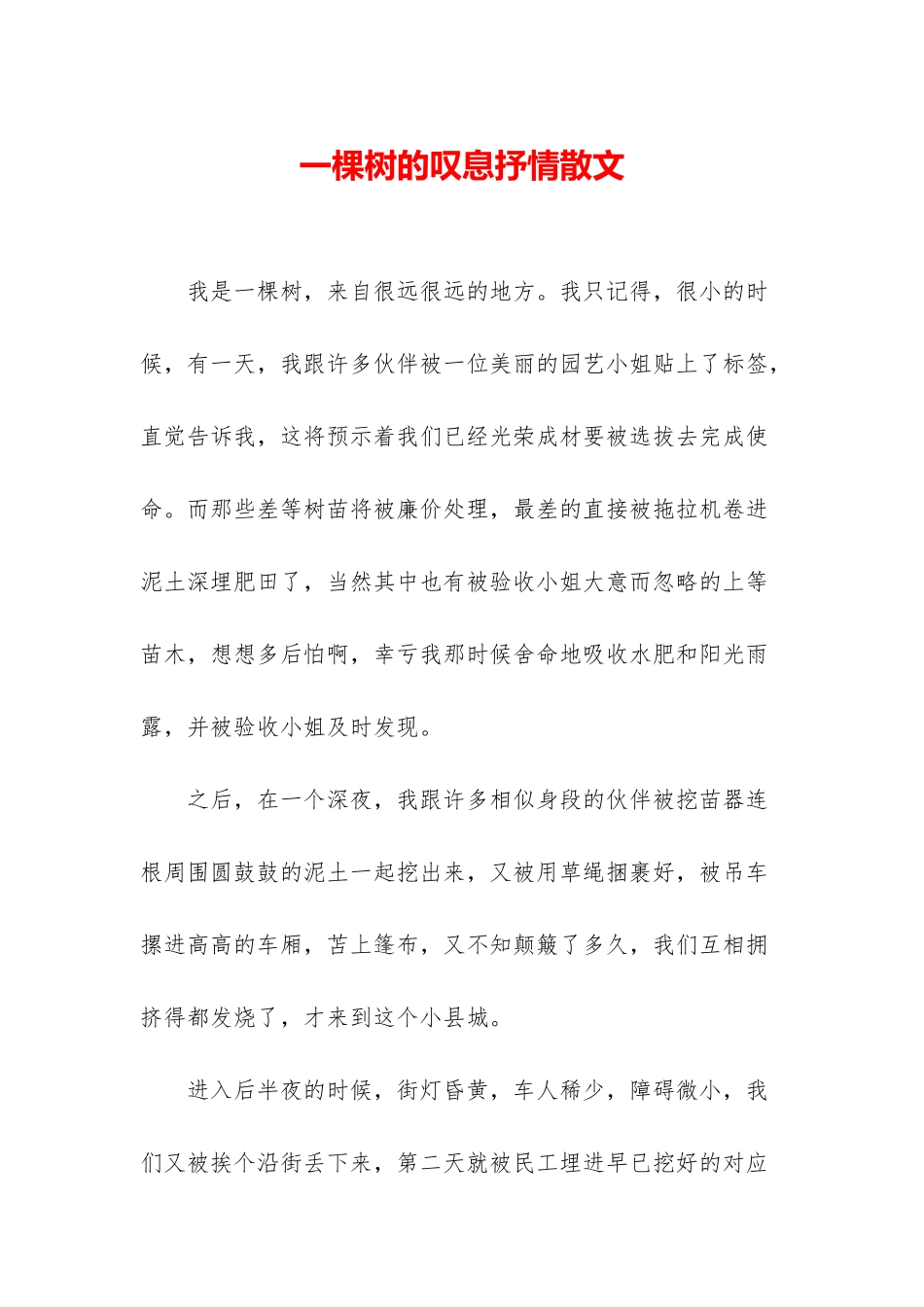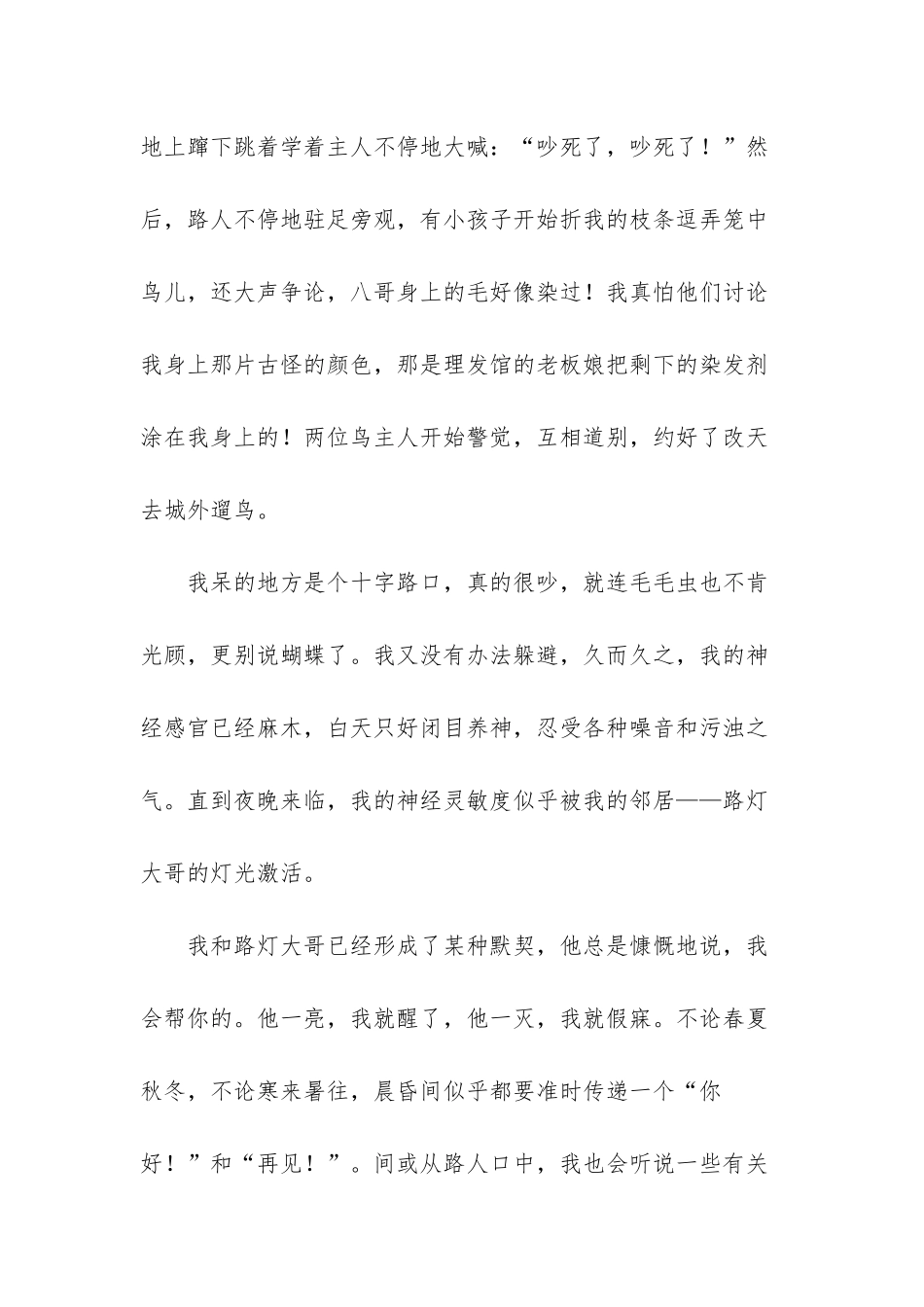一棵树的叹息抒情散文 我是一棵树,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只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我跟许多伙伴被一位美丽的园艺小姐贴上了标签,直觉告诉我,这将预示着我们已经光荣成材要被选拔去完成使命。而那些差等树苗将被廉价处理,最差的直接被拖拉机卷进泥土深埋肥田了,当然其中也有被验收小姐大意而忽略的上等苗木,想想多后怕啊,幸亏我那时候舍命地吸收水肥和阳光雨露,并被验收小姐及时发现。 之后,在一个深夜,我跟许多相似身段的伙伴被挖苗器连根周围圆鼓鼓的泥土一起挖出来,又被用草绳捆裹好,被吊车摞进高高的车厢,苫上篷布,又不知颠簸了多久,我们互相拥挤得都发烧了,才来到这个小县城。 进入后半夜的时候,街灯昏黄,车人稀少,障碍微小,我们又被挨个沿街丢下来,第二天就被民工埋进早已挖好的对应的坑里。我终于可以在宽阔的空间挺直腰板了,有人给我们哗哗地浇水,还有人给我们输液,我那片已经耷拉了好久马上撕裂的叶片又抖擞起来了。我终于舒了口气,贪欲地吸了几口新口味的水肥,感觉还不错。后来,我就只能与为数不多的伙伴遥遥相望,扎根这里,每天与路灯一起站得笔直,活像城市的哨兵。 也只有等到后半夜,整个城市开始短暂地睡眠时,我才能感受到风儿柔情的抚摸,才能听到自己甩头发的“沙沙”声音。其实,我最希望的是能有只美丽的小鸟儿依靠在我的胸膛,在我的臂膀间呼朋引伴、跳舞歌唱。可是,我等了好久,只等到一次,还是两只美丽的八哥被主人连笼子挂在了我的枝头,因为主人要腾出手来接电话。后来,又来了一位老伙计,和八哥的主人拉起了家常,居然说起了六十年前的县城,说到激动处,为了腾出手来打手势比划,老伙计又把他的一对儿百灵鸟连笼子顺手挂在了我的另一边。百灵鸟们开始对唱,八哥不怀好意地上蹿下跳着学着主人不停地大喊:“吵死了,吵死了!”然后,路人不停地驻足旁观,有小孩子开始折我的枝条逗弄笼中鸟儿,还大声争论,八哥身上的毛好像染过!我真怕他们讨论我身上那片古怪的颜色,那是理发馆的老板娘把剩下的染发剂涂在我身上的!两位鸟主人开始警觉,互相道别,约好了改天去城外遛鸟。 我呆的地方是个十字路口,真的很吵,就连毛毛虫也不肯光顾,更别说蝴蝶了。我又没有办法躲避,久而久之,我的神经感官已经麻木,白天只好闭目养神,忍受各种噪音和污浊之气。直到夜晚来临,我的神经灵敏度似乎被我的邻居——路灯大哥的灯光激活。 我和路灯大哥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他总是慷慨地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