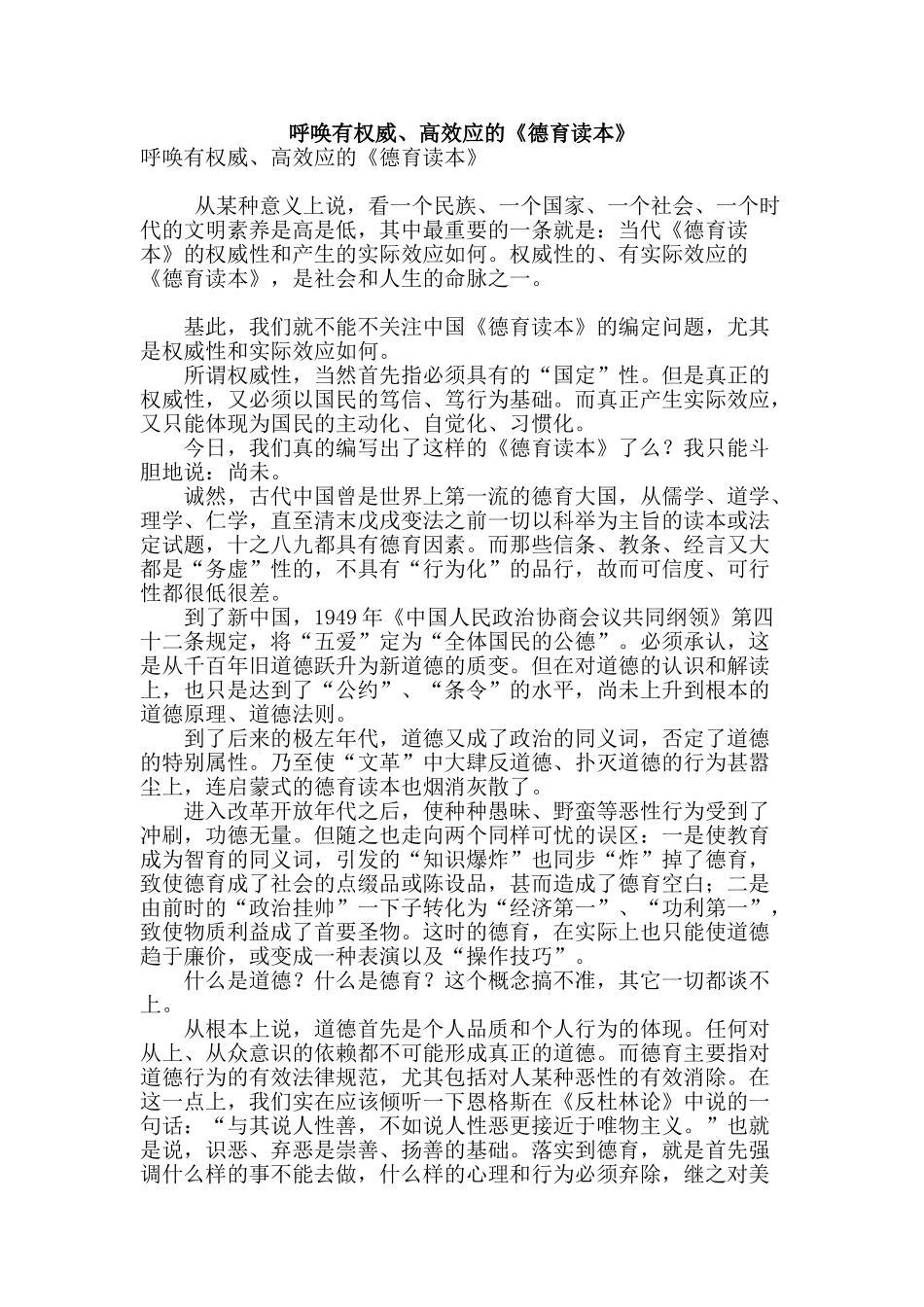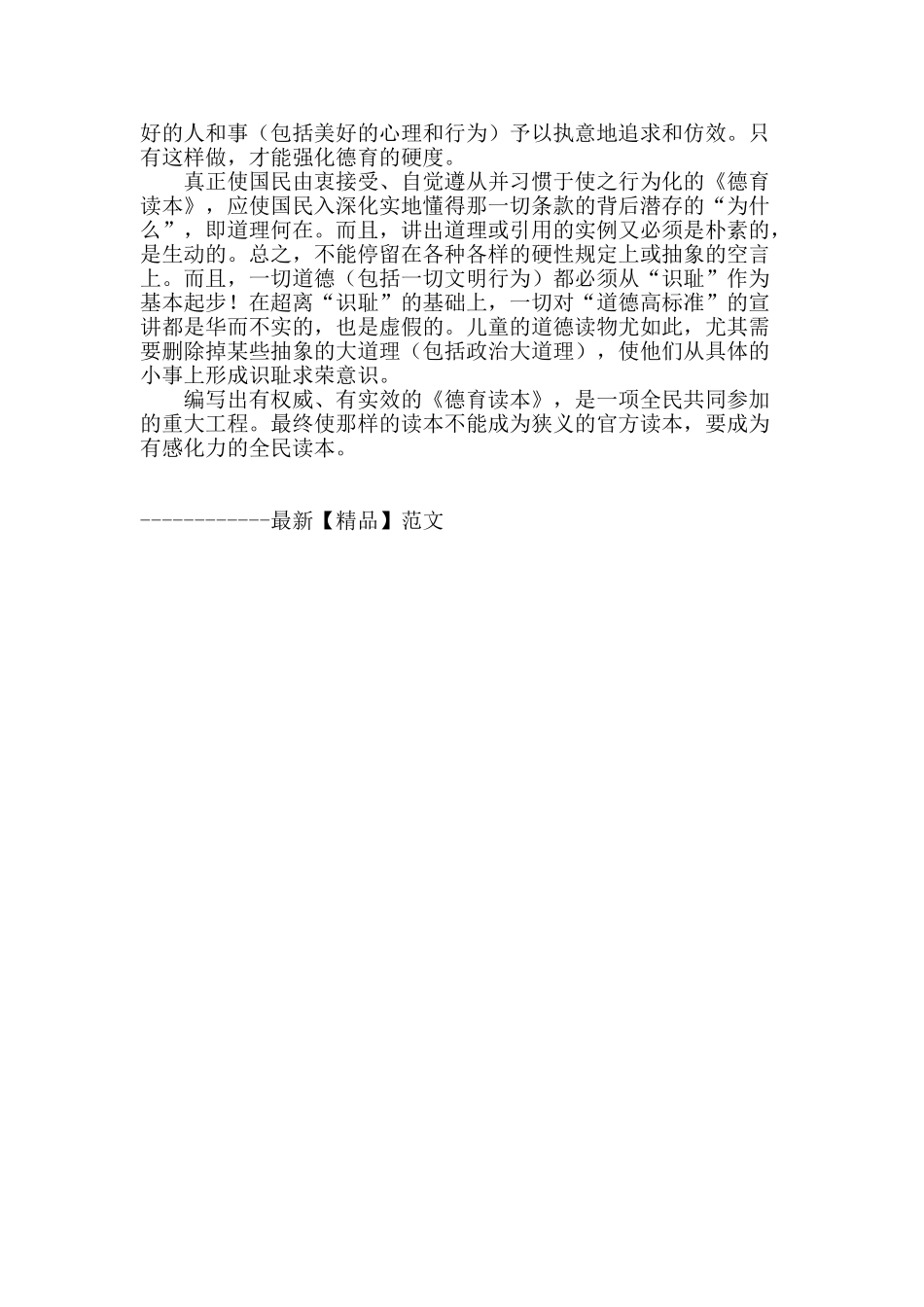呼唤有权威、高效应的《德育读本》呼唤有权威、高效应的《德育读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明素养是高是低,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当代《德育读本》的权威性和产生的实际效应如何。权威性的、有实际效应的《德育读本》,是社会和人生的命脉之一。 基此,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中国《德育读本》的编定问题,尤其是权威性和实际效应如何。 所谓权威性,当然首先指必须具有的“国定”性。但是真正的权威性,又必须以国民的笃信、笃行为基础。而真正产生实际效应,又只能体现为国民的主动化、自觉化、习惯化。 今日,我们真的编写出了这样的《德育读本》了么?我只能斗胆地说:尚未。 诚然,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德育大国,从儒学、道学、理学、仁学,直至清末戊戌变法之前一切以科举为主旨的读本或法定试题,十之八九都具有德育因素。而那些信条、教条、经言又大都是“务虚”性的,不具有“行为化”的品行,故而可信度、可行性都很低很差。 到了新中国,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规定,将“五爱”定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必须承认,这是从千百年旧道德跃升为新道德的质变。但在对道德的认识和解读上,也只是达到了“公约”、“条令”的水平,尚未上升到根本的道德原理、道德法则。 到了后来的极左年代,道德又成了政治的同义词,否定了道德的特别属性。乃至使“文革”中大肆反道德、扑灭道德的行为甚嚣尘上,连启蒙式的德育读本也烟消灰散了。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使种种愚昧、野蛮等恶性行为受到了冲刷,功德无量。但随之也走向两个同样可忧的误区:一是使教育成为智育的同义词,引发的“知识爆炸”也同步“炸”掉了德育,致使德育成了社会的点缀品或陈设品,甚而造成了德育空白;二是由前时的“政治挂帅”一下子转化为“经济第一”、“功利第一”,致使物质利益成了首要圣物。这时的德育,在实际上也只能使道德趋于廉价,或变成一种表演以及“操作技巧”。 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德育?这个概念搞不准,其它一切都谈不上。 从根本上说,道德首先是个人品质和个人行为的体现。任何对从上、从众意识的依赖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道德。而德育主要指对道德行为的有效法律规范,尤其包括对人某种恶性的有效消除。在这一点上,我们实在应该倾听一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一句话:“与其说人性善,不如说人性恶更接近于唯物主义。”也就是说,识恶、弃恶是崇善、扬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