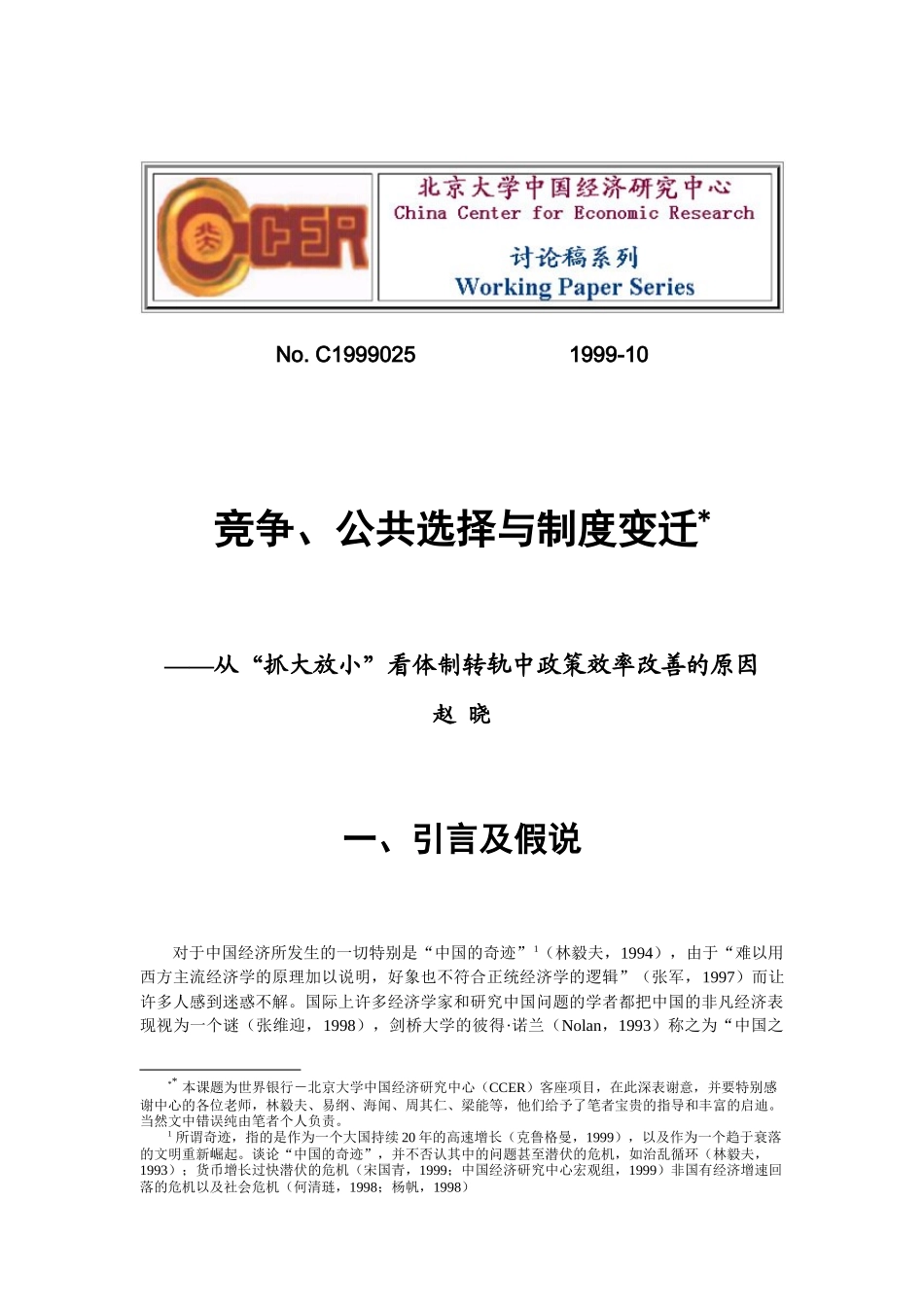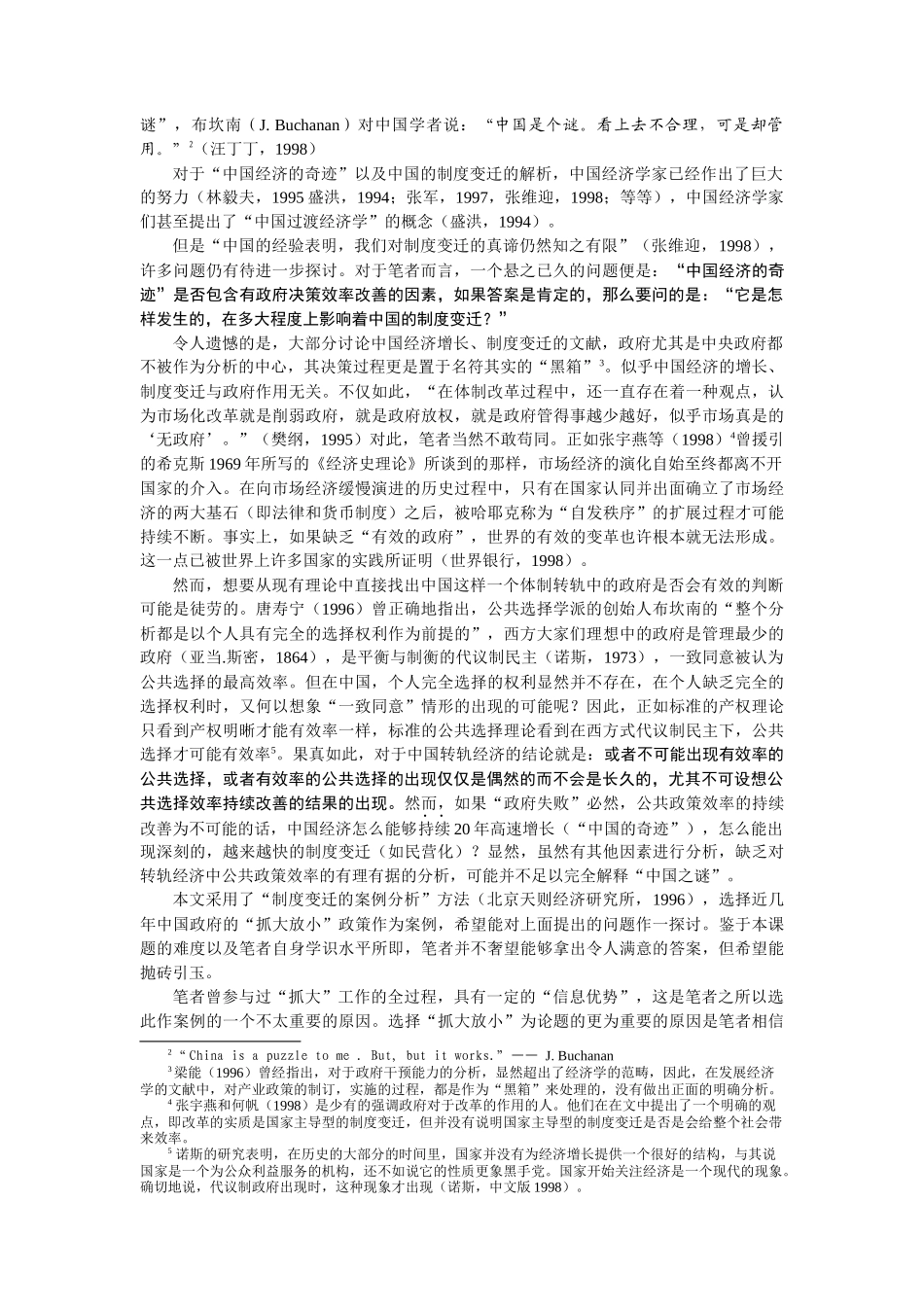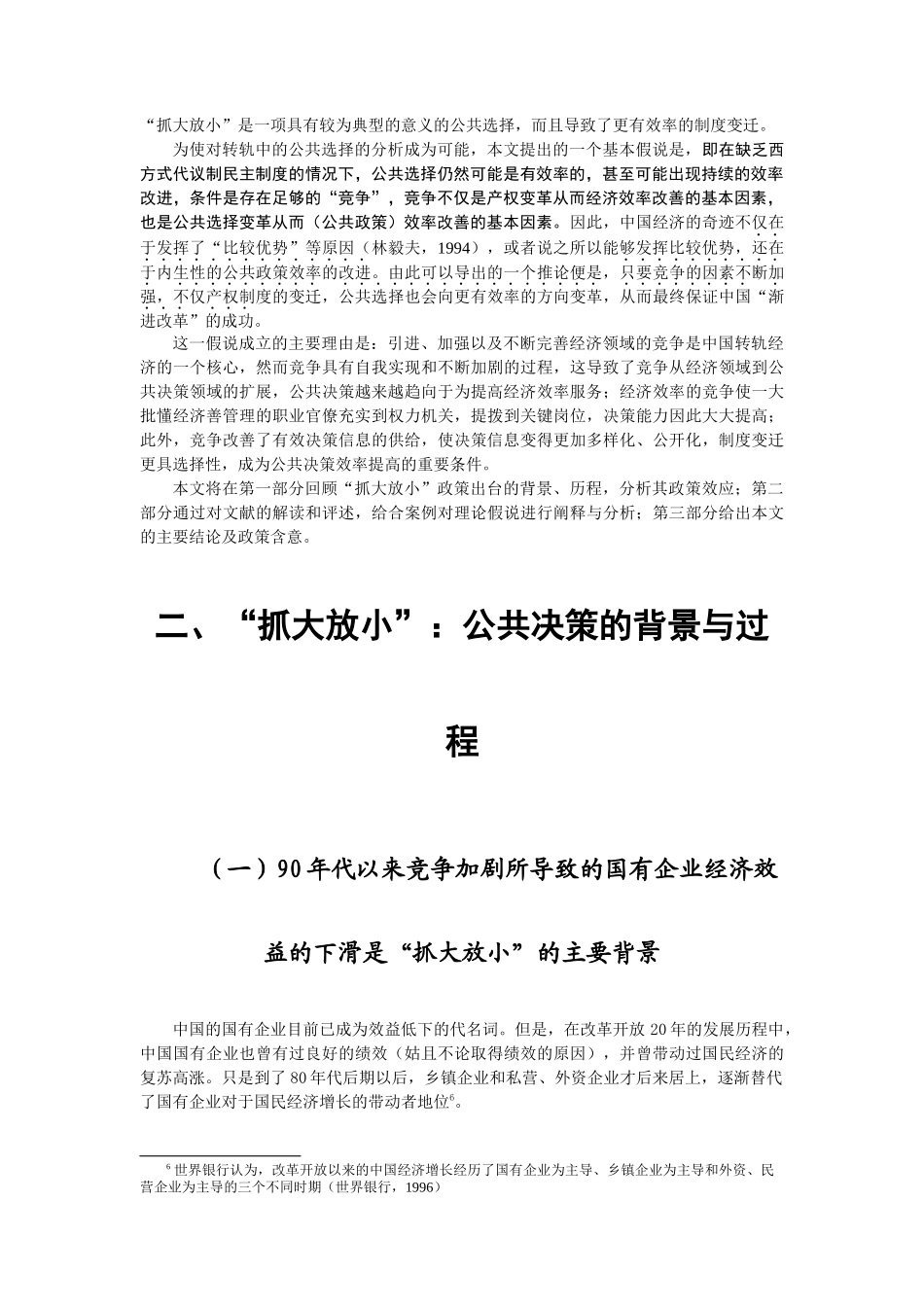No.C19990251999-10竞争、公共选择与制度变迁*――从“抓大放小”看体制转轨中政策效率改善的原因赵晓一、引言及假说对于中国经济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中国的奇迹”1(林毅夫,1994),由于“难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加以说明,好象也不符合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张军,1997)而让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中国的非凡经济表现视为一个谜(张维迎,1998),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Nolan,1993)称之为“中国之**本课题为世界银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客座项目,在此深表谢意,并要特别感谢中心的各位老师,林毅夫、易纲、海闻、周其仁、梁能等,他们给予了笔者宝贵的指导和丰富的启迪。当然文中错误纯由笔者个人负责。1所谓奇迹,指的是作为一个大国持续20年的高速增长(克鲁格曼,1999),以及作为一个趋于衰落的文明重新崛起。谈论“中国的奇迹”,并不否认其中的问题甚至潜伏的危机,如治乱循环(林毅夫,1993);货币增长过快潜伏的危机(宋国青,1999;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非国有经济增速回落的危机以及社会危机(何清琏,1998;杨帆,1998)谜”,布坎南(J.Buchanan)对中国学者说:“中国是个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2(汪丁丁,1998)对于“中国经济的奇迹”以及中国的制度变迁的解析,中国经济学家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林毅夫,1995盛洪,1994;张军,1997,张维迎,1998;等等),中国经济学家们甚至提出了“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概念(盛洪,1994)。但是“中国的经验表明,我们对制度变迁的真谛仍然知之有限”(张维迎,1998),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对于笔者而言,一个悬之已久的问题便是:“中国经济的奇迹”是否包含有政府决策效率改善的因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要问的是:“它是怎样发生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制度变迁?”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的文献,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都不被作为分析的中心,其决策过程更是置于名符其实的“黑箱”3。似乎中国经济的增长、制度变迁与政府作用无关。不仅如此,“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还一直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化改革就是削弱政府,就是政府放权,就是政府管得事越少越好,似乎市场真是的‘无政府’。”(樊纲,1995)对此,笔者当然不敢苟同。正如张宇燕等(1998)4曾援引的希克斯1969年所写的《经济史理论》所谈到的那样,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事实上,如果缺乏“有效的政府”,世界的有效的变革也许根本就无法形成。这一点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世界银行,1998)。然而,想要从现有理论中直接找出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中的政府是否会有效的判断可能是徒劳的。唐寿宁(1996)曾正确地指出,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的“整个分析都是以个人具有完全的选择权利作为前提的”,西方大家们理想中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亚当.斯密,1864),是平衡与制衡的代议制民主(诺斯,1973),一致同意被认为公共选择的最高效率。但在中国,个人完全选择的权利显然并不存在,在个人缺乏完全的选择权利时,又何以想象“一致同意”情形的出现的可能呢?因此,正如标准的产权理论只看到产权明晰才能有效率一样,标准的公共选择理论看到在西方式代议制民主下,公共选择才可能有效率5。果真如此,对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结论就是:或者不可能出现有效率的公共选择,或者有效率的公共选择的出现仅仅是偶然的而不会是长久的,尤其不可设想公共选择效率持续改善的结果的出现。然而,如果“政府失败”必然,公共政策效率的持续改善为不可能的话,中国经济怎么能够持续20年高速增长(“中国的奇迹”),怎么能出现深刻的,越来越快的制度变迁(如民营化)?显然,虽然有其他因素进行分析,缺乏对转轨经济中公共政策效率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可能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之谜”。本文采用了“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方法(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