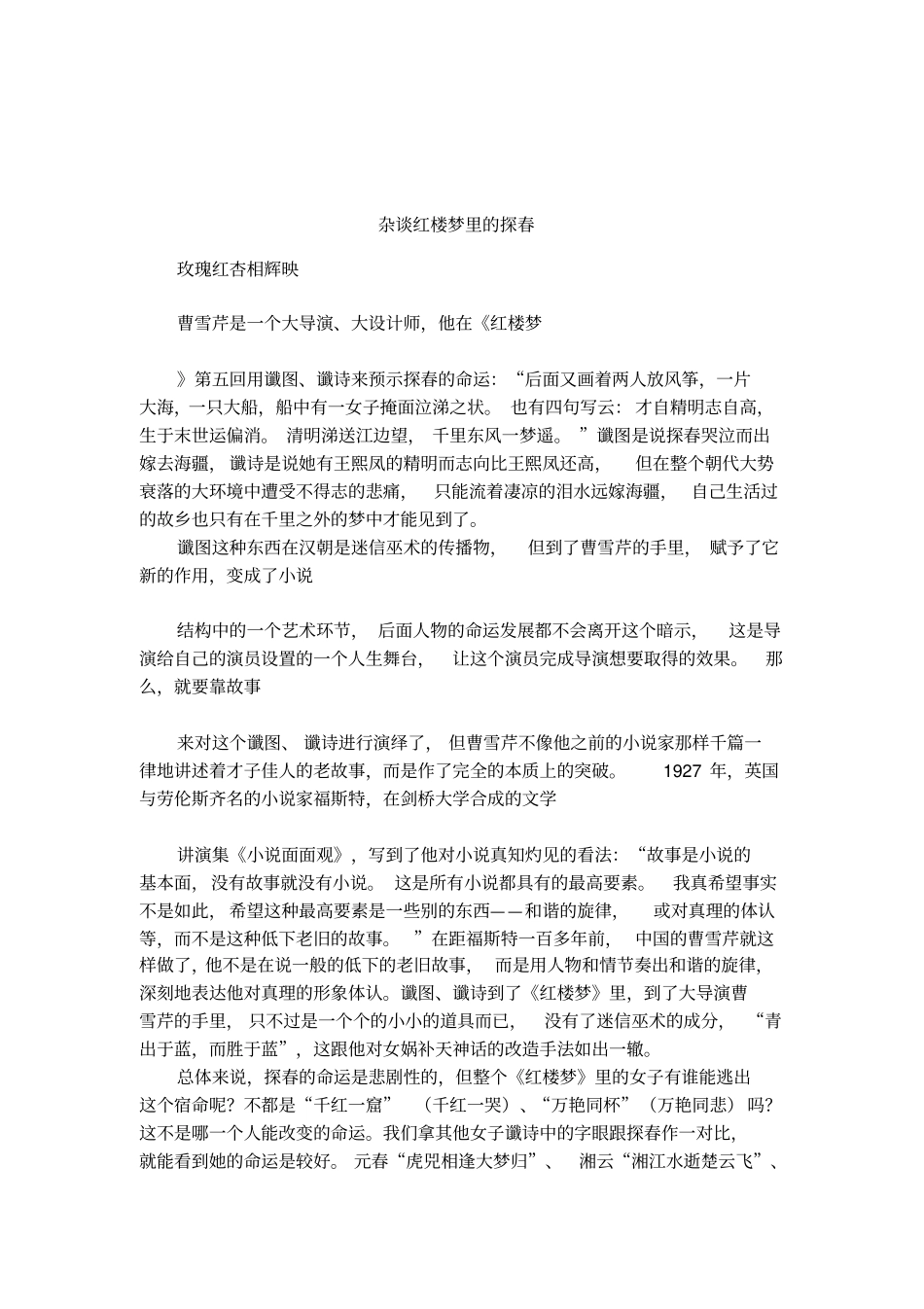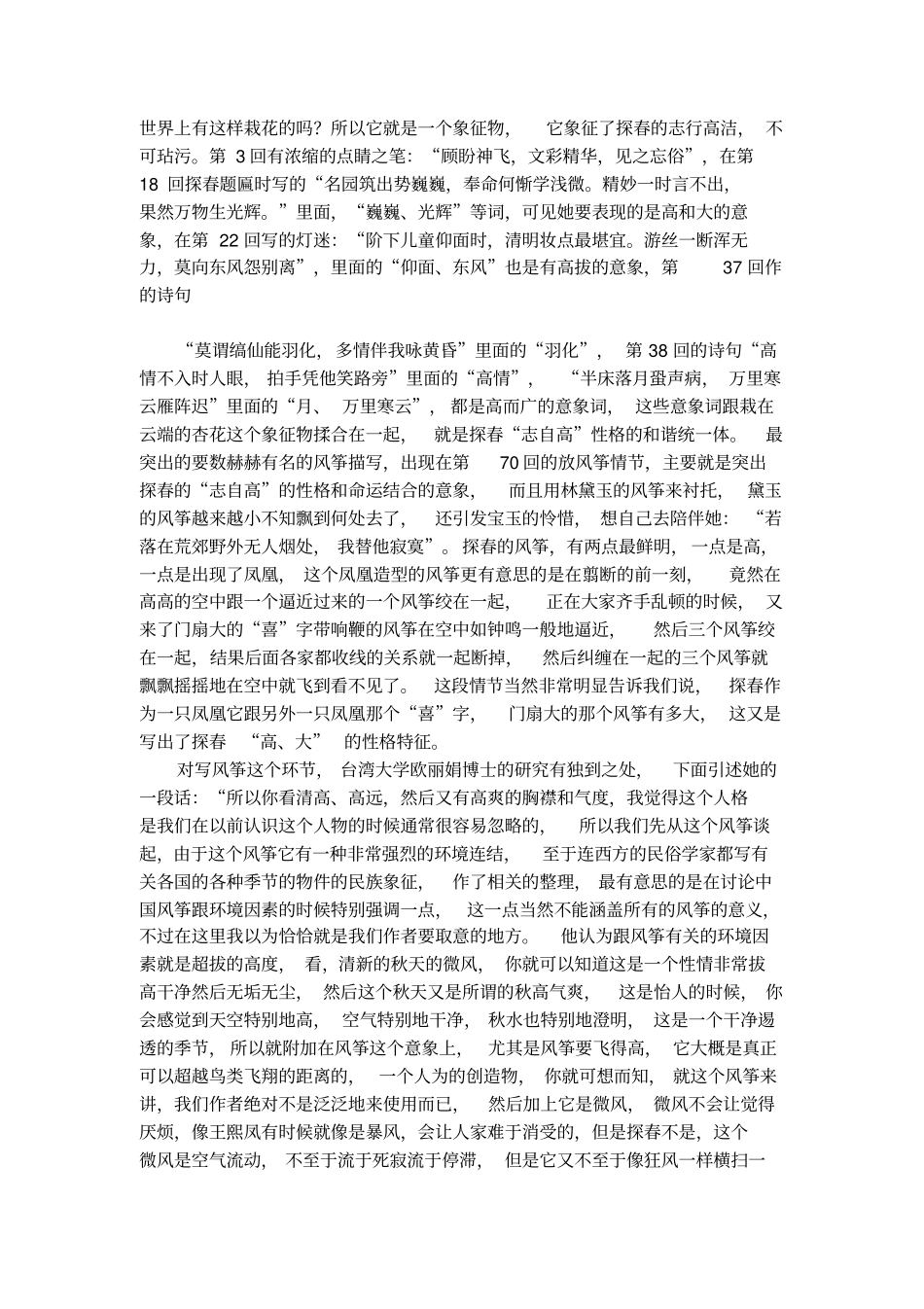杂谈红楼梦里的探春玫瑰红杏相辉映曹雪芹是一个大导演、大设计师,他在《红楼梦》第五回用谶图、谶诗来预示探春的命运:“后面又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也有四句写云: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谶图是说探春哭泣而出嫁去海疆,谶诗是说她有王熙凤的精明而志向比王熙凤还高,但在整个朝代大势衰落的大环境中遭受不得志的悲痛,只能流着凄凉的泪水远嫁海疆,自己生活过的故乡也只有在千里之外的梦中才能见到了。谶图这种东西在汉朝是迷信巫术的传播物,但到了曹雪芹的手里,赋予了它新的作用,变成了小说结构中的一个艺术环节,后面人物的命运发展都不会离开这个暗示,这是导演给自己的演员设置的一个人生舞台,让这个演员完成导演想要取得的效果。那么,就要靠故事来对这个谶图、谶诗进行演绎了,但曹雪芹不像他之前的小说家那样千篇一律地讲述着才子佳人的老故事,而是作了完全的本质上的突破。1927年,英国与劳伦斯齐名的小说家福斯特,在剑桥大学合成的文学讲演集《小说面面观》,写到了他对小说真知灼见的看法:“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这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要素。我真希望事实不是如此,希望这种最高要素是一些别的东西——和谐的旋律,或对真理的体认等,而不是这种低下老旧的故事。”在距福斯特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曹雪芹就这样做了,他不是在说一般的低下的老旧故事,而是用人物和情节奏出和谐的旋律,深刻地表达他对真理的形象体认。谶图、谶诗到了《红楼梦》里,到了大导演曹雪芹的手里,只不过是一个个的小小的道具而已,没有了迷信巫术的成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跟他对女娲补天神话的改造手法如出一辙。总体来说,探春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但整个《红楼梦》里的女子有谁能逃出这个宿命呢?不都是“千红一窟”(千红一哭)、“万艳同杯”(万艳同悲)吗?这不是哪一个人能改变的命运。我们拿其他女子谶诗中的字眼跟探春作一对比,就能看到她的命运是较好。元春“虎兕相逢大梦归”、湘云“湘江水逝楚云飞”、妙玉“终陷淖泥中”、迎春“一载赴黄粱”、惜春“独卧青灯古佛旁”、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巧姐“家亡莫论亲”、李纨“枉与他人作笑谈”、秦可卿“造衅开端实在宁”、宝钗“金簪雪里埋”、黛玉“玉带林中挂”,而探春“千里东风一梦遥”,虽说是“梦遥”,但起码还有“东风”,从字面上以及第119回写到她从海疆回到贾府来看,在所有这些女孩中,探春的归宿是最理想的,就元春、探春和宝玉的命运比较,元春因宫廷斗争而早逝,宝玉因看不透红尘飘然弃世,只有探春嫁出去后还有能力回来收拾贾府的宵小之辈。探春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与她性格有关,作者在第63回给了探春红杏花花签:“众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日边红杏倚云栽。”这朵红杏花虽然不是她的代表花,但却是她的命运之花。虽然作者在第65回又给了探春一朵玫瑰花,这朵玫瑰花是她的代表花,芳香以及带刺的特点,的确能代表探春的性格,但它与红杏花并不矛盾,这两朵美丽鲜艳的花,俯仰生姿,相映成趣,将探春的性格烘托得全面而生动。在《红楼梦》的研究中,关于探春这朵带刺的玫瑰花特征论述的文章很多,主要依据是第74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矢孤介杜绝宁国府”探春怒掴王善保家的:“一语未了,只听‘拍’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你打谅我是同你们姑娘那样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他,就错了主意!你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探春是一个立体人物形象,不是扁平形象,对于这朵玫瑰身上的“刺”,应该也要立体地来理解,它的刺可以伤人,可以刺伤敢于侵犯她的人,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尊严。但我这里就不这样来看这个“刺”了,我以为这个“刺”还可以是探春对本身空间的扩张,她要让自己的生存空间扩大,就用这个“刺”来延伸,它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