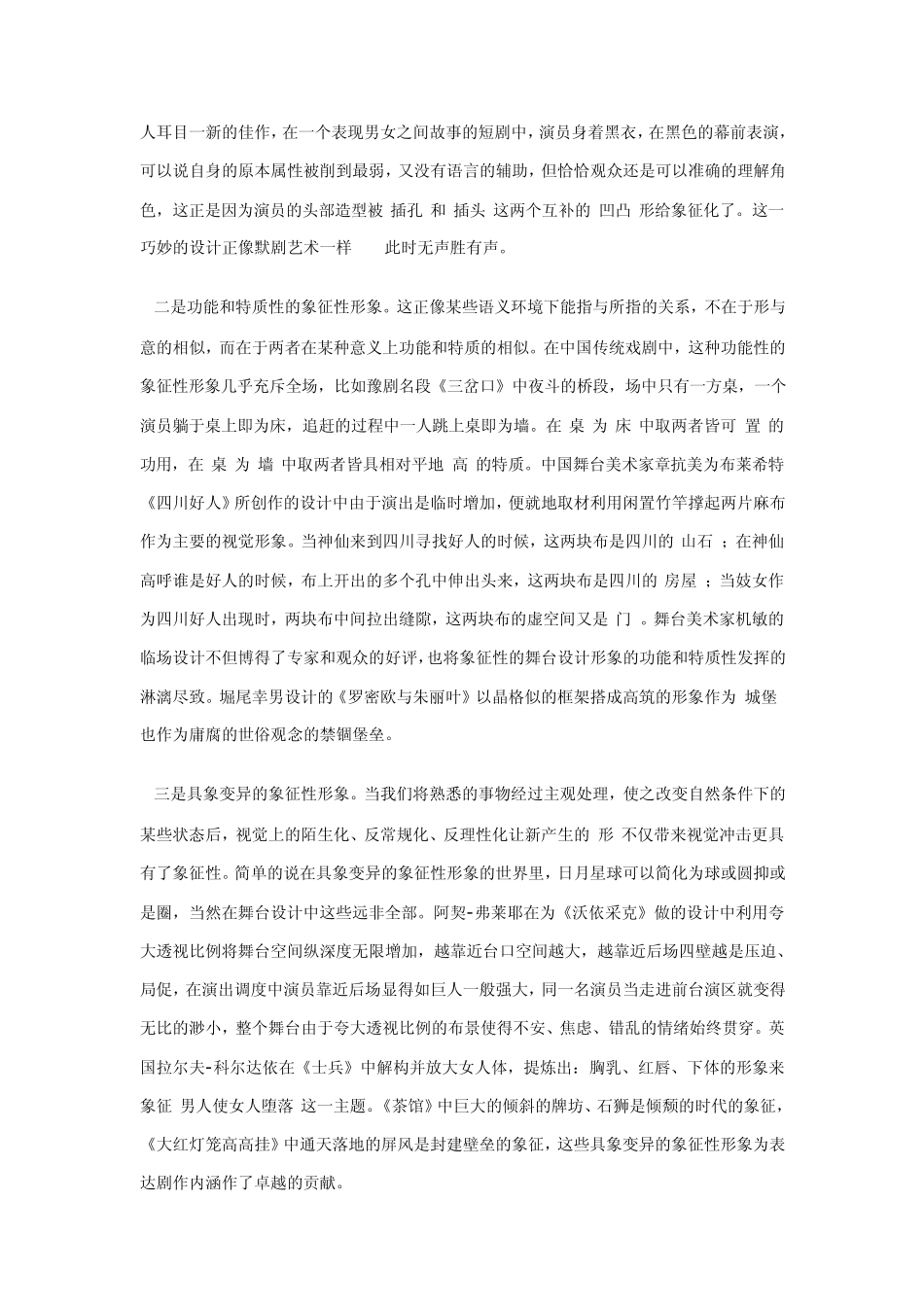浅读象征的诗性及象征性舞台设计形象 “诗人”与“石头” 波特莱尔在《恶之花》中将宇宙万物都看作虚幻和符号的总集,“象征之林”即是充满了狂热的创造欲、精美的音乐性和形而上的深度,只有诗人的想象力才赋予其形与意。象征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诗人让-拉莫提出,于是神秘的诗性色彩一直伴其左右。象征主义的象征性意在将不可视的抽象意义赋予一个可以感知的具体物象之上即通过可见物达到不可见的精神本体,作为对自由精神和最高的真实的体现。然而象征性来自文学却没有拘泥于文学,在绘画、建筑、平面设计、戏剧等视觉艺术领域也树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延伸出更深远的美学意义。在视觉艺术中象征性为之注入了诗性的表达: 首先象征性具有诗一般洗练的概括力。经过艺术处理过的象征性形象,往往是从一堆隐晦的、庞杂的、似是而非的概念里提炼出来,将最突出、最深刻的部分物化。也许这幻化出的形象并非最贴近现实物,也可以说它并非是真实的,但它必然是最高的真实,因为的它所贴近的正是精神的本体。荷兰艺术家皮特-蒙德里安创作的《码头与海洋》其中绘画元素被减少到一堆垂直与水平的短线,制造出一种忽隐忽现,神秘的十字形象,猛地看上去似乎并不具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然而一旦说出它的名字,那种波光粼粼的海洋就立刻在画面中呈现。舞台美术家理查德-哈德森为歌剧《贴木儿》创作,从众多的视觉素材中提炼出具有象征性意味的“巨大的脚踏着球”这样的视觉形象,意在表现贴木儿称霸世界的野心和王权巨大的威慑力,同时随着剧情的进展脚与球的布景又会有所变化,为一个视觉形象赋予多层象征意义。 其次象征性具有诗一般强大的感染力。在画家乔治-德希尔科创造的梦幻的、怪异的、空洞的城市中,充斥着潮湿、淡泊和悲伤,观者被莫名的绝望以强大的气场压得人感到连呼吸都困难,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布雷顿所说的“无法治愈的人类忧虑”。乔治- 西平为在日本演出的清唱剧《俄狄浦斯王》设计的“城”看上去是一只巨大的眼,它是俄狄浦斯王的眼、是“魔鬼”的眼、是“贪欲”的眼,也是宿命的眼。当俄狄浦斯王刺瞎双眼的霎那,从这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眼” 中倾泻而出的红绸顿时充斥了观者的双眼,被刺的疼痛和血水的流淌一时间分不清真假,血腥的味道也如在唇齿。红绸如血,如血的又何只是红绸。 最后象征性具有诗一般广袤的想象力。 我们通常苦恼于如何利用客观世界从现象世界通向本体世界,然而在主观世界里我们却可以用非理性的途径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