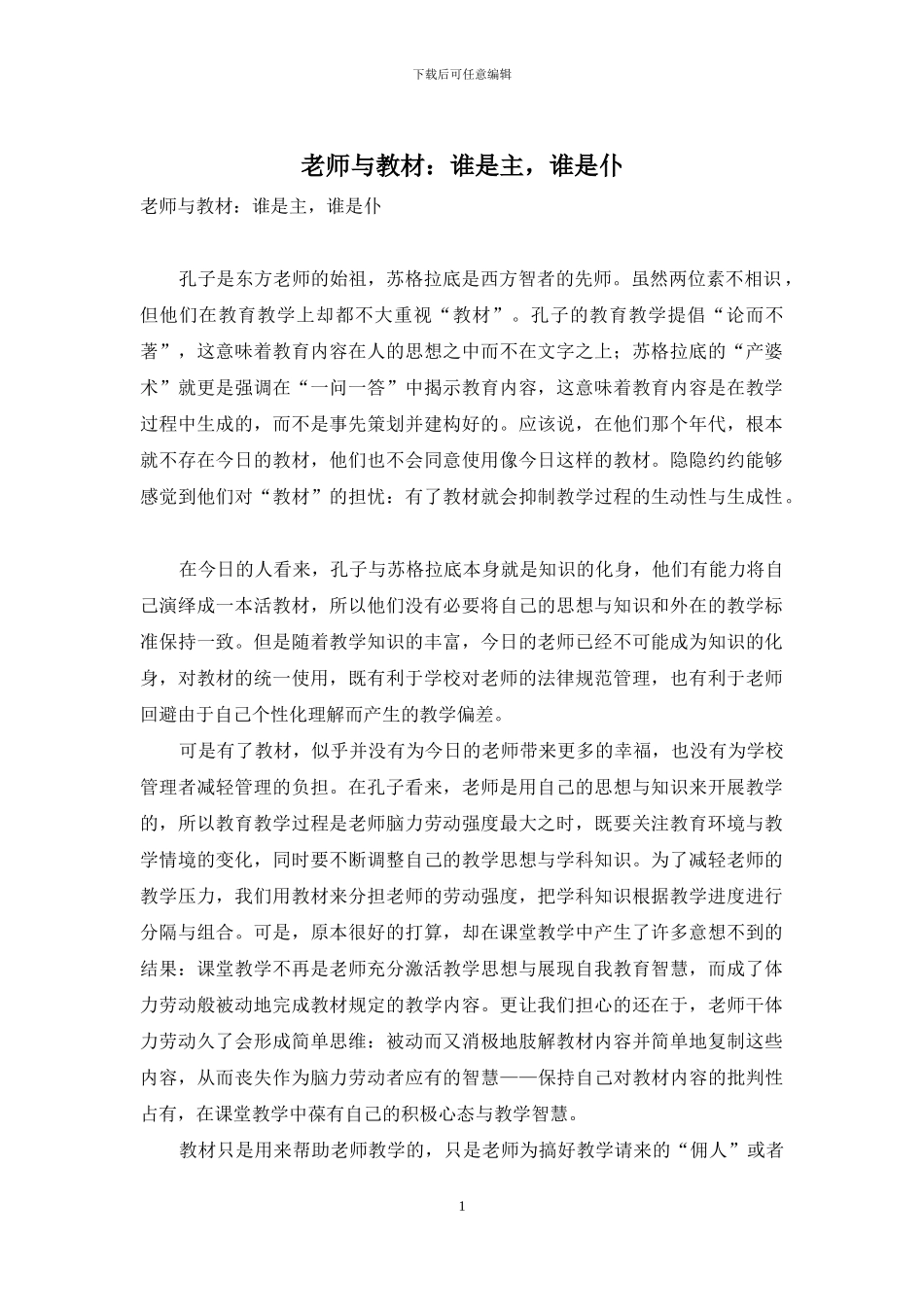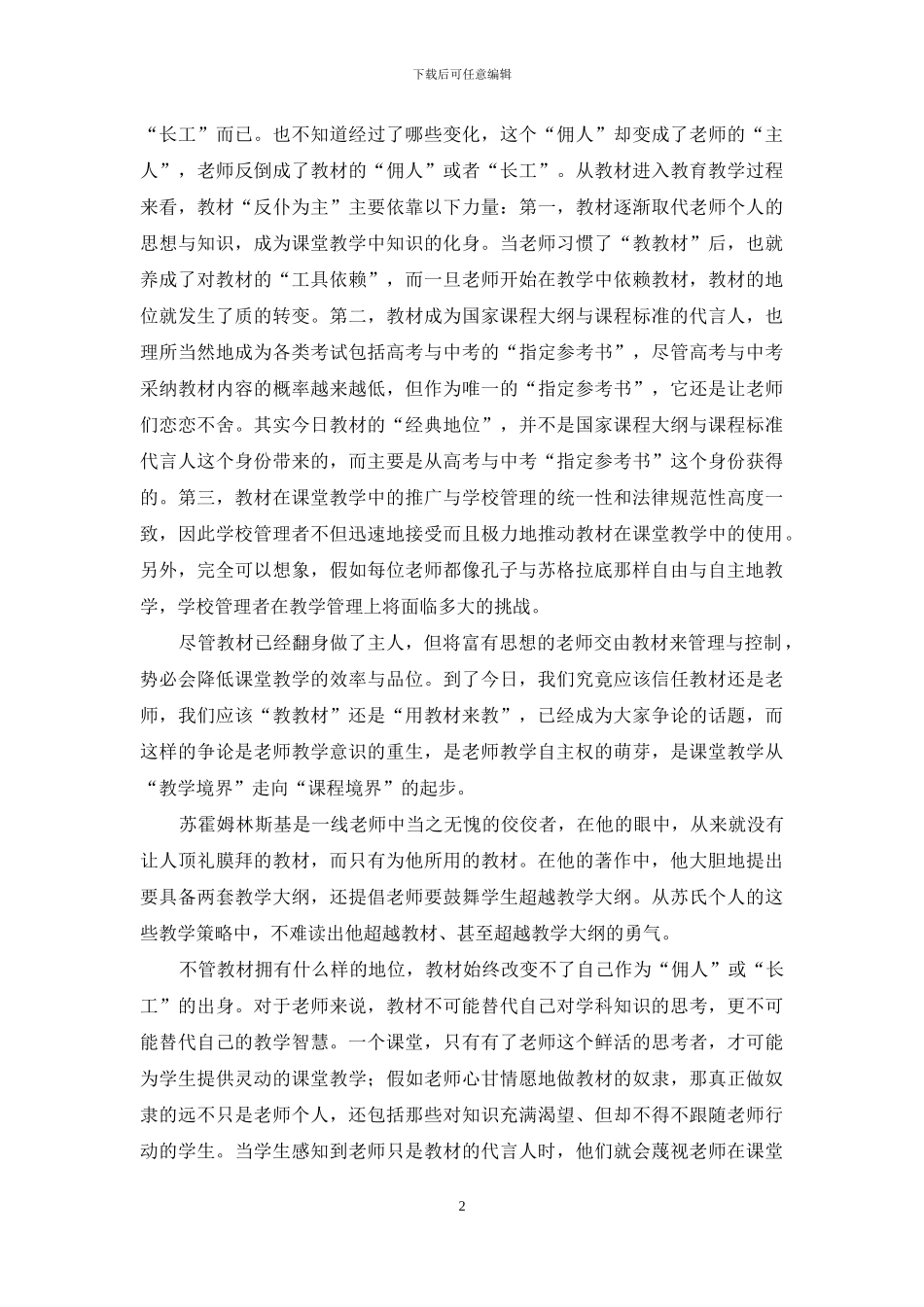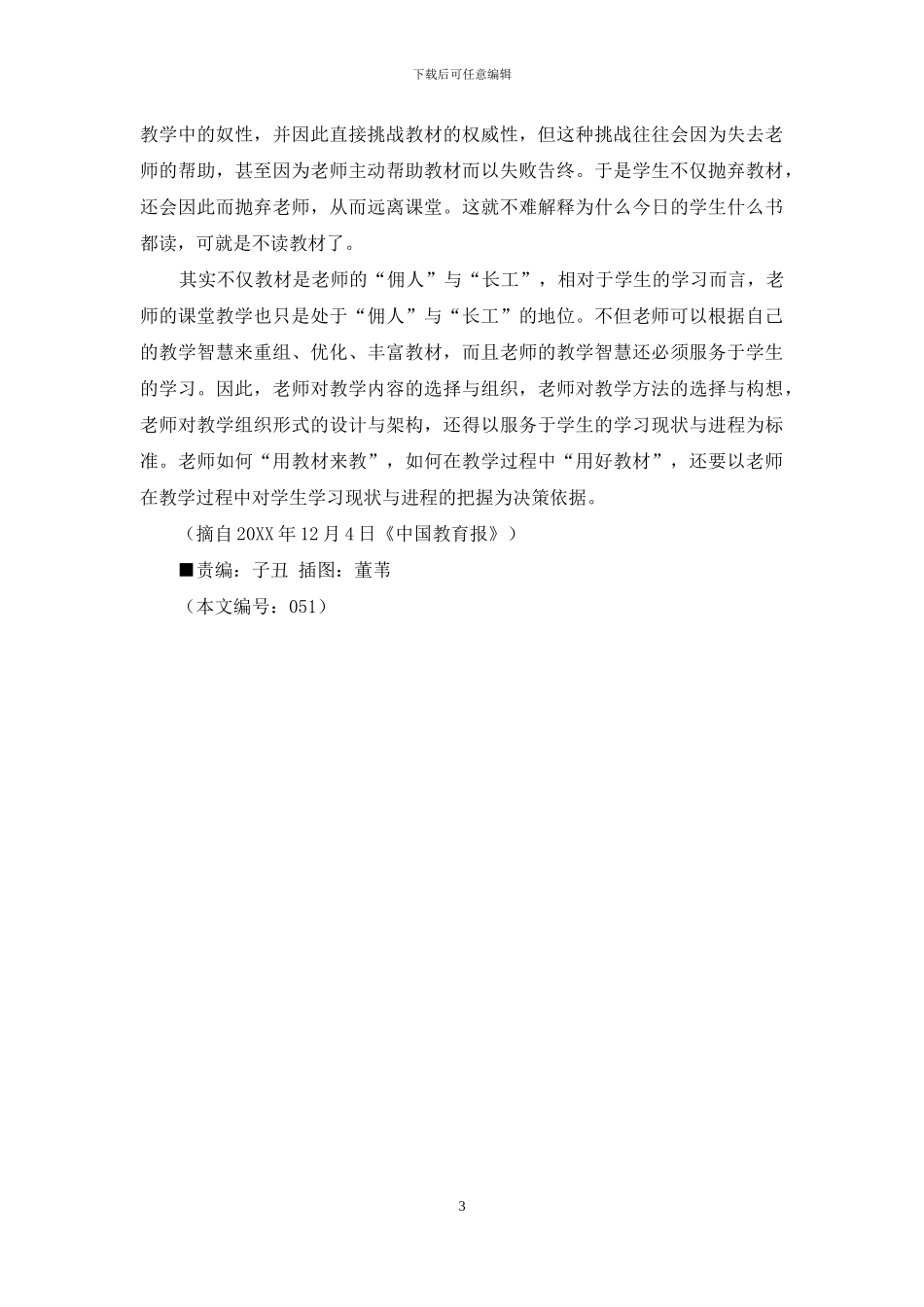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老师与教材:谁是主,谁是仆老师与教材:谁是主,谁是仆 孔子是东方老师的始祖,苏格拉底是西方智者的先师。虽然两位素不相识 ,但他们在教育教学上却都不大重视“教材”。孔子的教育教学提倡“论而不著”,这意味着教育内容在人的思想之中而不在文字之上;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就更是强调在“一问一答”中揭示教育内容,这意味着教育内容是在教学过程中生成的,而不是事先策划并建构好的。应该说,在他们那个年代,根本就不存在今日的教材,他们也不会同意使用像今日这样的教材。隐隐约约能够感觉到他们对“教材”的担忧:有了教材就会抑制教学过程的生动性与生成性。 在今日的人看来,孔子与苏格拉底本身就是知识的化身,他们有能力将自己演绎成一本活教材,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思想与知识和外在的教学标准保持一致。但是随着教学知识的丰富,今日的老师已经不可能成为知识的化身,对教材的统一使用,既有利于学校对老师的法律规范管理,也有利于老师回避由于自己个性化理解而产生的教学偏差。 可是有了教材,似乎并没有为今日的老师带来更多的幸福,也没有为学校管理者减轻管理的负担。在孔子看来,老师是用自己的思想与知识来开展教学的,所以教育教学过程是老师脑力劳动强度最大之时,既要关注教育环境与教学情境的变化,同时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思想与学科知识。为了减轻老师的教学压力,我们用教材来分担老师的劳动强度,把学科知识根据教学进度进行分隔与组合。可是,原本很好的打算,却在课堂教学中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课堂教学不再是老师充分激活教学思想与展现自我教育智慧,而成了体力劳动般被动地完成教材规定的教学内容。更让我们担心的还在于,老师干体力劳动久了会形成简单思维:被动而又消极地肢解教材内容并简单地复制这些内容,从而丧失作为脑力劳动者应有的智慧——保持自己对教材内容的批判性占有,在课堂教学中葆有自己的积极心态与教学智慧。 教材只是用来帮助老师教学的,只是老师为搞好教学请来的“佣人”或者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长工”而已。也不知道经过了哪些变化,这个“佣人”却变成了老师的“主人”,老师反倒成了教材的“佣人”或者“长工”。从教材进入教育教学过程来看,教材“反仆为主”主要依靠以下力量:第一,教材逐渐取代老师个人的思想与知识,成为课堂教学中知识的化身。当老师习惯了“教教材”后,也就养成了对教材的“工具依赖”,而一旦老师开始在教学中依赖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