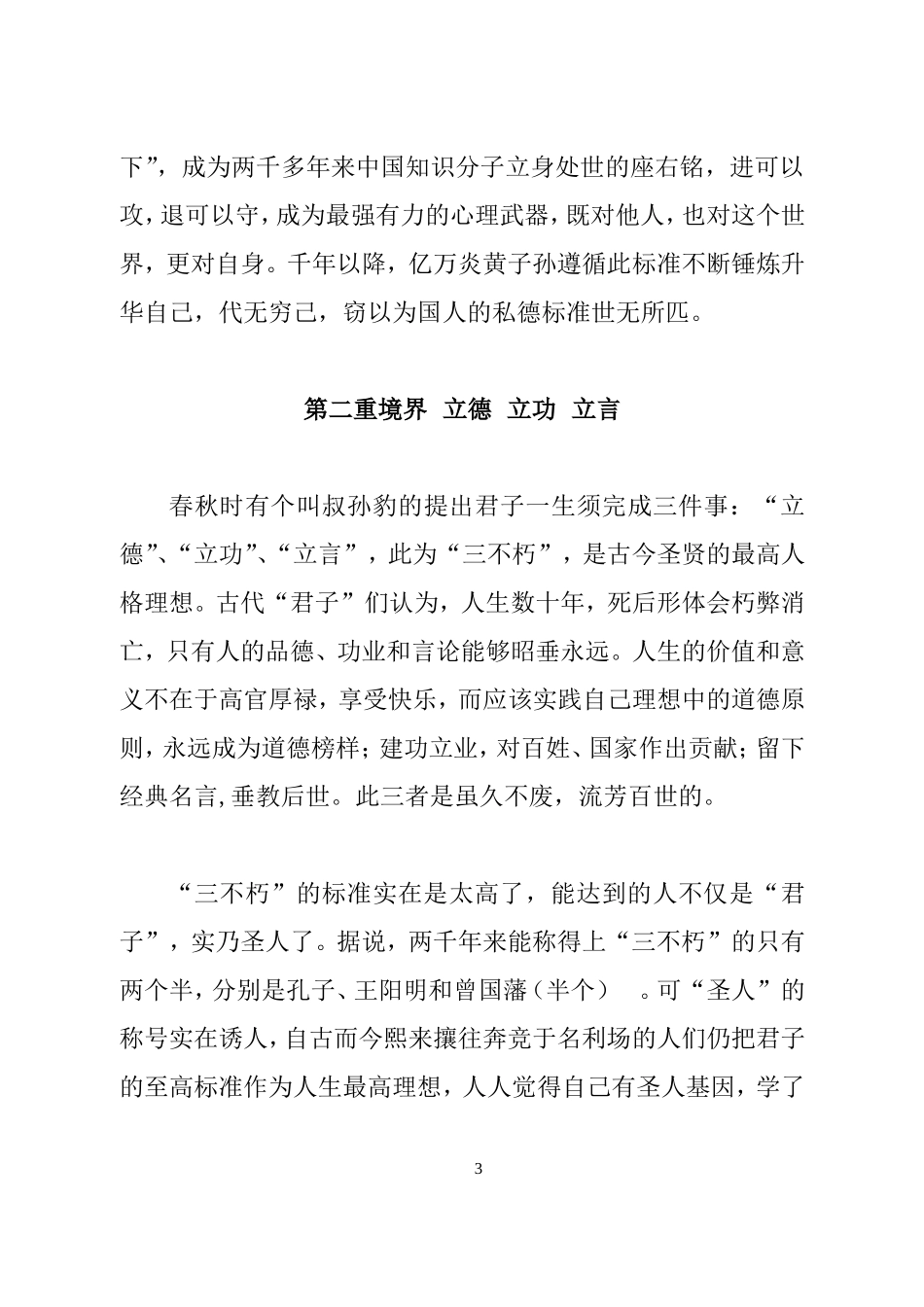君子的三重境界“君子”在先秦时代多指“君王之子”,着重强调政治地位的崇高。孔子为“君子”一词赋予了道德的含义,自此,“君子”一词有了德性。到汉代儒家被定为国教之后,“君子”标准便成了国民行为规范,人人遵守,流转千年。关于“君子”的研究层出不穷,规则繁复,要求日益提高,规矩日趋严密,终至提升到德治高于法治的地步,“以德治国”其实早已实行了千年。反思有关“君子”的标准与境界问题,确乎有助于裨益当下,继往开来。第一重境界君子的自我修养在儒家看来,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完人,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切实做到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然后孔子为世人定下了行为规范标准: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即所谓“九思”;后人又增加了新标准“四不”:不妄动、不徒语、不苟求、不虚行;乃至还有1“三费”、“三乐”等等各类要求,很有点类似今天我们的“五条例”、“八不准”。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的核心思想是“礼”。“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古有“礼”、“法”之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贵族遵照“礼”的要求开展道德约束,对普通民众则以“法(刑)”进行管理。孔子倡导以“仁”为核心的新“礼”念,“仁”为至高行为准则,乃至可以“杀身成仁”。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信条,推广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著有《礼论》,建立了等级制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这些本是社会伦理原则,是一种自我约束和约束他人的道德体系,相当于现在的规章制度,不具有法律效益,只不过古代的人们把这个看的比律法还要重要。等其被儒家用来作为尺子进而发展为“五常”、“三纲”的地步,统治者终于找到驾驭小民的利器,天下人都很容易地尽入彀中矣。君子标准的制定,预示着社会道德规范的进一步完善,人人可以照着规则修正自己,于是产生了自省、克己、忠恕、慎独等“君子价值观”。孟子将其归纳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2下”,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成为最强有力的心理武器,既对他人,也对这个世界,更对自身。千年以降,亿万炎黄子孙遵循此标准不断锤炼升华自己,代无穷己,窃以为国人的私德标准世无所匹。第二重境界立德立功立言春秋时有个叫叔孙豹的提出君子一生须完成三件事:“立德”、“立功”、“立言”,此为“三不朽”,是古今圣贤的最高人格理想。古代“君子”们认为,人生数十年,死后形体会朽弊消亡,只有人的品德、功业和言论能够昭垂永远。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高官厚禄,享受快乐,而应该实践自己理想中的道德原则,永远成为道德榜样;建功立业,对百姓、国家作出贡献;留下经典名言,垂教后世。此三者是虽久不废,流芳百世的。“三不朽”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能达到的人不仅是“君子”,实乃圣人了。据说,两千年来能称得上“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分别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半个)。可“圣人”的称号实在诱人,自古而今熙来攘往奔竞于名利场的人们仍把君子的至高标准作为人生最高理想,人人觉得自己有圣人基因,学了3几天“君子”规就开始追求“不朽”了,于是历代以来均不鲜见追名逐利的短期行为,假仁假义、外廉内贪的道德作秀引领败坏了社会风气,将“立德”的要求抛到了九天云外;各处可见急于“立功”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古时君子视为生命的“立言”,著书撰文者所求的也不再是不朽,而是速成,而速成者自然就难免乎速朽。自诩“圣人”的代不乏人,有“圣人”思维的更是随处可见。无论说的啥,官大就正确,无论懂不懂,动辄指点一番,无论有没有水平,白送都没人看的垃圾,竟然也当成“著作”。“君子”们的圣人情结实在是太深沉了,圣人思维已经刻到了骨子里。可如果,抽去这圣人目标,“君子”们还有努力的方向么?第三重境界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君子”的完美人生道路设计。修身不是为成仙,儒家讲道德和讲政治是紧密联结的,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