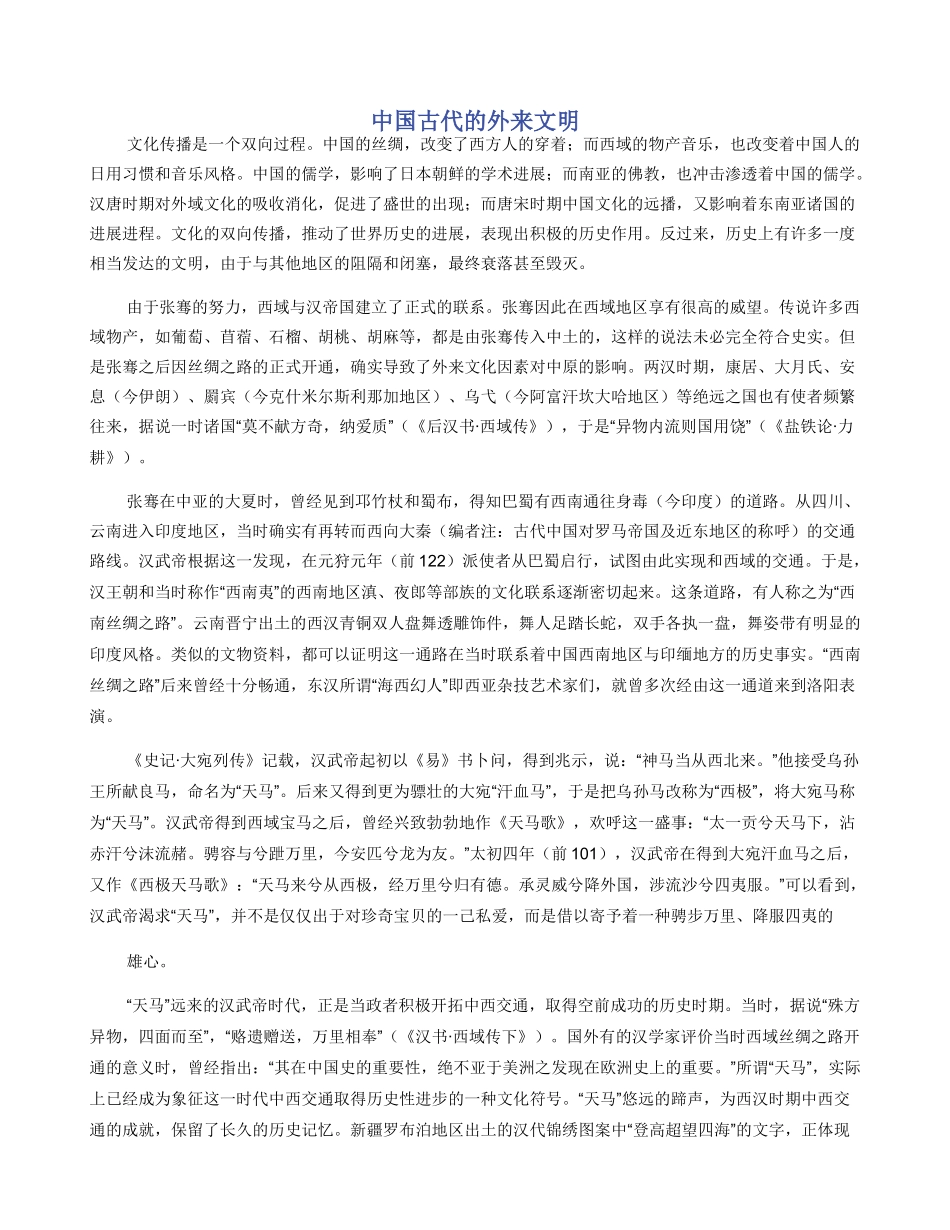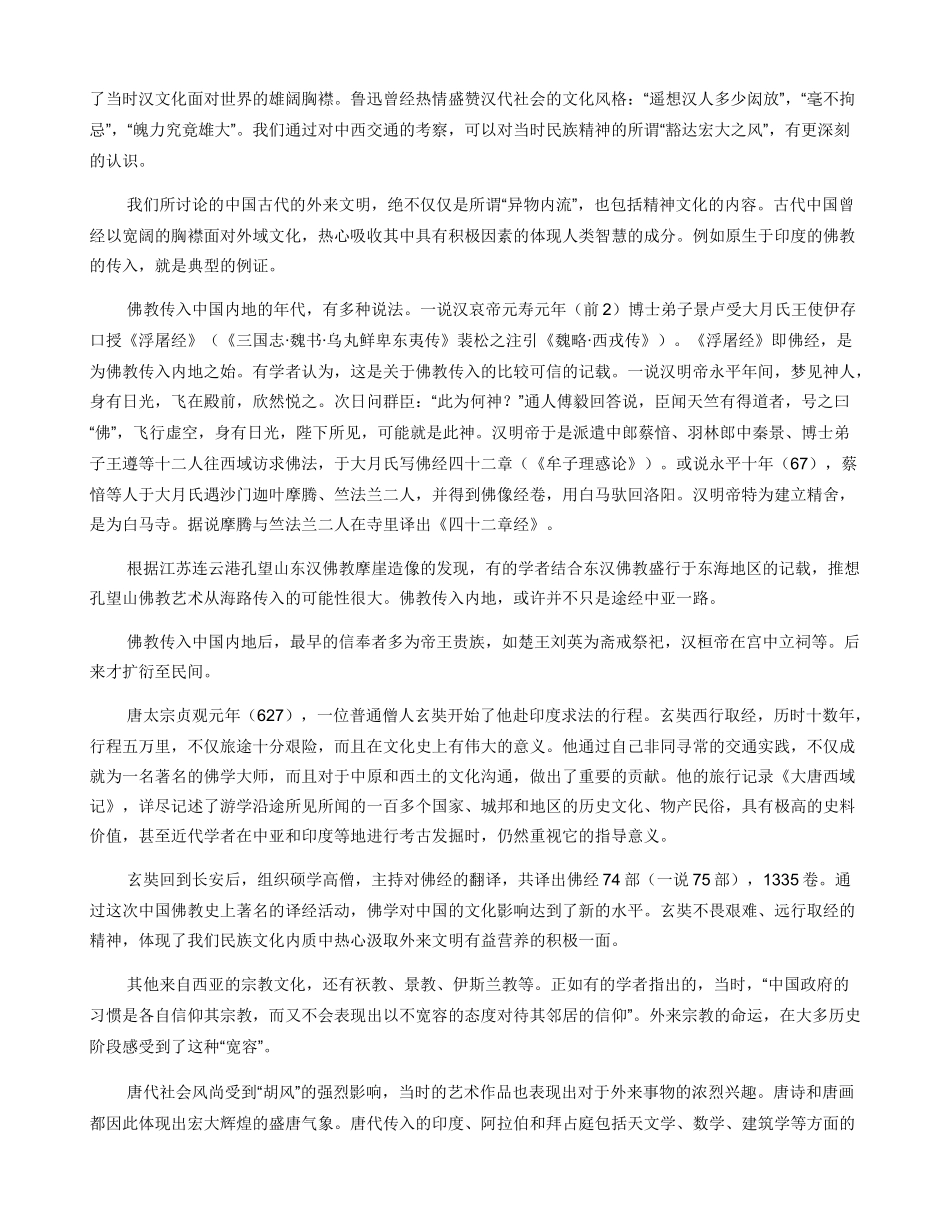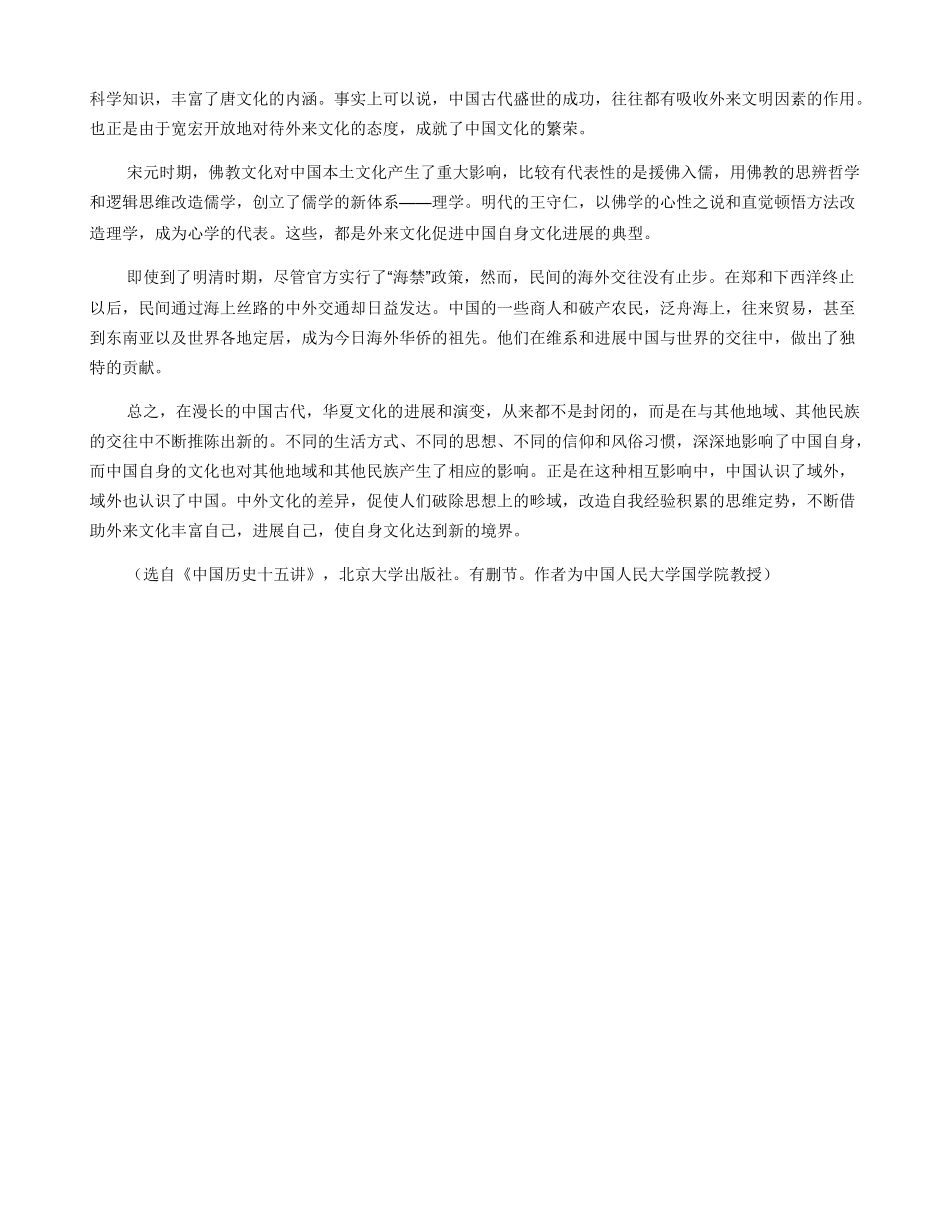中国古代的外来文明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过程。中国的丝绸,改变了西方人的穿着;而西域的物产音乐,也改变着中国人的日用习惯和音乐风格。中国的儒学,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学术进展;而南亚的佛教,也冲击渗透着中国的儒学。汉唐时期对外域文化的吸收消化,促进了盛世的出现;而唐宋时期中国文化的远播,又影响着东南亚诸国的进展进程。文化的双向传播,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展,表现出积极的历史作用。反过来,历史上有许多一度相当发达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的阻隔和闭塞,最终衰落甚至毁灭。由于张骞的努力,西域与汉帝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张骞因此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传说许多西域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张骞传入中土的,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是张骞之后因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确实导致了外来文化因素对中原的影响。两汉时期,康居、大月氏、安息(今伊朗)、罽宾(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地区)、乌弋(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等绝远之国也有使者频繁往来,据说一时诸国“莫不献方奇,纳爱质”(《后汉书·西域传》),于是“异物内流则国用饶”(《盐铁论·力耕》)。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从四川、云南进入印度地区,当时确实有再转而西向大秦(编者注: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的交通路线。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在元狩元年(前 122)派使者从巴蜀启行,试图由此实现和西域的交通。于是,汉王朝和当时称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区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这条道路,有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云南晋宁出土的西汉青铜双人盘舞透雕饰件,舞人足踏长蛇,双手各执一盘,舞姿带有明显的印度风格。类似的文物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通路在当时联系着中国西南地区与印缅地方的历史事实。“西南丝绸之路”后来曾经十分畅通,东汉所谓“海西幻人”即西亚杂技艺术家们,就曾多次经由这一通道来到洛阳表演。《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起初以《易》书卜问,得到兆示,说:“神马当从西北来。”他接受乌孙王所献良马,命名为“天马”。后来又得到更为骠壮的大宛“汗血马”,于是把乌孙马改称为“西极”,将大宛马称为“天马”。汉武帝得到西域宝马之后,曾经兴致勃勃地作《天马歌》,欢呼这一盛事:“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太初四年(前 101),汉武帝在得到大宛汗血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