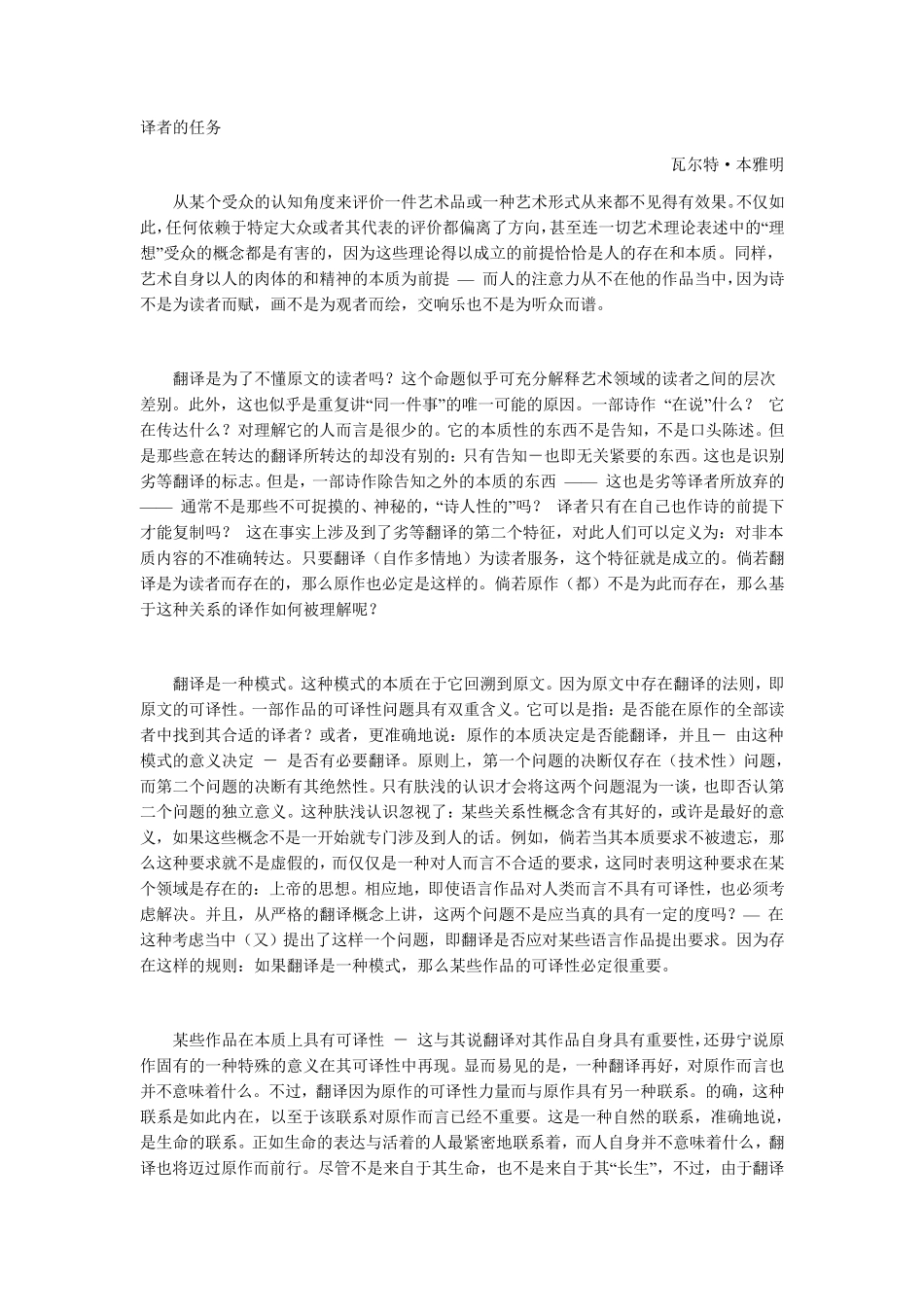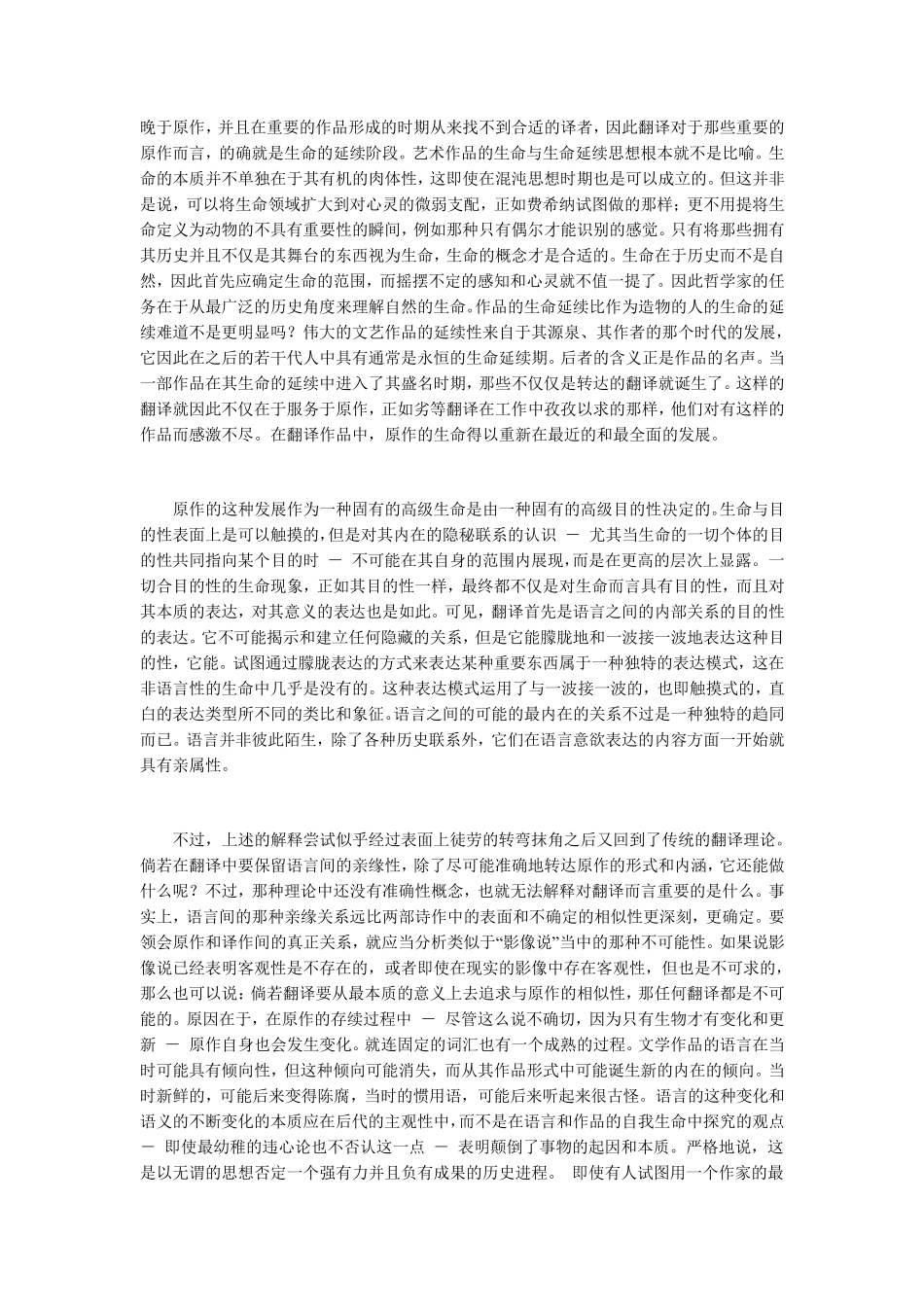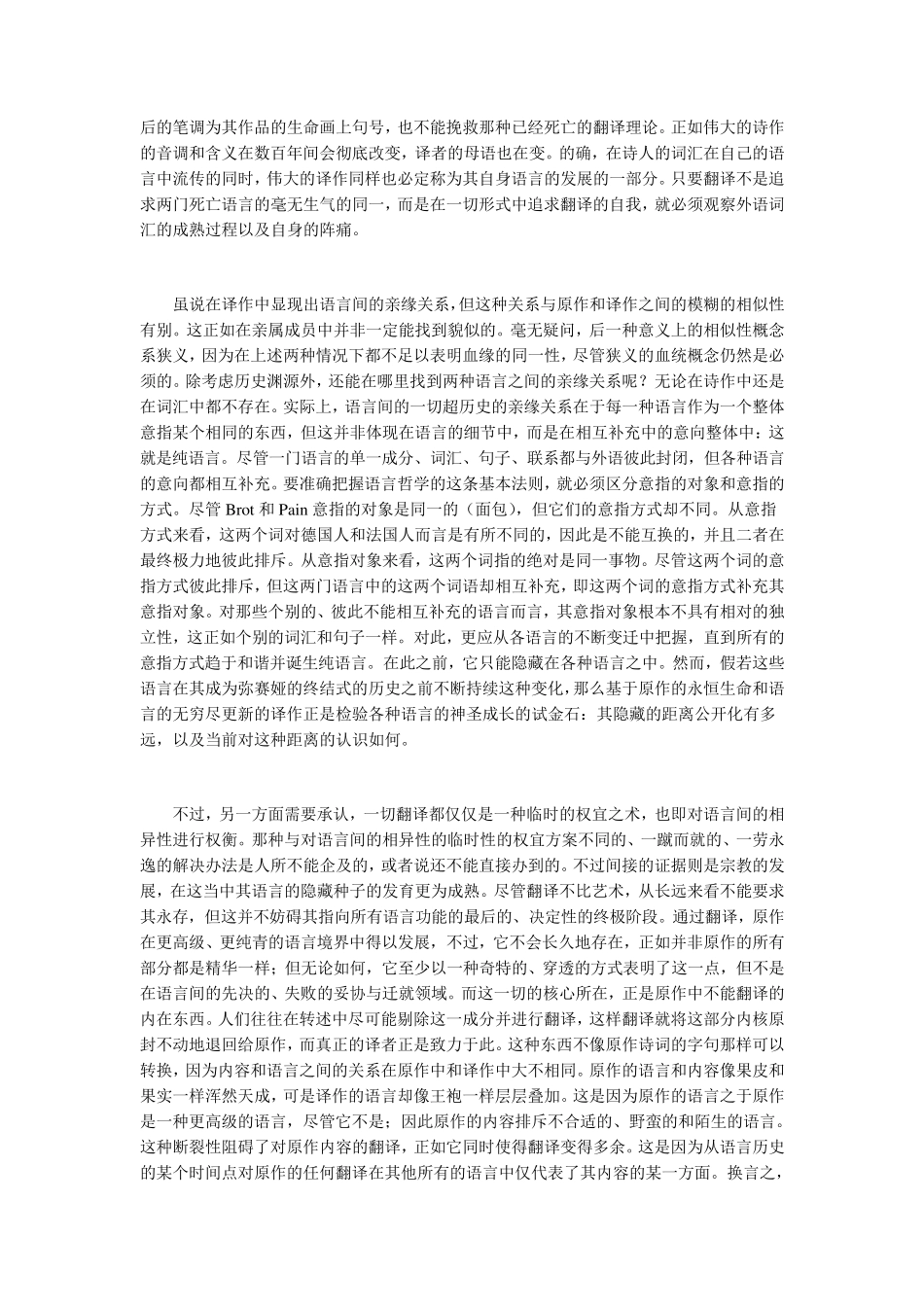译者的任务 瓦尔特·本雅明 从某个受众的认知角度来评价一件艺术品或一种艺术形式从来都不见得有效果。不仅如此,任何依赖于特定大众或者其代表的评价都偏离了方向,甚至连一切艺术理论表述中的“理想” 受众的概念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些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恰恰是人的存在和本质。同样,艺术自身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本质为前提 — 而人的注意力从不在他的作品当中,因为诗不是为读者而赋,画不是为观者而绘,交响乐也不是为听众而谱。 翻译是为了不懂原文的读者吗?这个命题似乎可充分解释艺术领域的读者之间的层次差别。此外,这也似乎是重复讲“同一件事” 的唯一可能的原因。一部诗作 “在说” 什么? 它在传达什么?对理解它的人而言是很少的。它的本质性的东西不是告知,不是口头陈述。但是那些意在转达的翻译所转达的却没有别的:只有告知-也即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也是识别劣等翻译的标志。但是,一部诗作除告知之外的本质的东西 — — 这也是劣等译者所放弃的 — — 通常不是那些不可捉摸的、神秘的,“诗人性的” 吗? 译者只有在自己也作诗的前提下才能复制吗? 这在事实上涉及到了劣等翻译的第二个特征,对此人们可以定义为:对非本质内容的不准确转达。只要翻译(自作多情地)为读者服务,这个特征就是成立的。倘若翻译是为读者而存在的,那么原作也必定是这样的。倘若原作(都)不是为此而存在,那么基于这种关系的译作如何被理解呢? 翻译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本质在于它回溯到原文。因为原文中存在翻译的法则,即原文的可译性。一部作品的可译性问题具有双重含义。它可以是指:是否能在原作的全部读者中找到其合适的译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原作的本质决定是否能翻译,并且- 由这种模式的意义决定 - 是否有必要翻译。原则上,第一个问题的决断仅存在(技术性)问题,而第二个问题的决断有其绝然性。只有肤浅的认识才会将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也即否认第二个问题的独立意义。这种肤浅认识忽视了:某些关系性概念含有其好的,或许是最好的意义,如果这些概念不是一开始就专门涉及到人的话。例如,倘若当其本质要求不被遗忘,那么这种要求就不是虚假的,而仅仅是一种对人而言不合适的要求,这同时表明这种要求在某个领域是存在的:上帝的思想。相应地,即使语言作品对人类而言不具有可译性,也必须考虑解决。并且,从严格的翻译概念上讲,这两个问题不是应当真的具有一定的度吗?— 在这种考虑当中(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