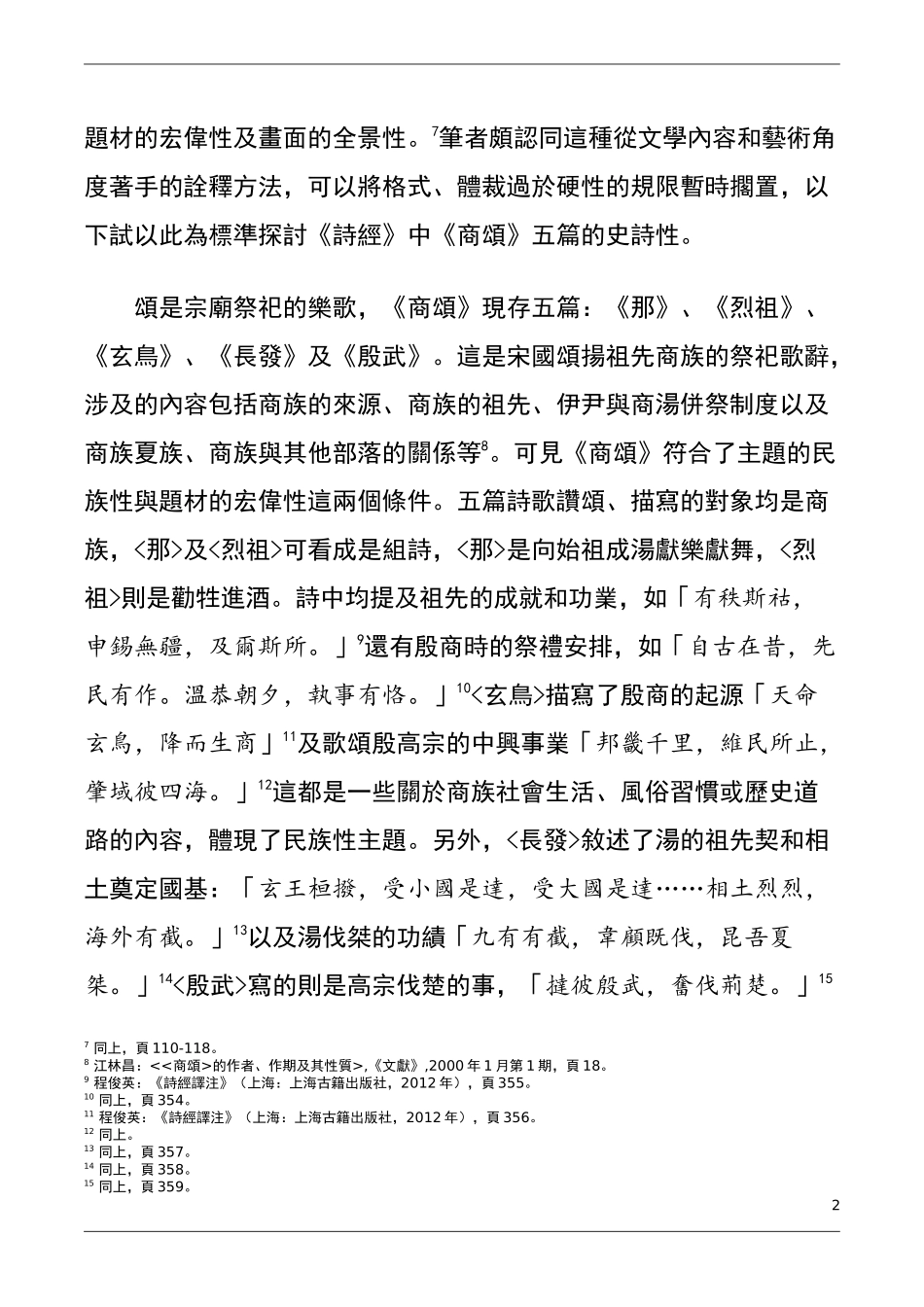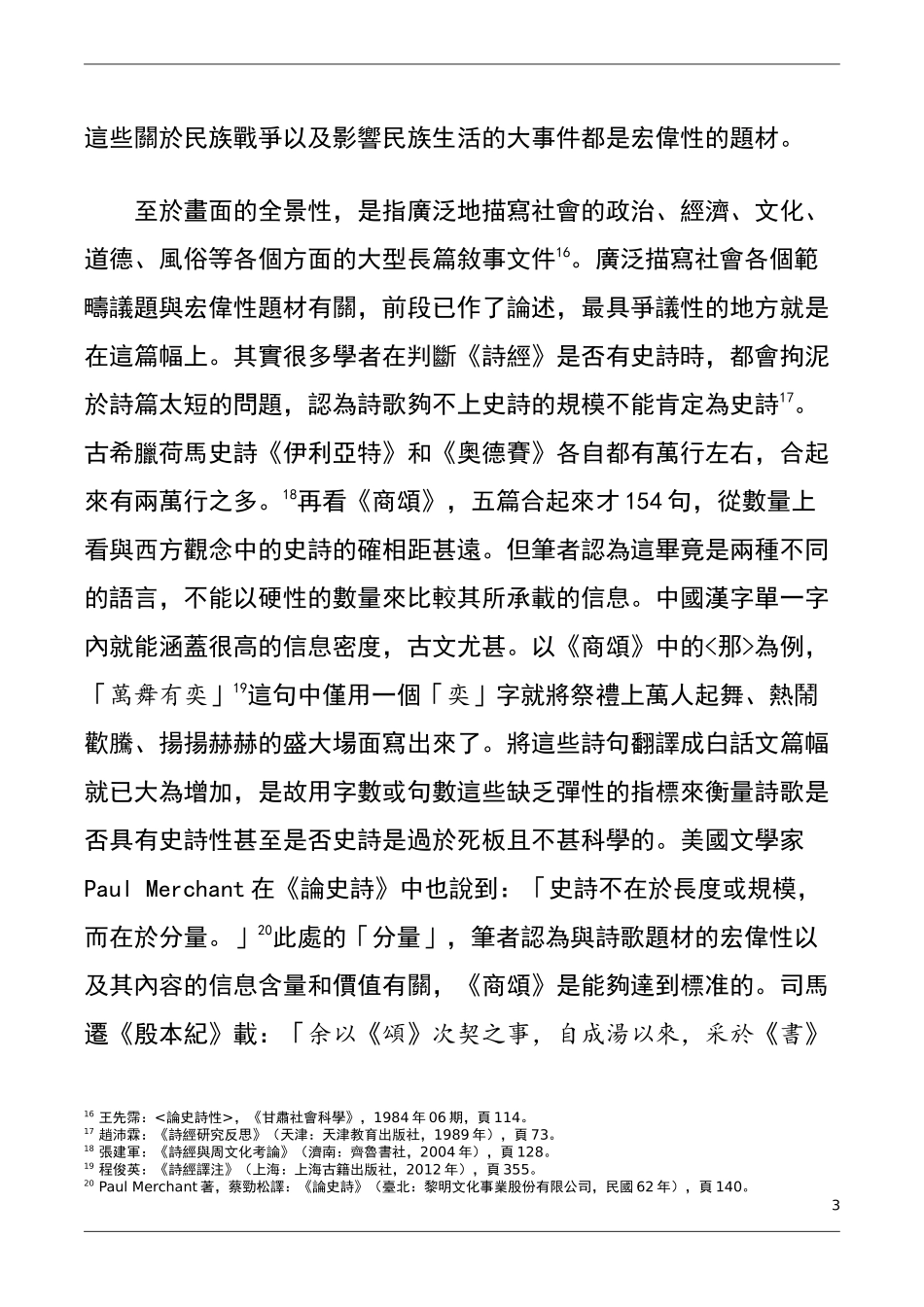從《商頌》論《詩經》的史詩性 將「史詩」引入詩經學研究是「五四」後才出現的現象,主要源於西方詩歌理論的影響。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首先提出「史詩」的概念,他將當時古希臘文學作品分為史詩、抒情詩和戲劇。黑格爾的《美學》在其基礎上對此進行了更詳細的論述,并認為「中國人卻沒有民族史詩」1。當然,那時尚未有《詩經》的德文譯本,故許多學者認為黑格爾對此的論斷不足為訓。近代學者對於《詩經》中史詩的討論,多集中在《大雅》中《生民》、《公劉》、《綿》、《皇矣》及《大明》五篇,各人眾說紛紜,學識並不統一。但近代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詩經》中有史詩,至少存在上述的五大史詩。2除此之外,《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和《常武》,以及《商頌》五篇均被部份學者列入史詩範圍。3王先霈先生認為史詩是一個多義名詞:作為一種文體,史詩指的是詩歌中的一種特殊的形式。4既然是從文體、形式的角度看,限制自然比較多而且是硬性的。「史詩」畢竟是西方的詩歌概念,是一個「舶來品」5,拿中國早期文學作品《詩經》來進行比附實在難以完全扣合,是故讓各學者各執己見爭議不斷。但如果從美學的觀念來看,史詩所指的對象要廣泛得多,同時又有更加確定的內涵6。王先霈先生把帶有史詩美學的因素稱為「史詩性」,主要體現在主題的民族性、1 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170。2 于新:《「詩經」研究概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 年),頁 133。3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74。4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 年 06 期,頁 110。5 張建軍:《詩經與周文化考論》(濟南:齊魯書社,2004 年),頁 128。6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 年 06 期,頁 110。1題材的宏偉性及畫面的全景性。7筆者頗認同這種從文學內容和藝術角度著手的詮釋方法,可以將格式、體裁過於硬性的規限暫時擱置,以下試以此為標準探討《詩經》中《商頌》五篇的史詩性。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商頌》現存五篇:《那》、《烈祖》、《玄鳥》、《長發》及《殷武》。這是宋國頌揚祖先商族的祭祀歌辭,涉及的內容包括商族的來源、商族的祖先、伊尹與商湯併祭制度以及商族夏族、商族與其他部落的關係等8。可見《商頌》符合了主題的民族性與題材的宏偉性這兩個條件。五篇詩歌讚頌、描寫的對象均是商族,<那>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