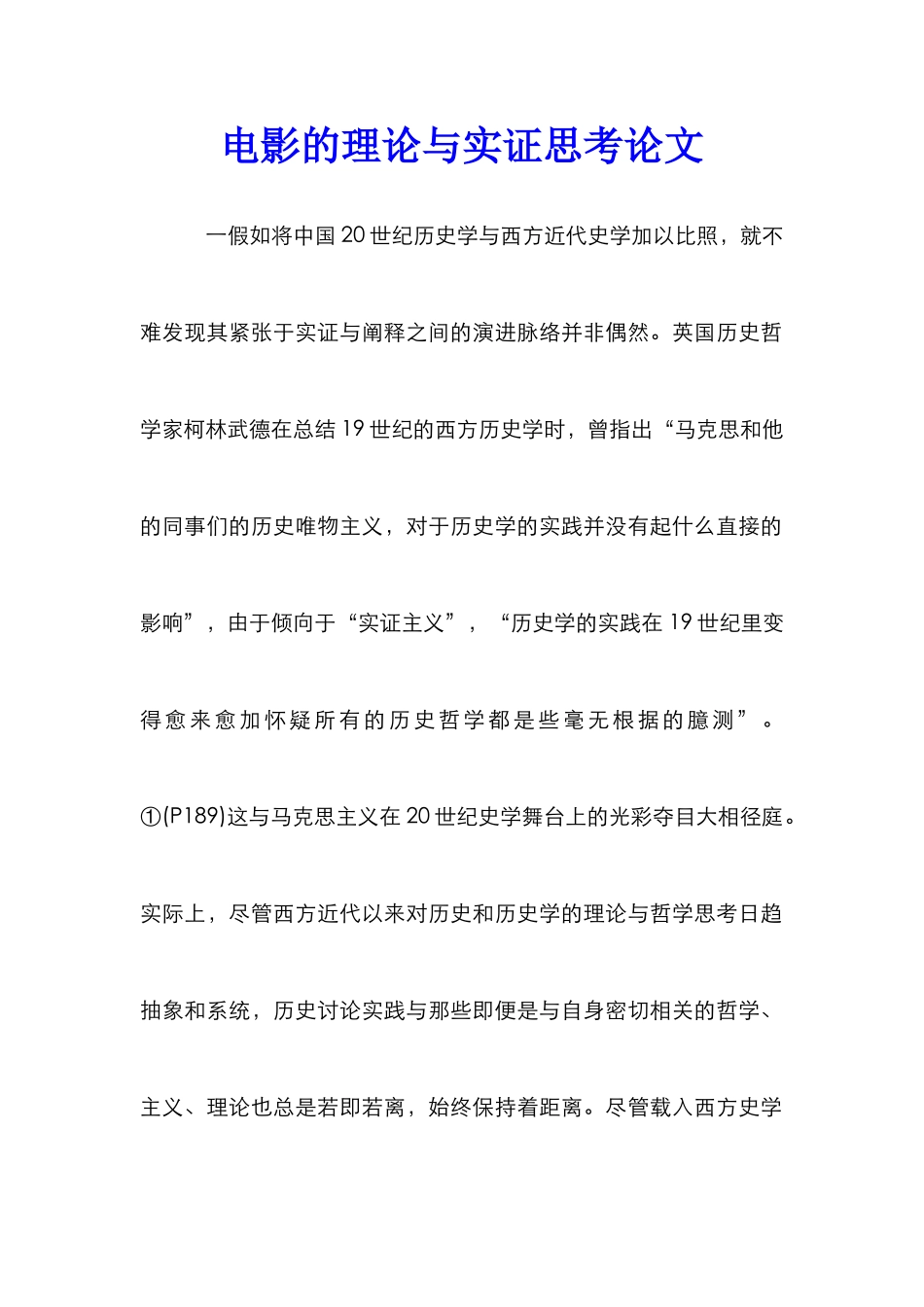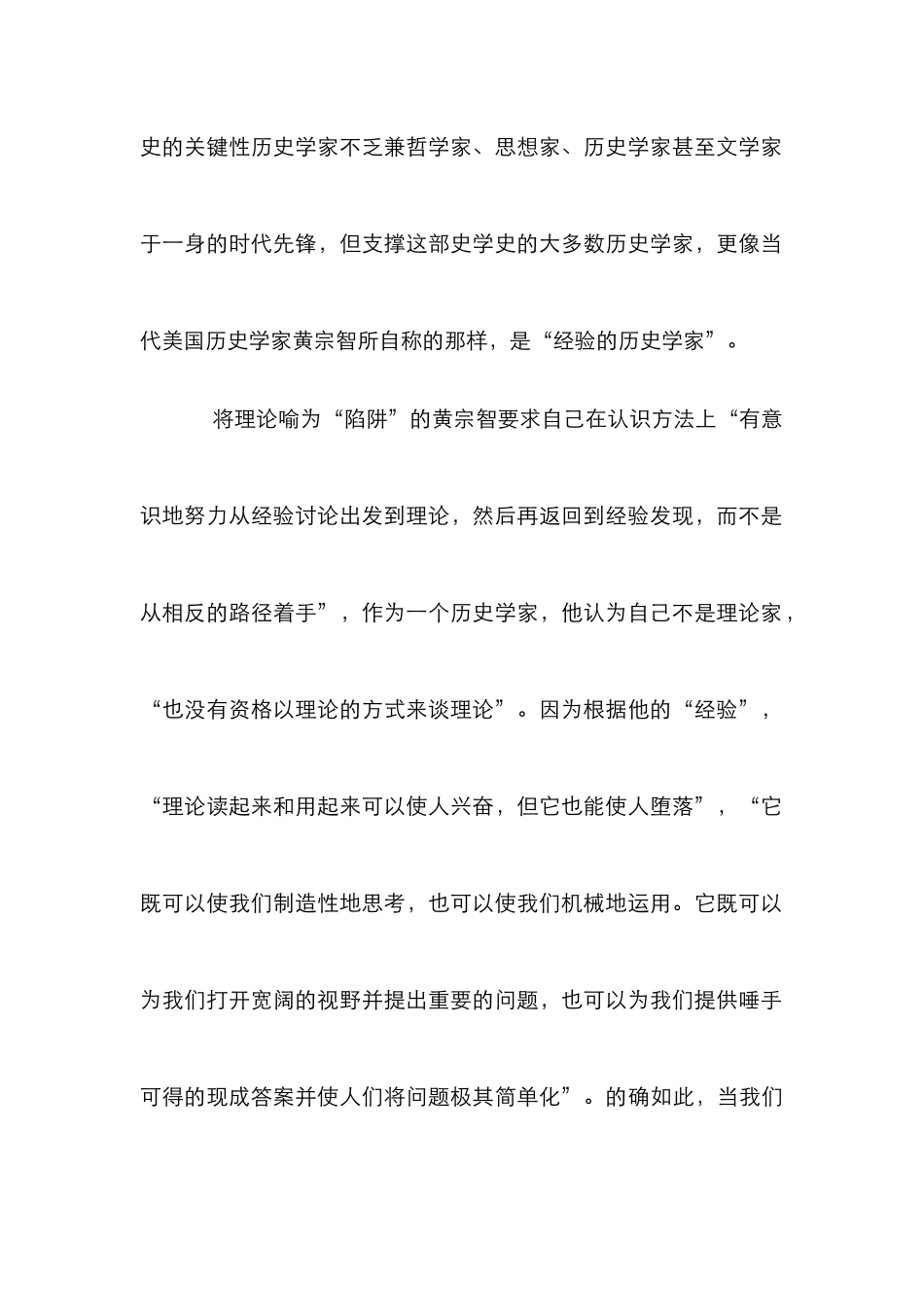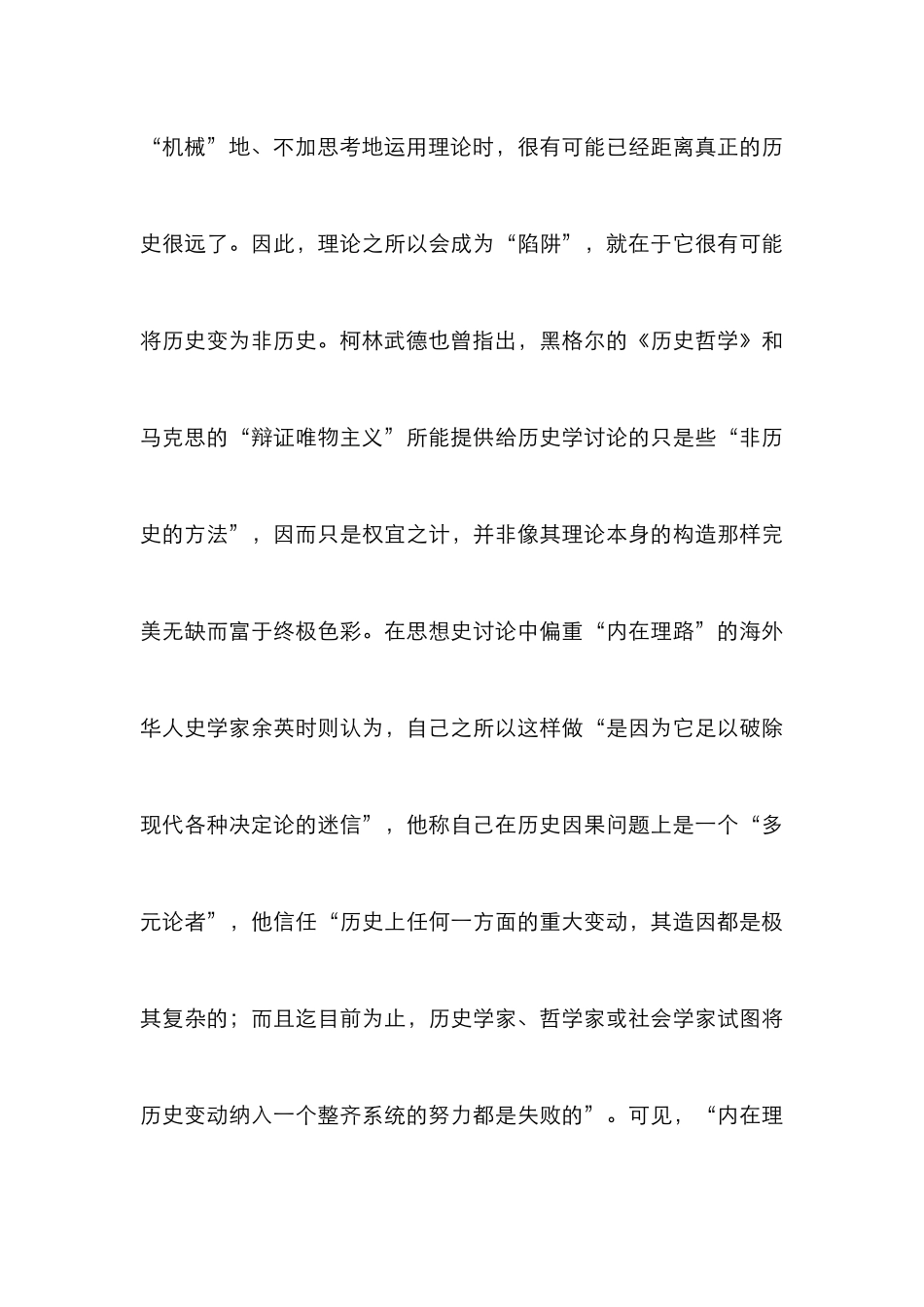电影的理论与实证思考论文 一假如将中国 20 世纪历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加以比照,就不难发现其紧张于实证与阐释之间的演进脉络并非偶然。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总结 19 世纪的西方历史学时,曾指出“马克思和他的同事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学的实践并没有起什么直接的影响”,由于倾向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实践在 19 世纪里变得愈来愈加怀疑所有的历史哲学都是些毫无根据的臆测”。①(P189)这与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史学舞台上的光彩夺目大相径庭。实际上,尽管西方近代以来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理论与哲学思考日趋抽象和系统,历史讨论实践与那些即便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哲学、主义、理论也总是若即若离,始终保持着距离。尽管载入西方史学史的关键性历史学家不乏兼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甚至文学家于一身的时代先锋,但支撑这部史学史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更像当代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所自称的那样,是“经验的历史学家”。 将理论喻为“陷阱”的黄宗智要求自己在认识方法上“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讨论出发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经验发现,而不是从相反的路径着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认为自己不是理论家,“也没有资格以理论的方式来谈理论”。因为根据他的“经验”,“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它既可以使我们制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宽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的确如此,当我们“机械”地、不加思考地运用理论时,很有可能已经距离真正的历史很远了。因此,理论之所以会成为“陷阱”,就在于它很有可能将历史变为非历史。柯林武德也曾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所能提供给历史学讨论的只是些“非历史的方法”,因而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像其理论本身的构造那样完美无缺而富于终极色彩。在思想史讨论中偏重“内在理路”的海外华人史学家余英时则认为,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足以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的迷信”,他称自己在历史因果问题上是一个“多元论者”,他信任“历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变动,其造因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迄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可见,“内在理路”说即是对理论“陷阱”的回应,这一讨论途径是否有被同化为“理论”形式的可能姑且不论,但其“内化”取向所包含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