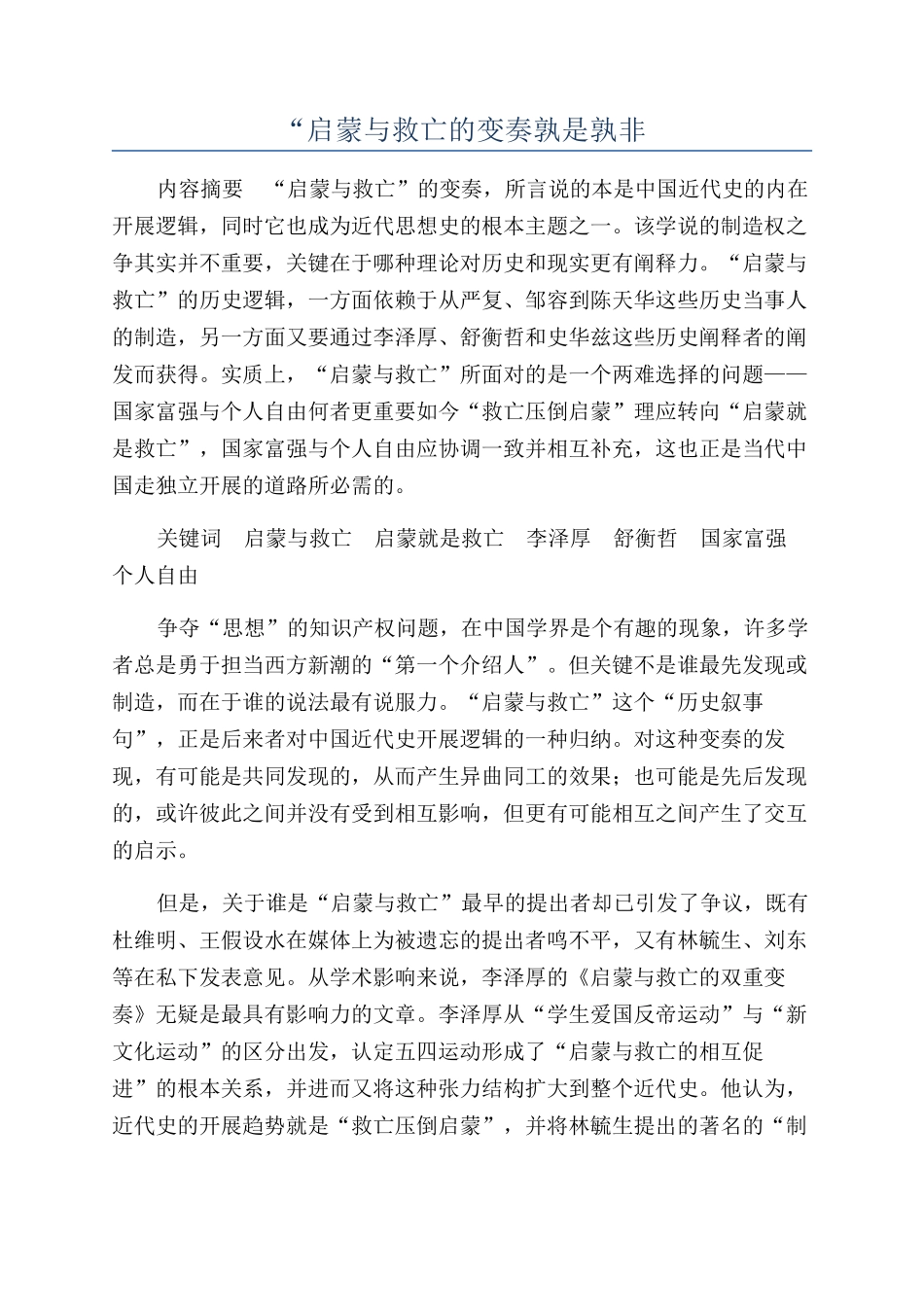“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孰是孰非内容摘要 “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所言说的本是中国近代史的内在开展逻辑,同时它也成为近代思想史的根本主题之一。该学说的制造权之争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哪种理论对历史和现实更有阐释力。“启蒙与救亡”的历史逻辑,一方面依赖于从严复、邹容到陈天华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制造,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李泽厚、舒衡哲和史华兹这些历史阐释者的阐发而获得。实质上,“启蒙与救亡”所面对的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何者更重要如今“救亡压倒启蒙”理应转向“启蒙就是救亡”,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应协调一致并相互补充,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走独立开展的道路所必需的。关键词 启蒙与救亡 启蒙就是救亡 李泽厚 舒衡哲 国家富强 个人自由争夺“思想”的知识产权问题,在中国学界是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学者总是勇于担当西方新潮的“第一个介绍人”。但关键不是谁最先发现或制造,而在于谁的说法最有说服力。“启蒙与救亡”这个“历史叙事句”,正是后来者对中国近代史开展逻辑的一种归纳。对这种变奏的发现,有可能是共同发现的,从而产生异曲同工的效果;也可能是先后发现的,或许彼此之间并没有受到相互影响,但更有可能相互之间产生了交互的启示。但是,关于谁是“启蒙与救亡”最早的提出者却已引发了争议,既有杜维明、王假设水在媒体上为被遗忘的提出者鸣不平,又有林毓生、刘东等在私下发表意见。从学术影响来说,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无疑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文章。李泽厚从“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分出发,认定五四运动形成了“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的根本关系,并进而又将这种张力结构扩大到整个近代史。他认为,近代史的开展趋势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并将林毓生提出的著名的“制造性的转换”(creativetranformation)转而变为“转换性的制造”,从社会体制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的两个层面来面对如何转化传统的问题。但是,李泽厚本人对此并不认同,这是因为他声称与舒衡哲早就结识。根据李泽厚自己的回忆,1981 年之前舒衡哲就来过北京,李泽厚请她吃过饭并做过几次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长谈。实际上,从 1979 年 2 月到1980 年 6 月,舒衡哲就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1 年李泽厚到美国也是应舒衡哲的邀请,据称他们再次讨论过近似的问题。在此,笔者既不想为舒衡哲匆忙翻案,更不想替李泽厚打抱不平,只是想给出两个根本推断。一个是“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