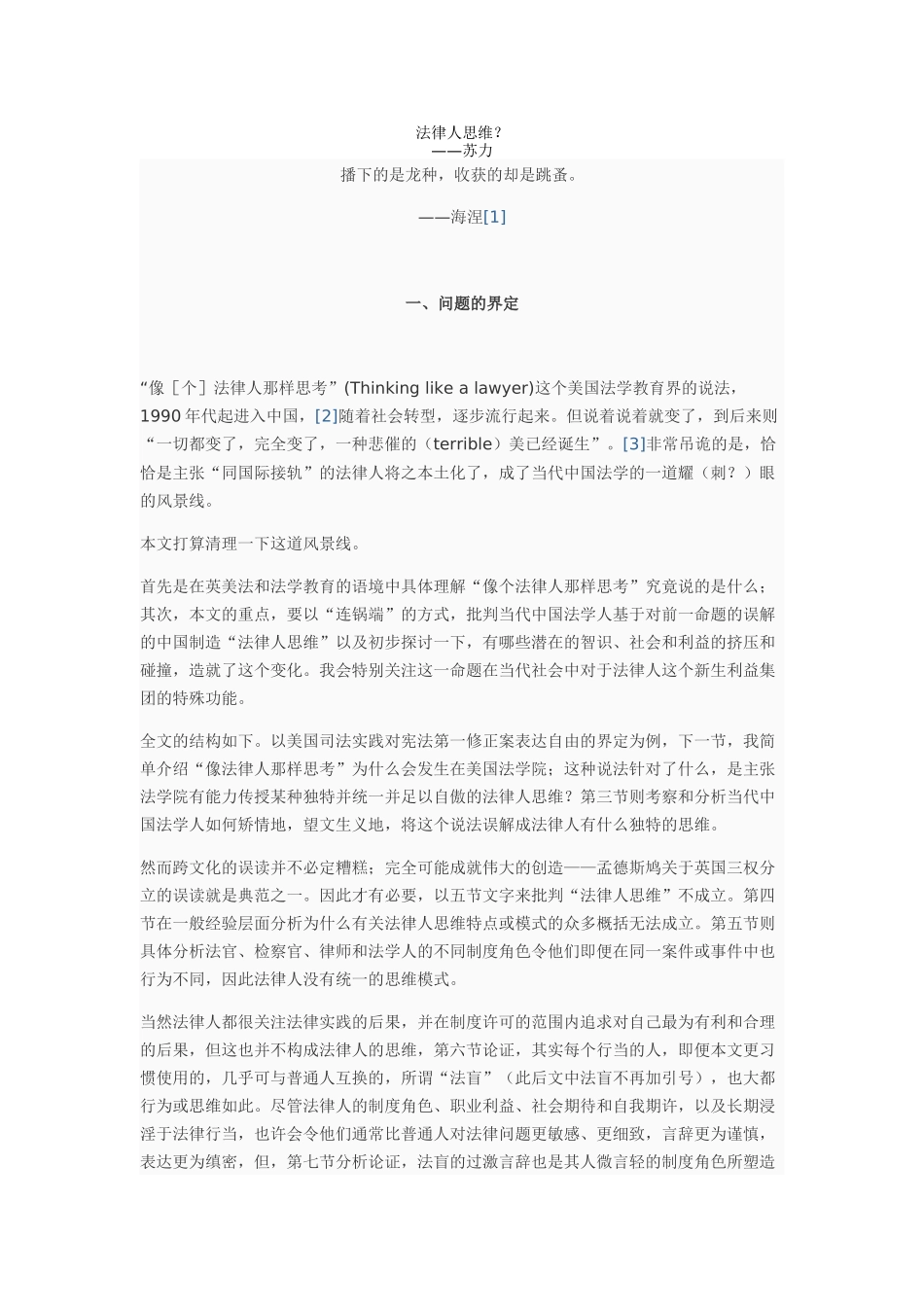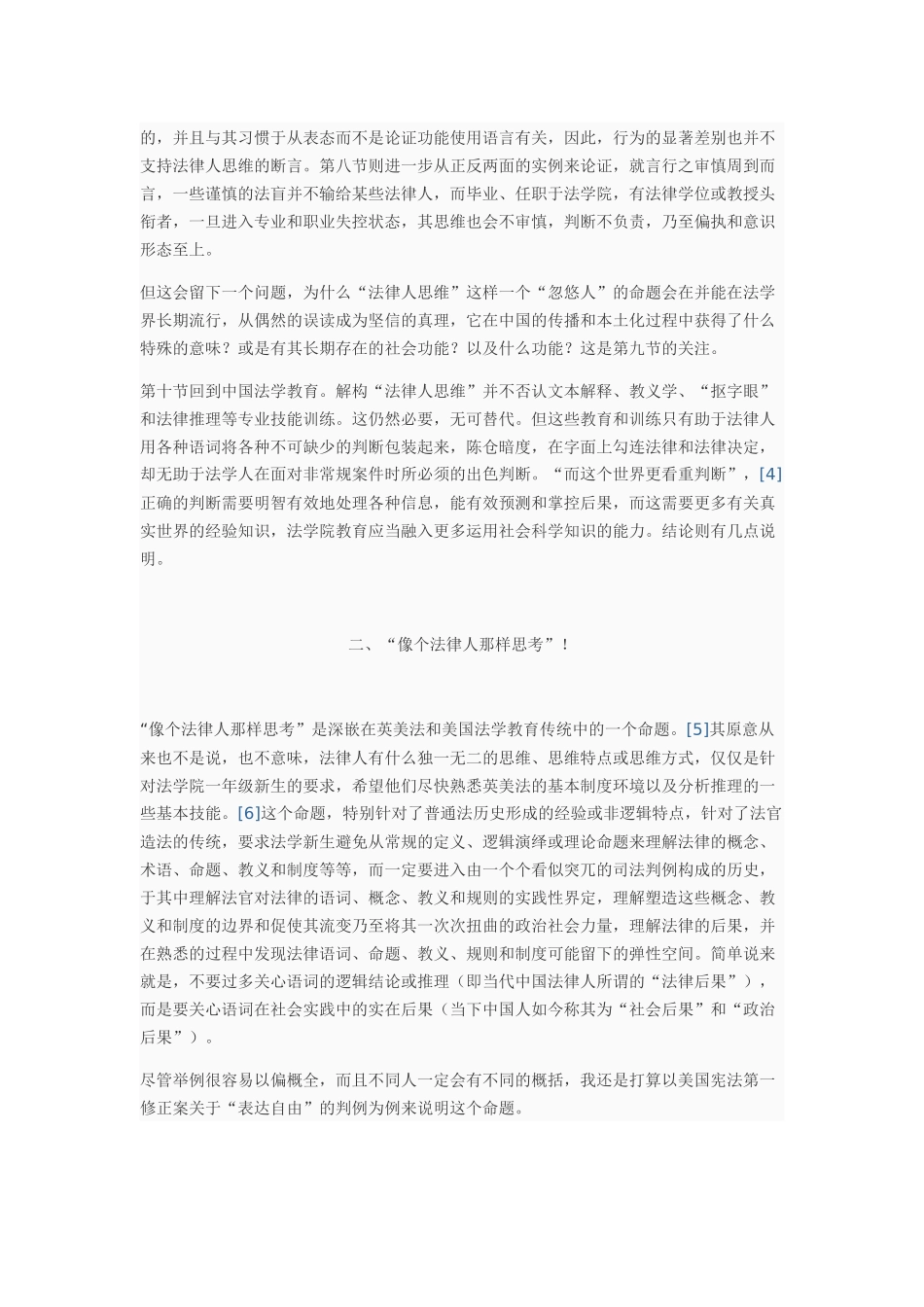法律人思维?——苏力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1] 一、问题的界定 “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lawyer)这个美国法学教育界的说法,1990 年代起进入中国,[2]随着社会转型,逐步流行起来。但说着说着就变了,到后来则“一切都变了,完全变了,一种悲催的(terrible)美已经诞生”。[3]非常吊诡的是,恰恰是主张“同国际接轨”的法律人将之本土化了,成了当代中国法学的一道耀(刺?)眼的风景线。本文打算清理一下这道风景线。首先是在英美法和法学教育的语境中具体理解“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究竟说的是什么;其次,本文的重点,要以“连锅端”的方式,批判当代中国法学人基于对前一命题的误解的中国制造“法律人思维”以及初步探讨一下,有哪些潜在的智识、社会和利益的挤压和碰撞,造就了这个变化。我会特别关注这一命题在当代社会中对于法律人这个新生利益集团的特殊功能。全文的结构如下。以美国司法实践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表达自由的界定为例,下一节,我简单介绍“像法律人那样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在美国法学院;这种说法针对了什么,是主张法学院有能力传授某种独特并统一并足以自傲的法律人思维?第三节则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法学人如何矫情地,望文生义地,将这个说法误解成法律人有什么独特的思维。然而跨文化的误读并不必定糟糕;完全可能成就伟大的创造——孟德斯鸠关于英国三权分立的误读就是典范之一。因此才有必要,以五节文字来批判“法律人思维”不成立。第四节在一般经验层面分析为什么有关法律人思维特点或模式的众多概括无法成立。第五节则具体分析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人的不同制度角色令他们即便在同一案件或事件中也行为不同,因此法律人没有统一的思维模式。当然法律人都很关注法律实践的后果,并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对自己最为有利和合理的后果,但这也并不构成法律人的思维,第六节论证,其实每个行当的人,即便本文更习惯使用的,几乎可与普通人互换的,所谓“法盲”(此后文中法盲不再加引号),也大都行为或思维如此。尽管法律人的制度角色、职业利益、社会期待和自我期许,以及长期浸淫于法律行当,也许会令他们通常比普通人对法律问题更敏感、更细致,言辞更为谨慎,表达更为缜密,但,第七节分析论证,法盲的过激言辞也是其人微言轻的制度角色所塑造的,并且与其习惯于从表态而不是论证功能使用语言有关,因此,行为的显著差别也并不支持法律人思维的断言。第八节则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