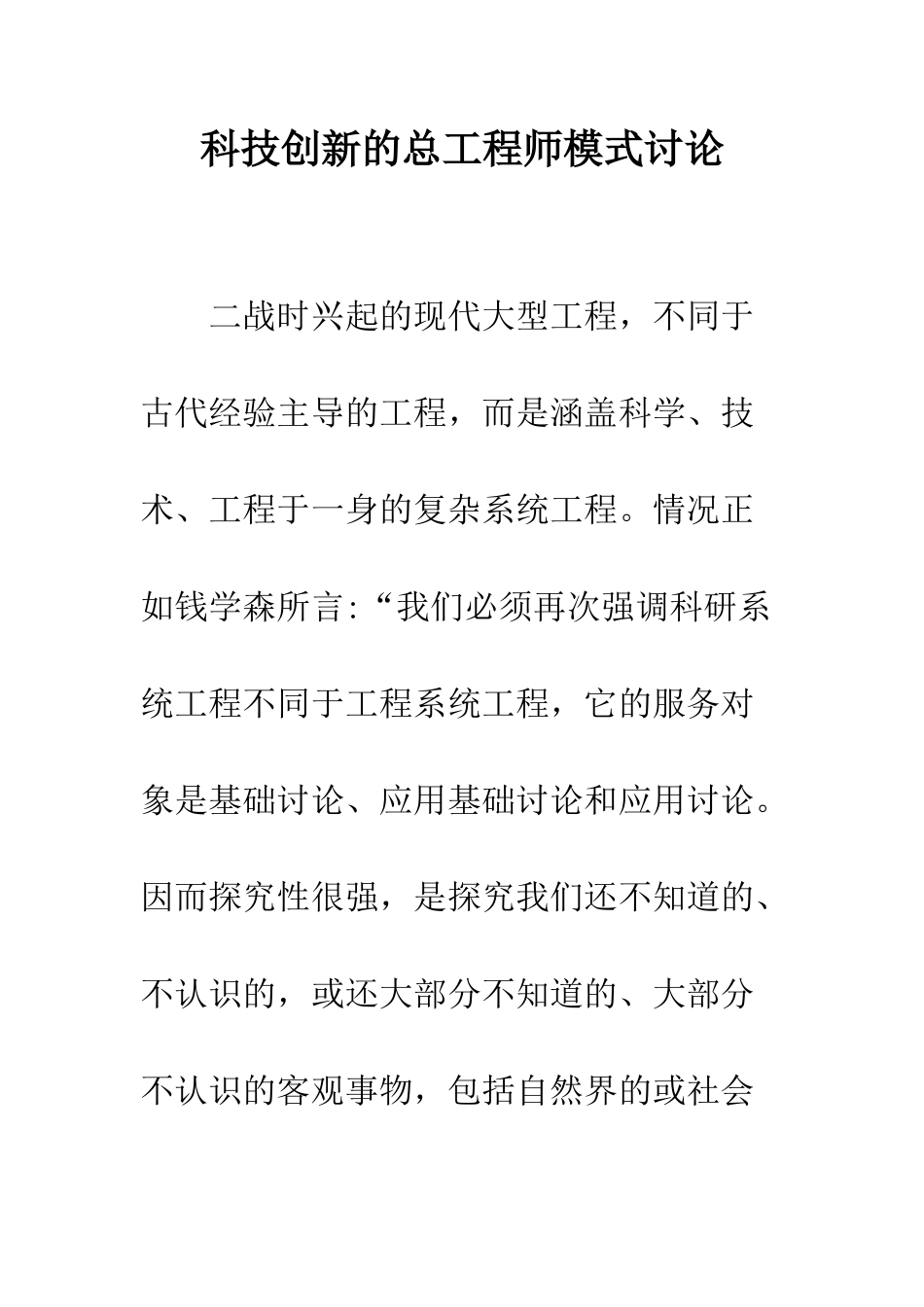科技创新的总工程师模式讨论 二战时兴起的现代大型工程,不同于古代经验主导的工程,而是涵盖科学、技术、工程于一身的复杂系统工程。情况正如钱学森所言:“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科研系统工程不同于工程系统工程,它的服务对象是基础讨论、应用基础讨论和应用讨论。因而探究性很强,是探究我们还不知道的、不认识的,或还大部分不知道的、大部分不认识的客观事物,包括自然界的或社会的。这样就在工作规划、计划中对工作对象不完全掌握,有一部分要在讨论实践中逐步掌握;而一旦全部掌握了,讨论工作就完成了。所以科研系统工程免不了要猜,可能猜对,也可能猜错”[1]。现代科技工程呈现出的高科技含量和空前的复杂性,使得纯粹的政府和军方官员难以胜任工程管理者的角色,而具有管理才能的科学精英,则显示出从事国防科技工程管理的天然优势。在二战期间的战时科研中,范尼瓦尔•布什、奥本海默、费米、查德威克、康普顿、布里奇曼、劳伦斯等人,即是科学家投身国防工程管理的典范。他们既是学界德高望重的领袖,又具备复合型的能力素养,既有一流的业务水平,又要有灵活务实的管理理念,既能整体把握科技工程的进程,又能高效洞察军事技术突破的瓶颈,兼具卓越的科研能力、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因而能够以“总工程师模式”成功实现科学技术创新。 国内方面,新中国应对霸权国家“核讹诈”的国家安全需求与“全国一盘棋”的国防科研方略,促使中国科学精英走上工程管理岗位。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为应对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给国家安全与和平进展带来的挑战,抵制霸权国家的核威慑和国际军备竞赛,中央做出进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尖端军事技术的战略决策。1956 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我国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进展规划》,开启了新中国大型国防科技工程的序幕。建国以后陆续开启的大型国防科技工程,就其高密度的科技含量和极端的复杂性而言,既是中国科技史和工程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科学技术管理史上的一次重大挑战。在工程筹备之初,一方面,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工业制造基础仍然非常薄弱,另一方面,在科研工程领域,行政管理权威的力量并不强大,如何汇聚各领域的高水平科学家共同进行国防工程大协作,这是传统行政管理人才无法实现的。因此,钱学森、钱三强、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孙家栋、王永志等科学权威凭借个人的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和在专业领域的强大号召力,为大型军事工程的科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