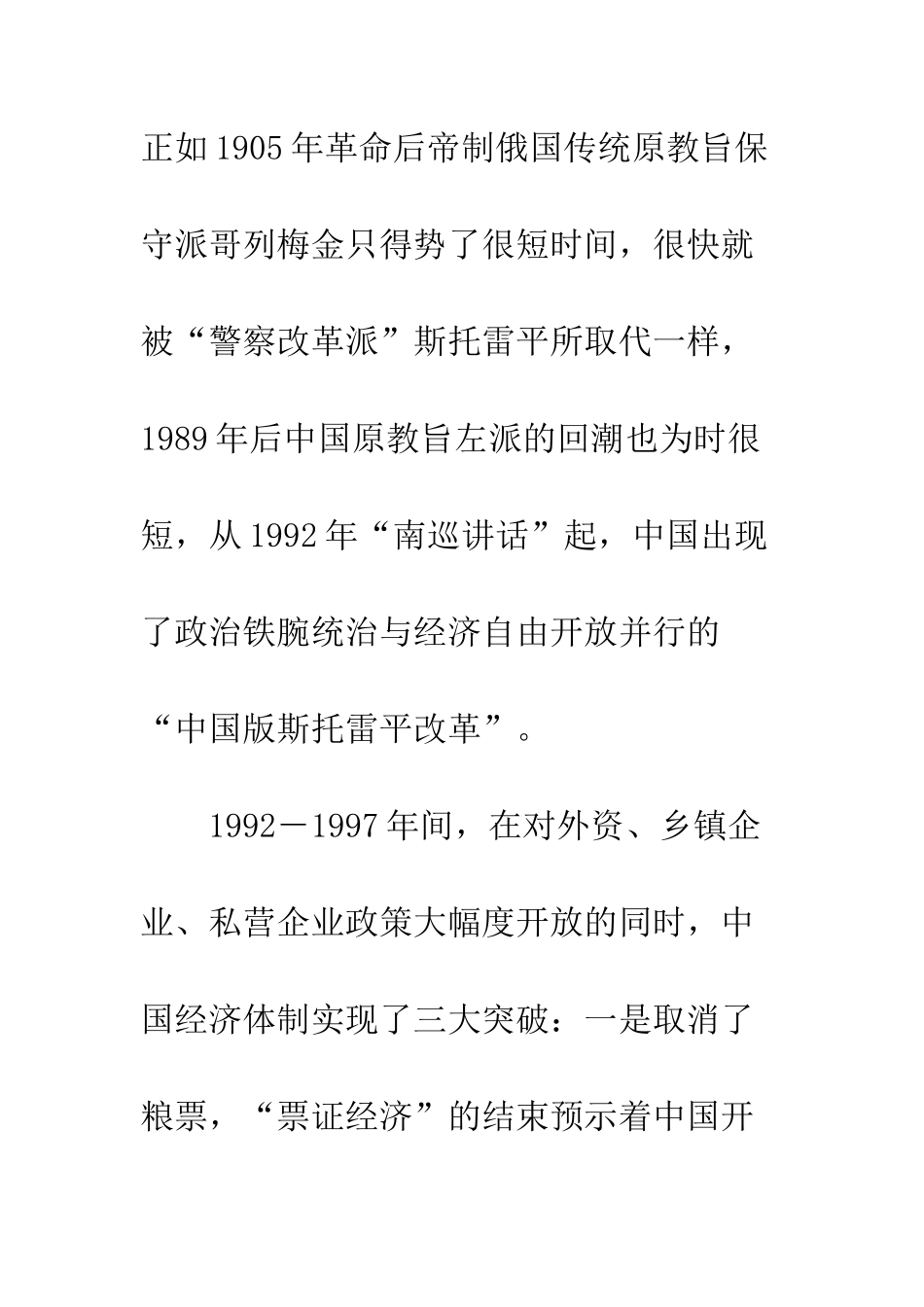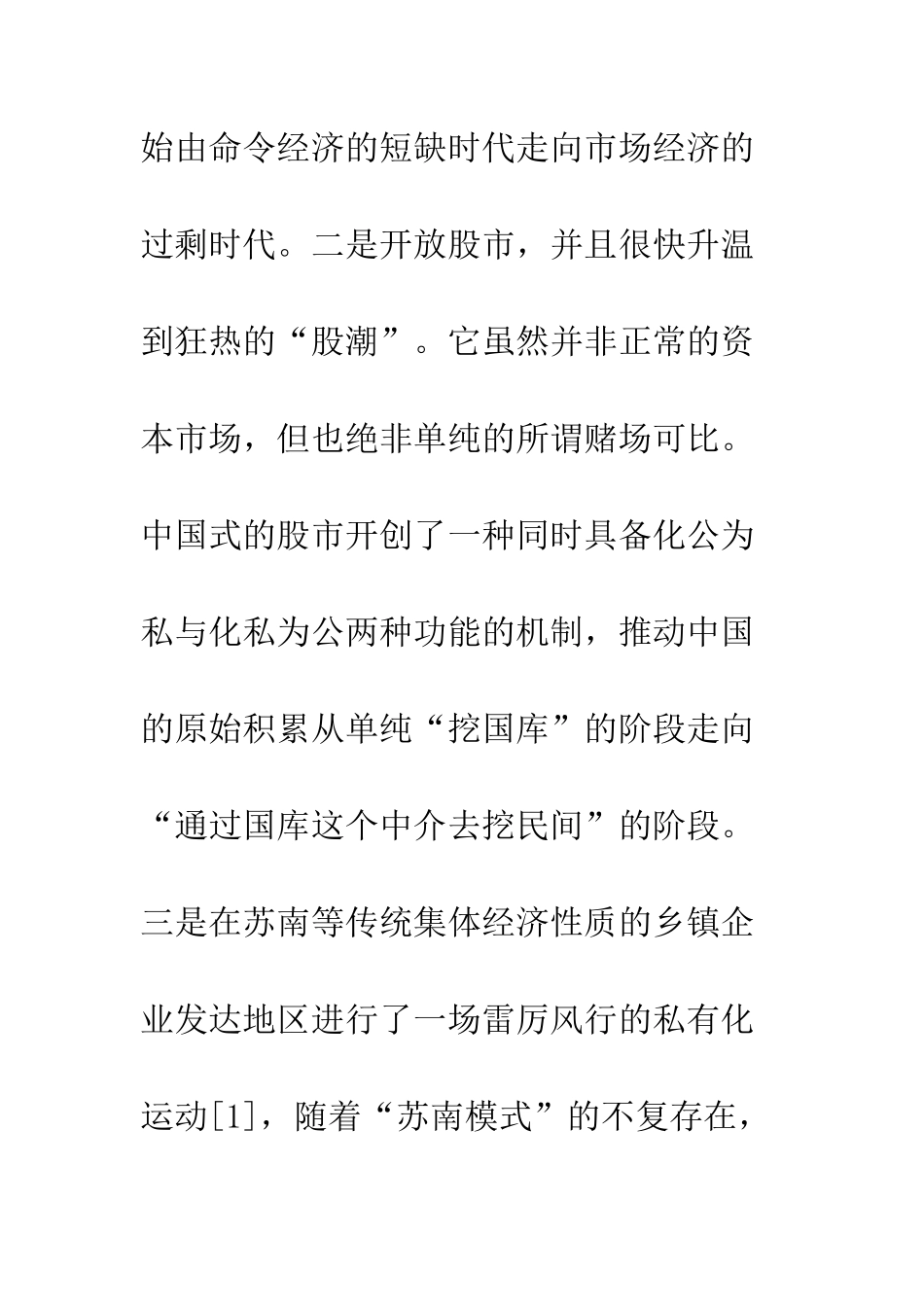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 “中国版斯托雷平改革” 1989 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确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989 年的事件,不仅对民间社会,而且对执政党都是一次“意识形态祛魅”进程,甚至可以说它对执政党的自我祛魅作用大于对除异见人士以外的一般民众。随着“革命党意识”由于自身受到革命的威胁而被解构,执政党的利益自觉空前凸显。正如 1905 年革命后帝制俄国传统原教旨保守派哥列梅金只得势了很短时间,很快就被“警察改革派”斯托雷平所取代一样,1989 年后中国原教旨左派的回潮也为时很短,从 1992 年“南巡讲话”起,中国出现了政治铁腕统治与经济自由开放并行的“中国版斯托雷平改革”。 1992-1997 年间,在对外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政策大幅度开放的同时,中国经济体制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取消了粮票,“票证经济”的结束预示着中国开始由命令经济的短缺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二是开放股市,并且很快升温到狂热的“股潮”。它虽然并非正常的资本市场,但也绝非单纯的所谓赌场可比。中国式的股市开创了一种同时具备化公为私与化私为公两种功能的机制,推动中国的原始积累从单纯“挖国库”的阶段走向“通过国库这个中介去挖民间”的阶段。三是在苏南等传统集体经济性质的乡镇企业发达地区进行了一场雷厉风行的私有化运动[1],随着“苏南模式”的不复存在,1997 年出台的《乡镇企业法》首次明确了“乡镇企业”概念的非特定所有制含义,由“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渊源形成的乡企属于“集体经济”之说从此成为历史。受“乡企转制”成功的推动,一些地区出现了县域范围内地方国有企业“全卖光”乃至“送光”的实践。 1997 年的中共十五大开始了又一新阶段。这次大会吹响了“国企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十五大期间《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国企改革的通栏文章题曰《可以,可以,也可以》,就是这种氛围的概括。自此,中国各中心城市和各省相继表示了告辞“国有独资”的决心,这在世界私有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表态。 1997 年起,许多省市相继宣布“今后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当年湖南省首开其例,紧接着深圳、武汉、四川、重庆及其他各省纷纷表态。深圳市提出:今后深圳原则上不再增设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经济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来。今明两年先从小企业“撤退”,再用 5-8 年时间逐步从大中型抽身而出。1999 年,武汉市表示:不再新办国有独资企业后,国有资本今后进入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