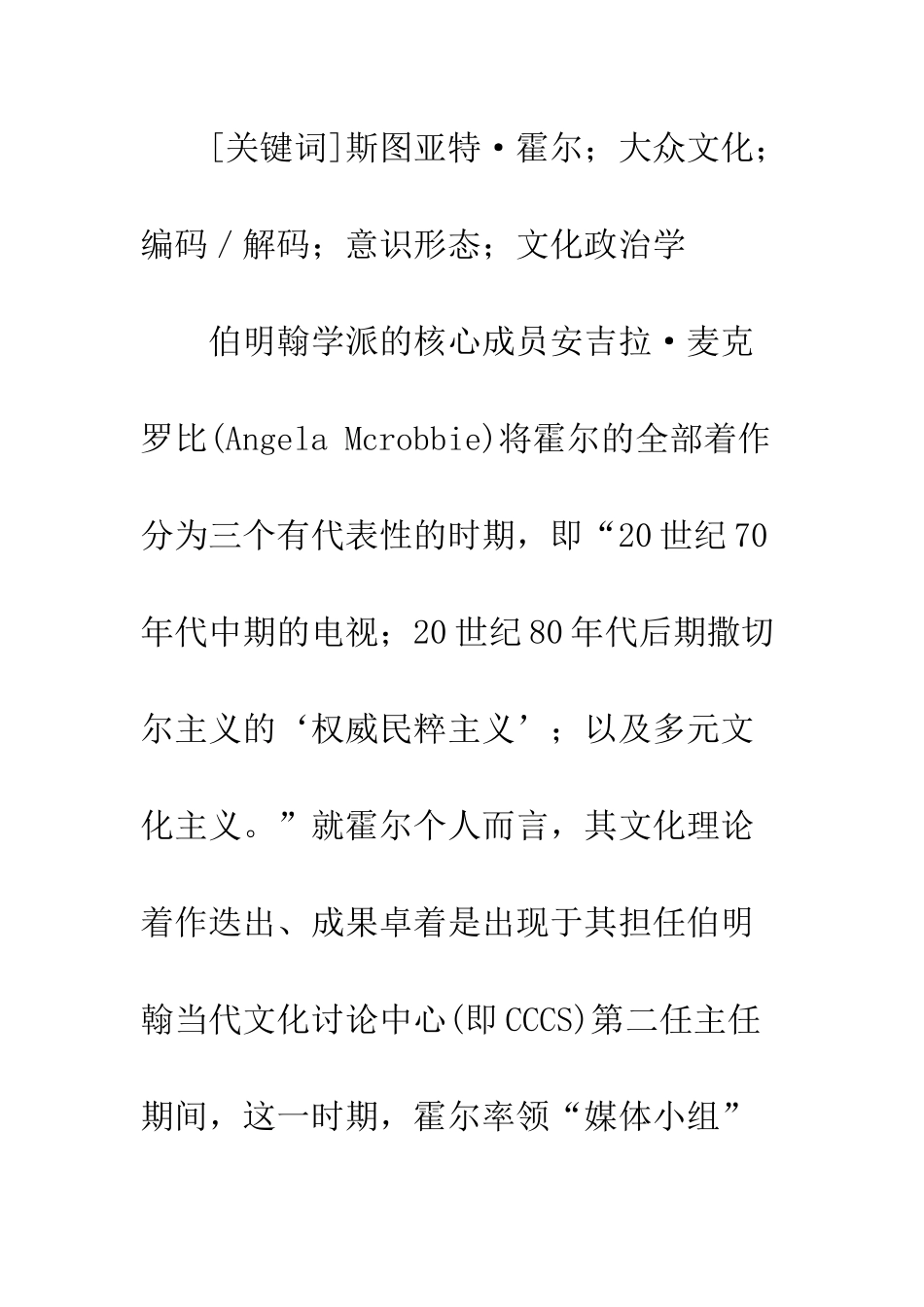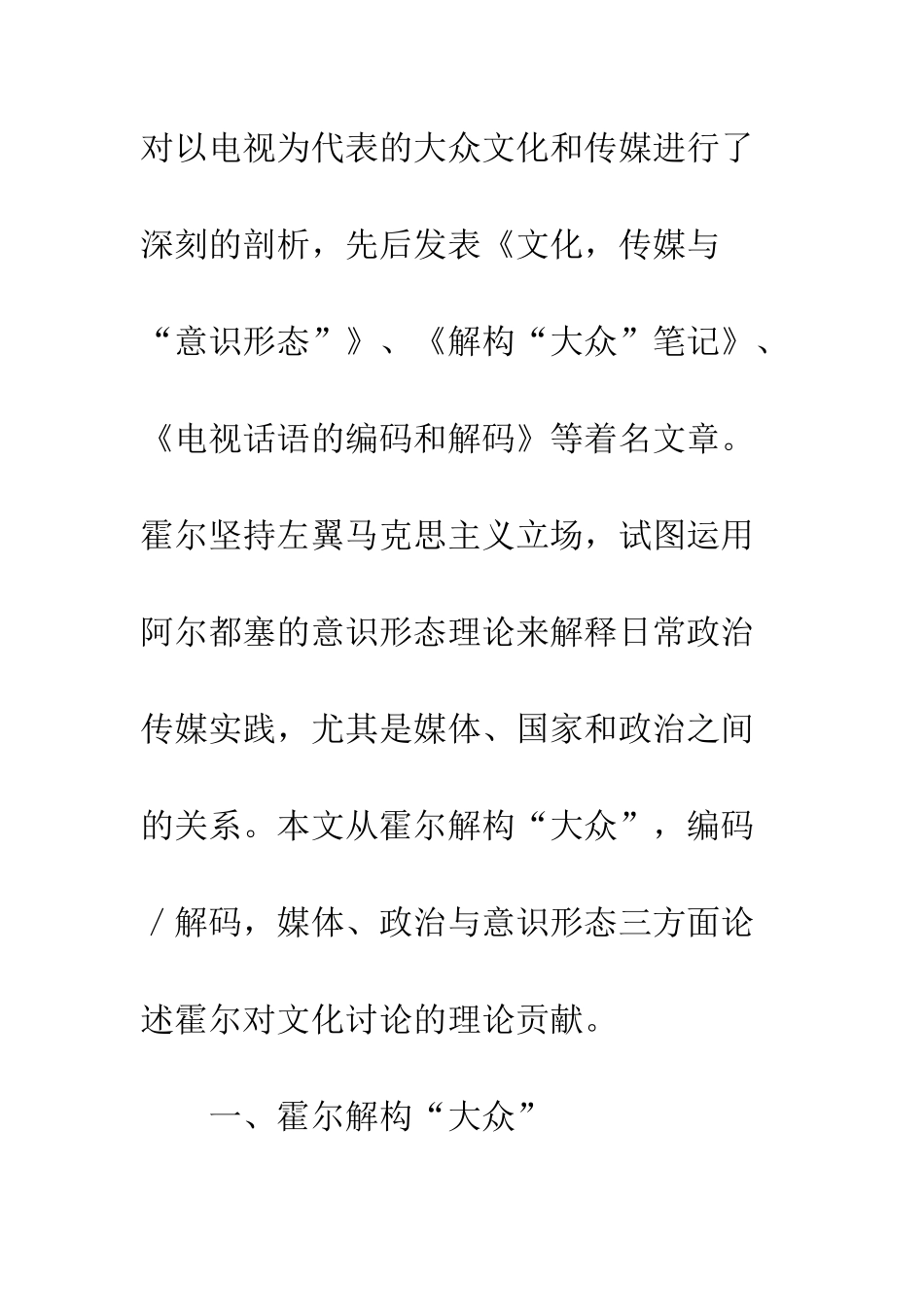斯图亚特·霍尔论大众文化与传媒 [摘要]作为文化讨论的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的声名很大程度上缘于其对大众文化与传媒的论述。霍尔坚持左翼马克思主义立场,试图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思想来解释日常政治传媒实践。霍尔对大众文化的定义、编码/解码模式的创立,尤其是对媒体、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从不同层面拓展了文化讨论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大众文化;编码/解码;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学 伯明翰学派的核心成员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将霍尔的全部着作分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时期,即“20 世纪 70年代中期的电视;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撒切尔主义的‘权威民粹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就霍尔个人而言,其文化理论着作迭出、成果卓着是出现于其担任伯明翰当代文化讨论中心(即 CCCS)第二任主任期间,这一时期,霍尔率领“媒体小组”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传媒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先后发表《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解构“大众”笔记》、《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等着名文章。霍尔坚持左翼马克思主义立场,试图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日常政治传媒实践,尤其是媒体、国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本文从霍尔解构“大众”,编码/解码,媒体、政治与意识形态三方面论述霍尔对文化讨论的理论贡献。 一、霍尔解构“大众” 霍尔在《解构“大众”笔记》一文中以社会关系作为大众文化的起点,“在向农业资本主义转变的漫长阶段,以及其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和进展的过程中,劳动者,劳动阶级,和穷人的文化中或长或短地持续着斗争。”在霍尔看来,“大众”往往成为社会“改革”的对象,要求其符合统治阶级的最大利益。霍尔言及的大众文化与威廉斯极端浪漫的描述“为民所有,所享,所用”大相径庭,霍尔注重从社会关系来定义“大众文化”。 霍尔围绕“大众”一词,对“大众文化”的不同定义进行了三个层次的解构:其一,是“大众文化”的市场或商业定义,即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霍尔认为,这一定义与对民众的操纵和贬低联系在一起,民众无异于“群氓”,是一群生活在“虚假意识”中的文化傻瓜。对这一同质化和描述性的定义,霍尔持反对态度,“归根结底,把民众视为完全被动的外围力量,是一种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其二,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这接近于大众的“人类学”概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