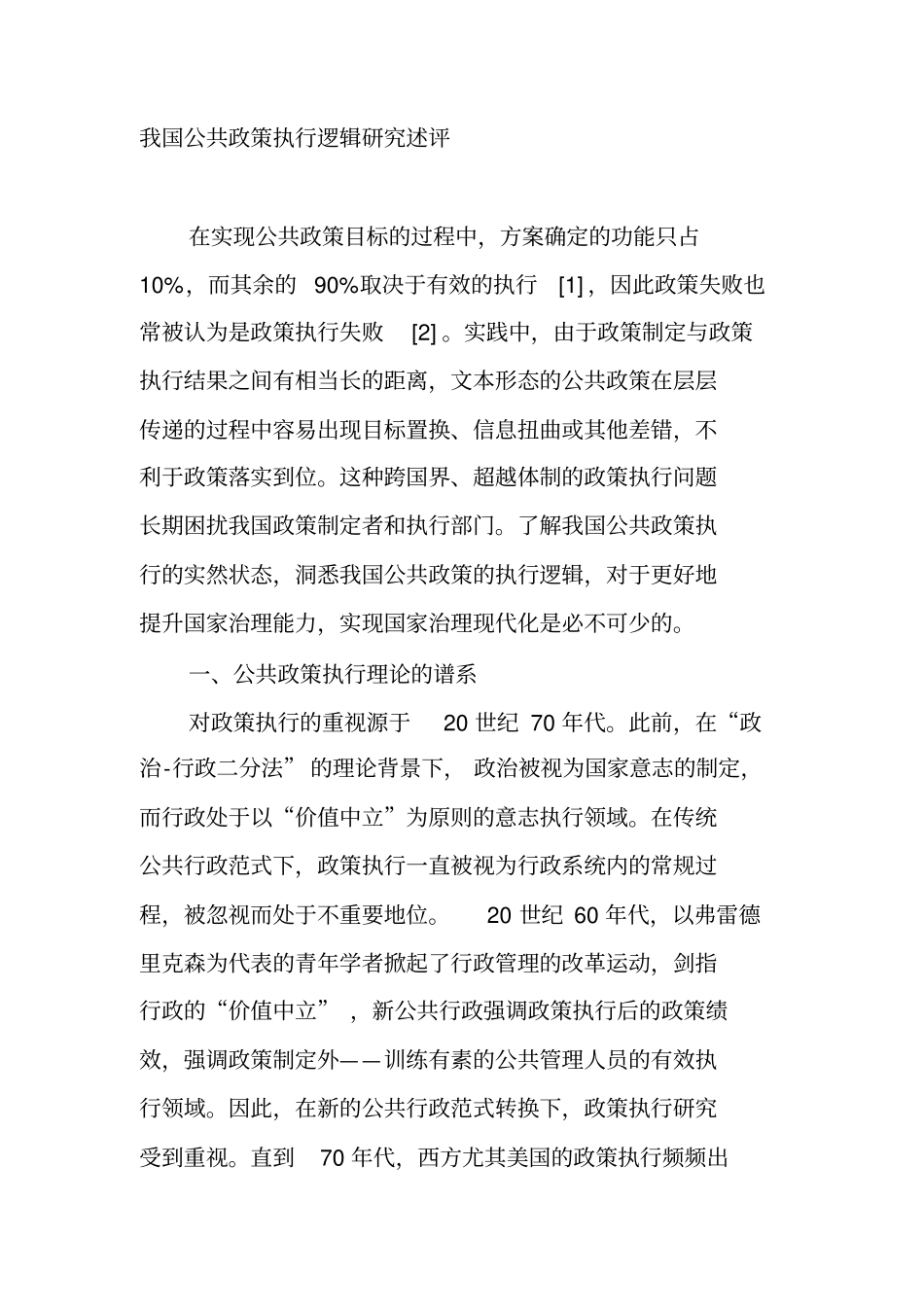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逻辑研究述评在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1],因此政策失败也常被认为是政策执行失败[2]。实践中,由于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结果之间有相当长的距离,文本形态的公共政策在层层传递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目标置换、信息扭曲或其他差错,不利于政策落实到位。这种跨国界、超越体制的政策执行问题长期困扰我国政策制定者和执行部门。了解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实然状态,洞悉我国公共政策的执行逻辑,对于更好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一、公共政策执行理论的谱系对政策执行的重视源于20世纪70年代。此前,在“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理论背景下,政治被视为国家意志的制定,而行政处于以“价值中立”为原则的意志执行领域。在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政策执行一直被视为行政系统内的常规过程,被忽视而处于不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青年学者掀起了行政管理的改革运动,剑指行政的“价值中立”,新公共行政强调政策执行后的政策绩效,强调政策制定外——训练有素的公共管理人员的有效执行领域。因此,在新的公共行政范式转换下,政策执行研究受到重视。直到70年代,西方尤其美国的政策执行频频出现问题,导致了声势浩大的“执行研究运动”,尤以1973年学者普瑞斯曼和维尔达夫斯基《执行:华盛顿的伟大期望是如何在奥克兰破灭的》一书的出版为标志[3]。因此在理论范式转变和执行研究运动实践的双重需求下,政策执行研究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纵观四十多年的公共政策执行研究,按照其理论发展脉络,学者大致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综合模型”三种研究路径。如表1所示,这三种路径在研究的出发点、视角以及理论假设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话语特点。学者丁煌将三种路径包含的执行因素变量划分为“组织理论”、“网络分析”、“制度分析”、“阐释性”四类[4]。组织理论关注官僚机构内部及其与私营部门的关系,关注执行组织的特征,关注执行组织成员的意向等变量;网络分析关注政策网络中的行为主体地位、策略、资源多寡、资源交换等网络行动者行为的描述;制度分析出于行动者行为改变的“成本-收益”关系视角,分析制度、激励等其他行为约束性因素变量;阐释性视角提出政策执行的文化维度和执行者对政策的认知框架,强调对政策内容意思解构的阐释性和共享性。表1执行理论变迁学者涂锋从三种路径依托的方法论视角,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行动者导向”和“结构导向”对三代研究进行归纳[5]。他认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争”其实属于行动者视角的内部争论。自上而下模型将政策执行三要素归为“问题可控性”、“构建执行的法律框架能力”、“影响执行的非法律性变量”,自下而上模型则认为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下的一系列个人决策集合构成了政府决策。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政策制定者与街头官僚孰起决定作用。但这两种路径都忽视了结构分析和多元行动者,因此接下来的执行研究转向寻求结构解释,借助Elomore发展的“向后绘图”的概念[6],试图从影响目标的行为出发向后建构执行过程。包括Matland对执行情景的分类、萨巴蒂尔的倡导联盟框架对结构性变量的强调等,都是以综合性路径分析行为背后的机制性原因。学者龚虹波在对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梳理中,将自上而下模型对应为官僚制模型,自下而上模型为政治动员模型,综合模型为博弈模型[7]。总体来说,国内外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均是遵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综合模型”路径展开。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特色现象中国公共政策执行有独特的结构。首先,在“以党领政”的政治生态下,形成了以党为主导、高位推动的政策执行体制。其次,在央地二分的府际关系和组织网络下,公共政策的执行网络具有横向上的块块特征和纵向上的条条特征,导致政策目标具有多属性和纵向上的层级性特点。多属性指中央制定的目标偏向笼统和原则层面,而地方细化后的目标指向可操作、可实现的本土层面;层级性指政策执行需要多职能部门的协同配合,因此政策往往有多元目标构成的目标群[8]。在复杂的政策执行结构下,政策执行结果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