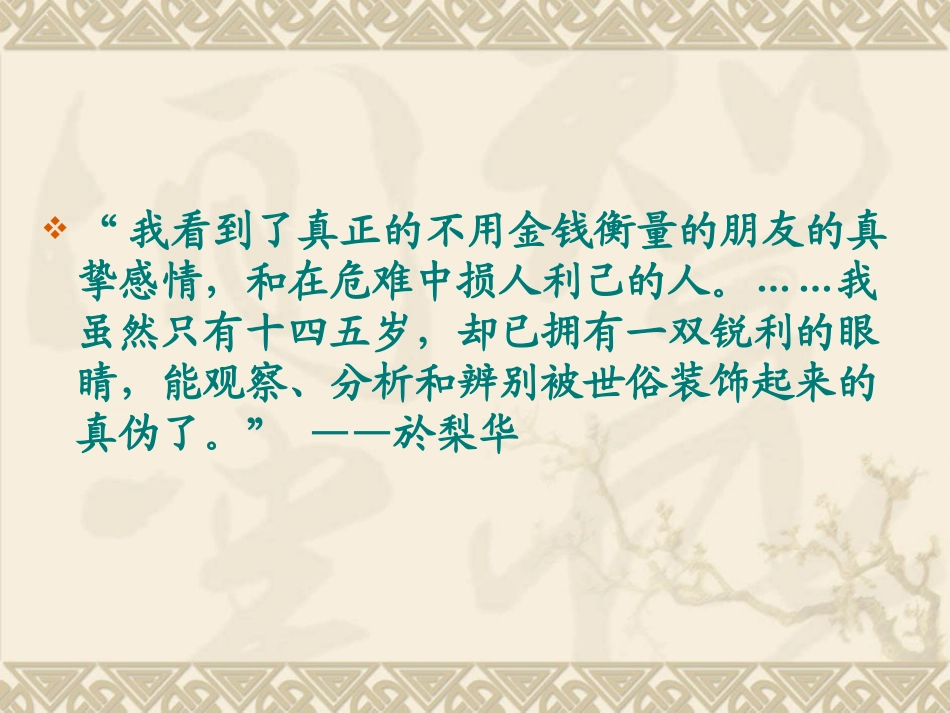第三节、於梨华及其创作一、作家其人於梨华,祖籍浙江镇海。1931年出生于上海,在家排行老二。1937-1944年间,随着家人辗转各地。从浙江到福建,再到江西、湖南、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又绕道陕西、河南回到宁波。回到家乡,於梨华先就读于镇海县立中学,后进入宁波女子师范。“我看到了真正的不用金钱衡量的朋友的真挚感情,和在危难中损人利己的人。……我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却已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观察、分析和辨别被世俗装饰起来的真伪了。”——於梨华1948年全家迁去台湾,於梨华进入台湾女子中学就读。1949年考入台大外文系,由于英文底子差,被迫转到历史系。1953年毕业后前去美国留学。寄住在一对犹太夫妻家里,充当了免费的佣人。在朋友的帮助下,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院攻读新闻。1956年,英文习作《扬子江头几多愁》获美国电影制片公司米高梅在加大设立的文艺奖第一名。同年获得新闻硕士学位,并与孙至悦(物理系博士)结婚。婚后充当家庭主妇,连生了三个孩子。不甘愿就此放弃写作,在家务劳动之余写作意图在美国发表,三年未有任何收获。之后转向中文写作,《梦回青河》初稿完成后,带着孩子回台湾,被朋友送给《皇冠》杂志,后连载并出版,一炮打红。“九年,从一个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到一个把梦捧在手中的留学生,到一个把梦踩在脚下的女人——家庭主妇。但是把梦踩碎了的生活未始不是一个好的、踏实的生活。做梦的生活固然美,却是迷迷糊糊,不知路的方向;踏实的生活平平稳稳,知道自己要什么,能什么,做什么,写什么。不,也许不知道自己写什么,但至少知道了自己要写,这一点是踏实的。”60年代以来,《也是秋天》、《归》、《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傅家的儿女们》等相继问世,奠定她在台湾文坛的地位,尤其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巨大成功,更使她无可厚非地成为“留学生文学鼻祖”。1967年这部小说获台湾嘉新年度最佳小说奖。1968年起在纽约州立大学文学院任教。1980年与丈夫离婚。1982年改嫁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校长欧立文。1993年在纽约州立大学执教25年的於梨华退休。“写作是我的丈夫,教书是我的情人……。现在我与我的情人道别,我将把我的全副精力交给他!”2003年发表长篇新作《在离去与道别之间》,被称为“北美版《围城》”和“北美版《儒林外史》”。二、作品分析1、《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7年牟天磊眉立(初恋情人)佳利(少妇)意珊(通信恋人)天美(妹妹)邱尚峰(老师)“没有具体的苦可讲……那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一种感觉……我是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我没有不快乐,也没有快乐。在美国十年,既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我不喜欢美国,可是我还要回去。并不是我在这里不能生活得很好,而是我和这里也脱了节,在这里我也没有根。”牟天磊的境况:到美国前,他朝气蓬勃倔强、任性,有时还有点野;而十年后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心灵的苍老、早衰主要来源于在美国独自“打天下”痛苦的留学生生活。两边都是客人,在美国无法扎根,在台湾也是客人。“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的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你还是外国人。”当他回到台湾,却看到在台湾的人也感到空虚和寂寞。不说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快闷得发炸了”的年轻人,浅薄的意珊,就连他尊敬的待人诚恳、诲人不倦、情愿在台北清苦生活,不愿去美国史丹福大学教中文的邱尚峰教授,也有“连武侠小说都救不了”的更深的寂寞。天磊“溶在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欢笑中,坐在亲人中间”,他却觉得自己是站在“漩涡之外的陌生客”,“他的一切想法,一切观念和他们脱了节。”他说:“我在这里也没有根”。所以,虽然他并“不喜欢美国,可是他还要回去”。“这一则不太温馨而充分象征时代苦闷的恋爱故事是於梨华小说艺术已臻新阶段的明证。”——夏志清有人说海明威他们是失落的一代,我们呢?我们这一代呢,应该是没有根的一代了吧?没有根是这代人深深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