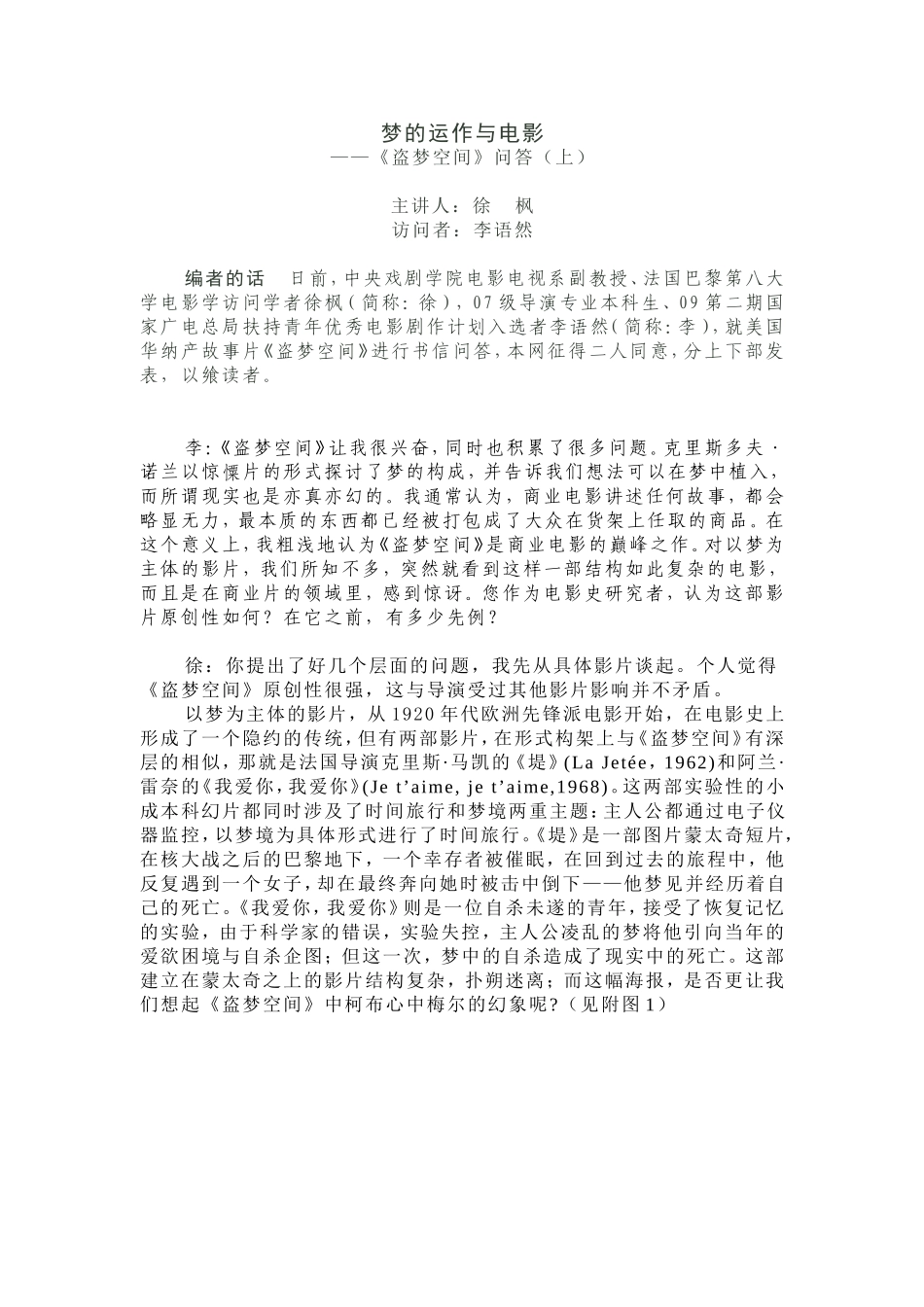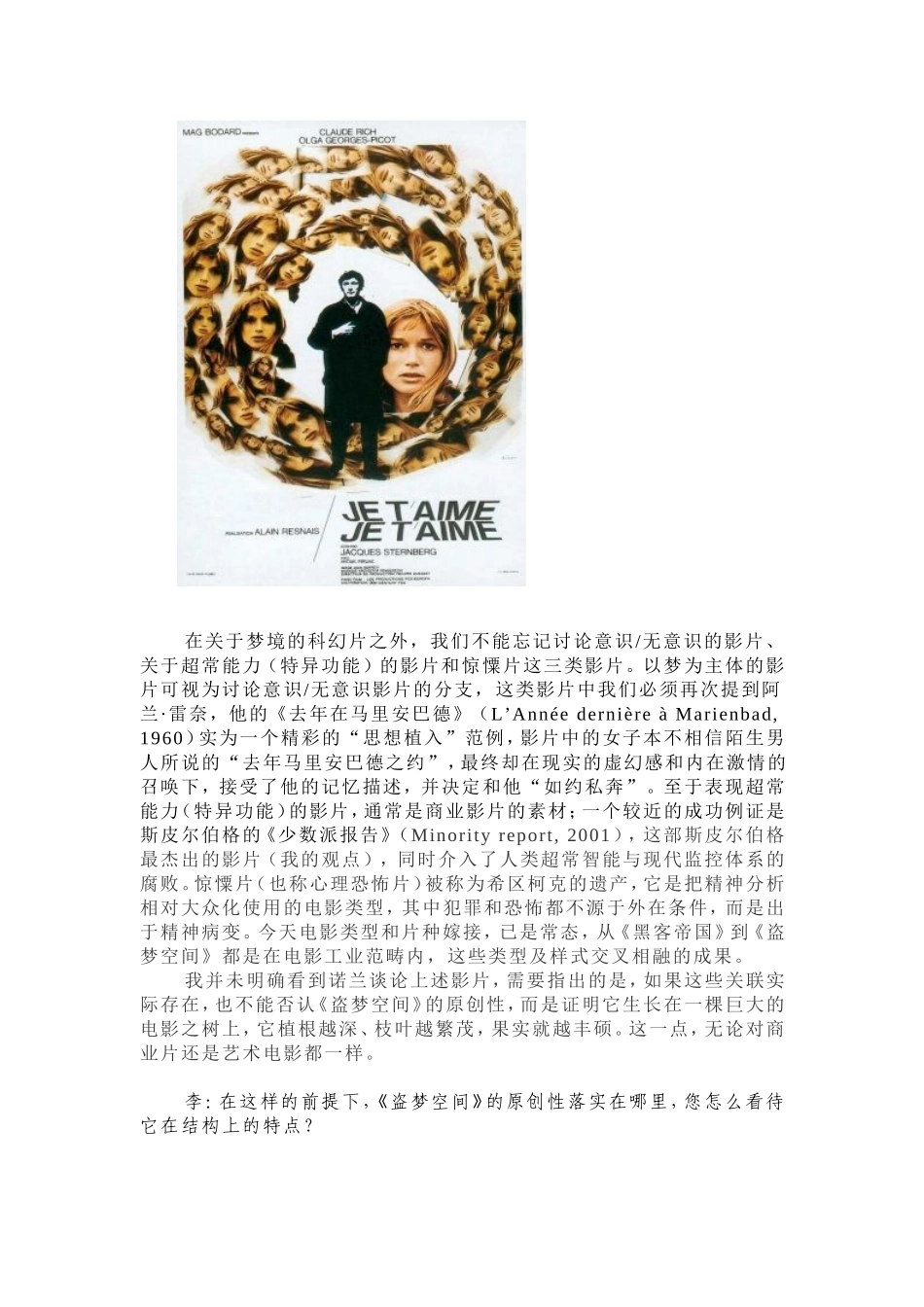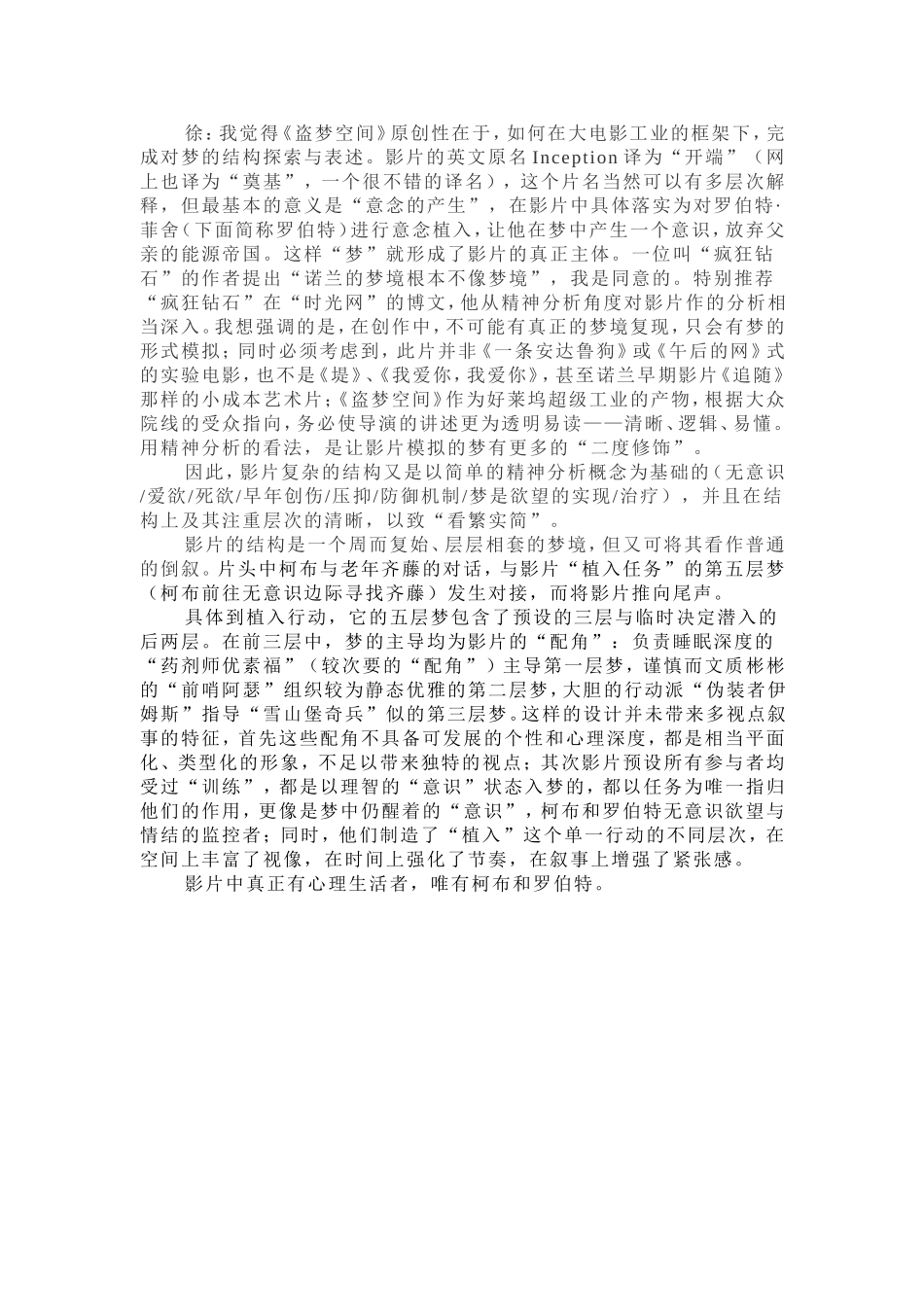梦的运作与电影——《盗梦空间》问答(上)主讲人:徐枫访问者:李语然编者的话日前,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电影学访问学者徐枫(简称:徐),07级导演专业本科生、09第二期国家广电总局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入选者李语然(简称:李),就美国华纳产故事片《盗梦空间》进行书信问答,本网征得二人同意,分上下部发表,以飨读者。李:《盗梦空间》让我很兴奋,同时也积累了很多问题。克里斯多夫·诺兰以惊憟片的形式探讨了梦的构成,并告诉我们想法可以在梦中植入,而所谓现实也是亦真亦幻的。我通常认为,商业电影讲述任何故事,都会略显无力,最本质的东西都已经被打包成了大众在货架上任取的商品。在这个意义上,我粗浅地认为《盗梦空间》是商业电影的巅峰之作。对以梦为主体的影片,我们所知不多,突然就看到这样一部结构如此复杂的电影,而且是在商业片的领域里,感到惊讶。您作为电影史研究者,认为这部影片原创性如何?在它之前,有多少先例?徐:你提出了好几个层面的问题,我先从具体影片谈起。个人觉得《盗梦空间》原创性很强,这与导演受过其他影片影响并不矛盾。以梦为主体的影片,从1920年代欧洲先锋派电影开始,在电影史上形成了一个隐约的传统,但有两部影片,在形式构架上与《盗梦空间》有深层的相似,那就是法国导演克里斯·马凯的《堤》(LaJetée,1962)和阿兰·雷奈的《我爱你,我爱你》(Jet’aime,jet’aime,1968)。这两部实验性的小成本科幻片都同时涉及了时间旅行和梦境两重主题:主人公都通过电子仪器监控,以梦境为具体形式进行了时间旅行。《堤》是一部图片蒙太奇短片,在核大战之后的巴黎地下,一个幸存者被催眠,在回到过去的旅程中,他反复遇到一个女子,却在最终奔向她时被击中倒下——他梦见并经历着自己的死亡。《我爱你,我爱你》则是一位自杀未遂的青年,接受了恢复记忆的实验,由于科学家的错误,实验失控,主人公凌乱的梦将他引向当年的爱欲困境与自杀企图;但这一次,梦中的自杀造成了现实中的死亡。这部建立在蒙太奇之上的影片结构复杂,扑朔迷离;而这幅海报,是否更让我们想起《盗梦空间》中柯布心中梅尔的幻象呢?(见附图1)在关于梦境的科幻片之外,我们不能忘记讨论意识/无意识的影片、关于超常能力(特异功能)的影片和惊憟片这三类影片。以梦为主体的影片可视为讨论意识/无意识影片的分支,这类影片中我们必须再次提到阿兰·雷奈,他的《去年在马里安巴德》(L’AnnéedernièreàMarienbad,1960)实为一个精彩的“思想植入”范例,影片中的女子本不相信陌生男人所说的“去年马里安巴德之约”,最终却在现实的虚幻感和内在激情的召唤下,接受了他的记忆描述,并决定和他“如约私奔”。至于表现超常能力(特异功能)的影片,通常是商业影片的素材;一个较近的成功例证是斯皮尔伯格的《少数派报告》(Minorityreport,2001),这部斯皮尔伯格最杰出的影片(我的观点),同时介入了人类超常智能与现代监控体系的腐败。惊憟片(也称心理恐怖片)被称为希区柯克的遗产,它是把精神分析相对大众化使用的电影类型,其中犯罪和恐怖都不源于外在条件,而是出于精神病变。今天电影类型和片种嫁接,已是常态,从《黑客帝国》到《盗梦空间》都是在电影工业范畴内,这些类型及样式交叉相融的成果。我并未明确看到诺兰谈论上述影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些关联实际存在,也不能否认《盗梦空间》的原创性,而是证明它生长在一棵巨大的电影之树上,它植根越深、枝叶越繁茂,果实就越丰硕。这一点,无论对商业片还是艺术电影都一样。李:在这样的前提下,《盗梦空间》的原创性落实在哪里,您怎么看待它在结构上的特点?徐:我觉得《盗梦空间》原创性在于,如何在大电影工业的框架下,完成对梦的结构探索与表述。影片的英文原名Inception译为“开端”(网上也译为“奠基”,一个很不错的译名),这个片名当然可以有多层次解释,但最基本的意义是“意念的产生”,在影片中具体落实为对罗伯特·菲舍(下面简称罗伯特)进行意念植入,让他在梦中产生一个意识,放弃父亲的能源帝国。这样“梦”就形成了影片的真正主体。一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