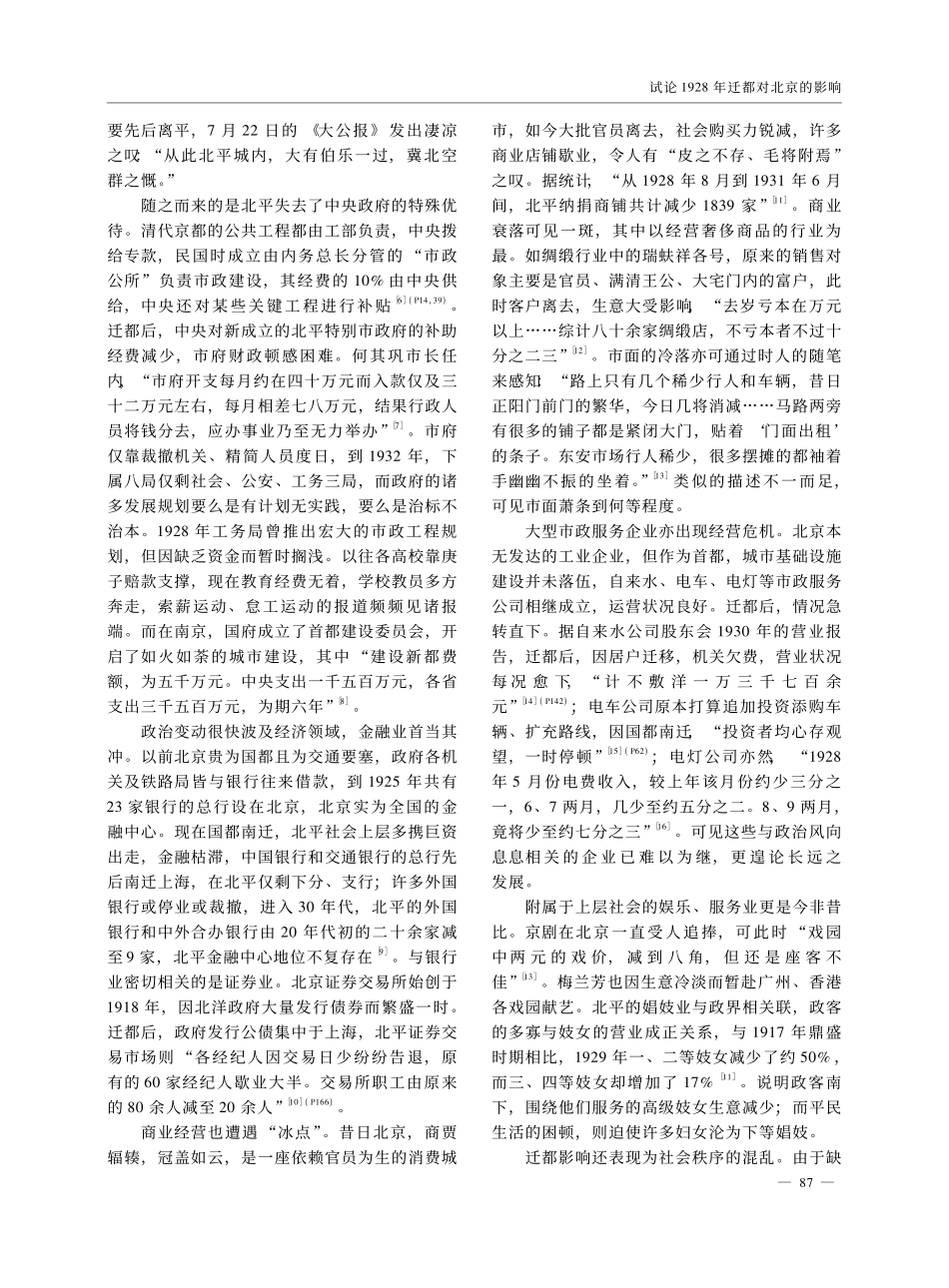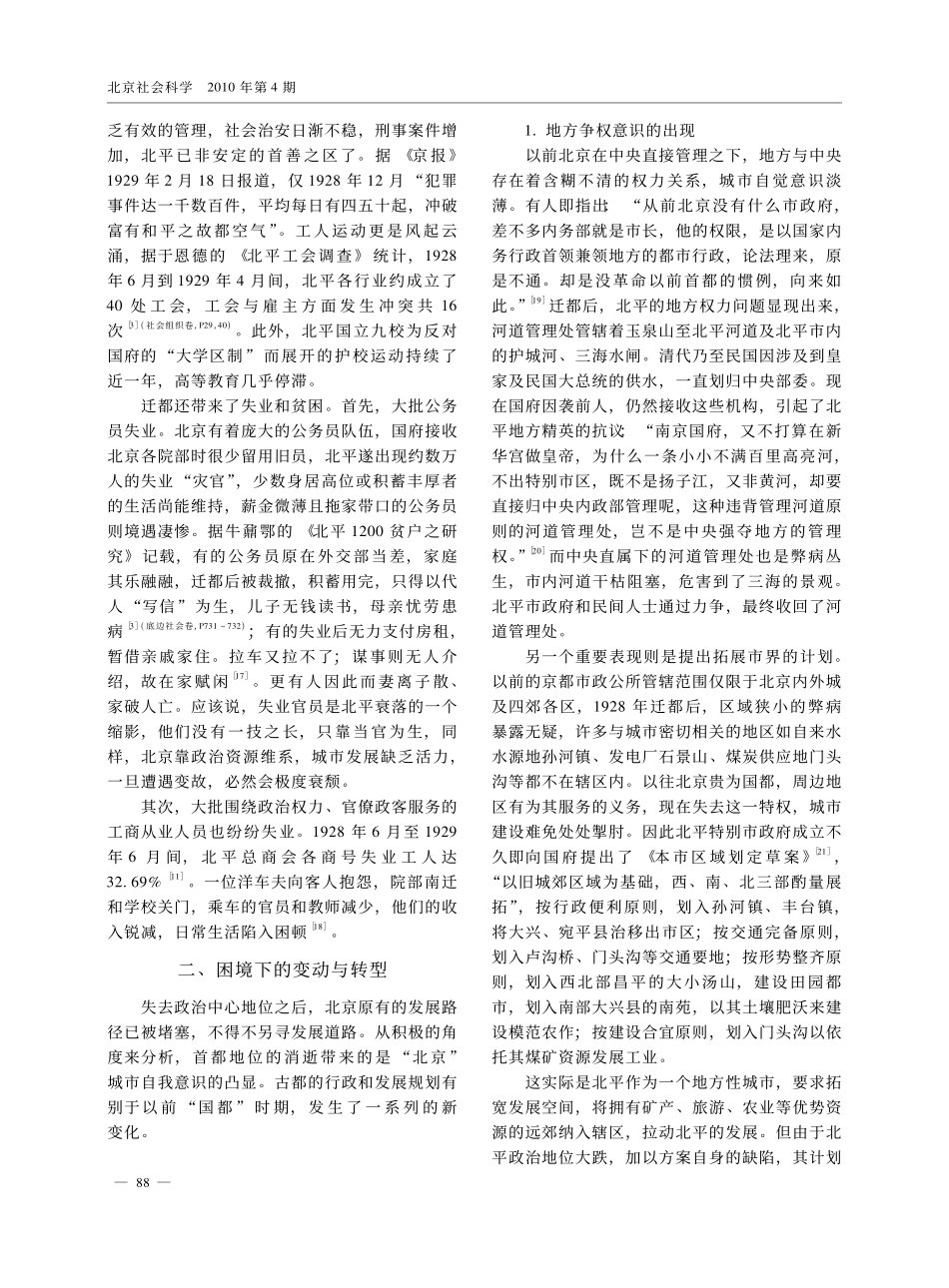试论1928年迁都对北京的影响陈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北京100872)[摘要]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1]。失去“国都”光环的北平在呈现百业凋零态势的同时,城市发展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自我意识和地方特色得以彰显。这一阶段是北京这一传统的政治中心古城向现代化城市转型的重要环节,对理解近代北京发展历程及今天的首都建设都不无裨益。[关键词]迁都;北平;影响;转型[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054(2010)04-0086-07[收稿日期]2009-11-20[作者简介]陈鹏(1985-),男,安徽安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硕士研究生.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特别市。迁都这一突发事件给古都北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学界对此问题尚缺乏全面、细致的探讨,关于这一时期的北京史研究对此问题多数只是一笔带过,专门的论述尚不多见[2]。本文拟以迁都后前两年(即北平各界反映最激烈的时候)为考察时段,对故都丧失政治资源后社会衰落状况及由此引发的城市发展转型进行勾勒,以期对迁都的影响做出初步的探究。一、迁都之初北平的急剧衰落北京属于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元、明、清三代一直贵为帝都,城市发展得益于历代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进入民国后,依然如此。中央重点、优先发展首都,将各种有利资源汇集于此,机关林立,官僚众多。又因政治与思想文化的紧密联系,北京承载了文化中心职能,高校汇聚,名牌教授云集,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堪称人文荟萃之所。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也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交通重镇和信息中心。北京作为一座消费都市,围绕官僚集团服务的金融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娱乐业盛极一时,吸引了大量外籍人口前来谋生,成为一座百万人口规模的大都市。然而,国都优势是一把双刃剑,北京在获利的同时,也积淀了不少社会问题:城市发展路径单一,仅依托政治因素支撑,工业匮乏,繁荣的商业依赖官员消费,缺乏经济造血功能。社会风气保守,很多旧俗得以存活,到1928年,发辫、缠足之风仍很盛行,一般市民的奢靡之风、游惰之情胜过他处。贫富差距悬殊,贫困人口多,据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的调查报告,到1926年,北京需要靠救济为生的“极贫户、次贫户家庭”占全市家庭的26.1%,处于“中户”以下水平的占73.5%[3](城市生活卷,P5);而社会上层则过着纸醉金迷、养尊处优的生活。这些问题都是北京近代化道路上的障碍。迁都使北京丧失了“国都”的至尊地位,已有的隐患暴露无遗。围绕政治权力、官僚群体运转的社会体系濒临崩溃,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城市发展举步维艰。首都资格的丢失意味着政治中心职能的消退,中央机关及大批高官南迁,昔日门庭若市的军政机关人去楼空。如原外交部、教育部就分别易为外交部、教育部档案保管处[4](P344,350),这似乎昭示北平将成为陈列文物之旧都。原来全国性质的回民公会等组织,不得不降格为北平分会[5],北平不再是号令全国的中心了。1928年7月蒋介石来北平视察后,同阎锡山、李济深等政—68—要先后离平,7月22日的《大公报》发出凄凉之叹:“从此北平城内,大有伯乐一过,冀北空群之慨。”随之而来的是北平失去了中央政府的特殊优待。清代京都的公共工程都由工部负责,中央拨给专款,民国时成立由内务总长分管的“市政公所”负责市政建设,其经费的10%由中央供给,中央还对某些关键工程进行补贴[6](P14,39)。迁都后,中央对新成立的北平特别市政府的补助经费减少,市府财政顿感困难。何其巩市长任内,“市府开支每月约在四十万元而入款仅及三十二万元左右,每月相差七八万元,结果行政人员将钱分去,应办事业乃至无力举办”[7]。市府仅靠裁撤机关、精简人员度日,到1932年,下属八局仅剩社会、公安、工务三局,而政府的诸多发展规划要么是有计划无实践,要么是治标不治本。1928年工务局曾推出宏大的市政工程规划,但因缺乏资金而暂时搁浅。以往各高校靠庚子赔款支撑,现在教育经费无着,学校教员多方奔走,索薪运动、怠工运动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而在南京,国府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开启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其中“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