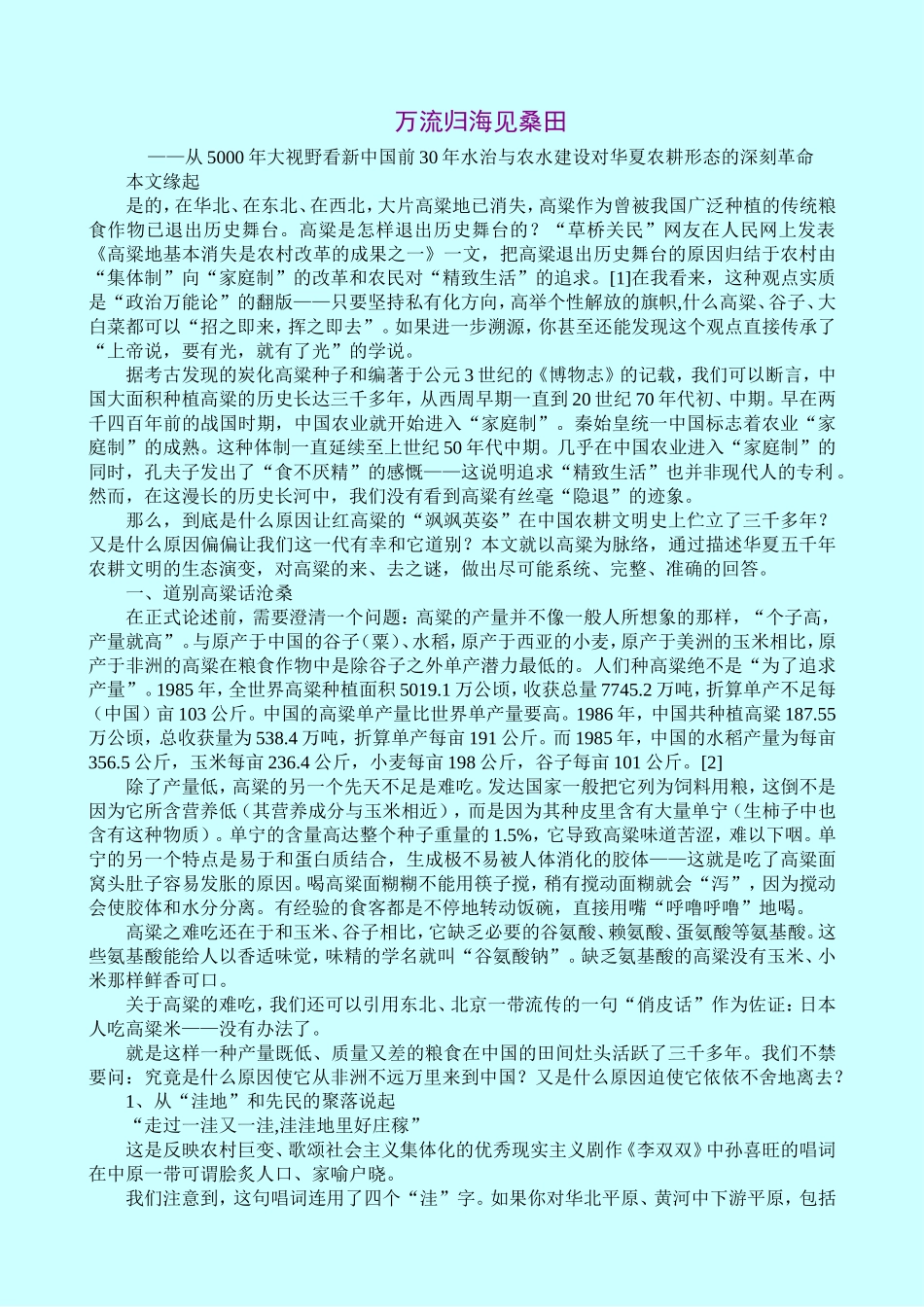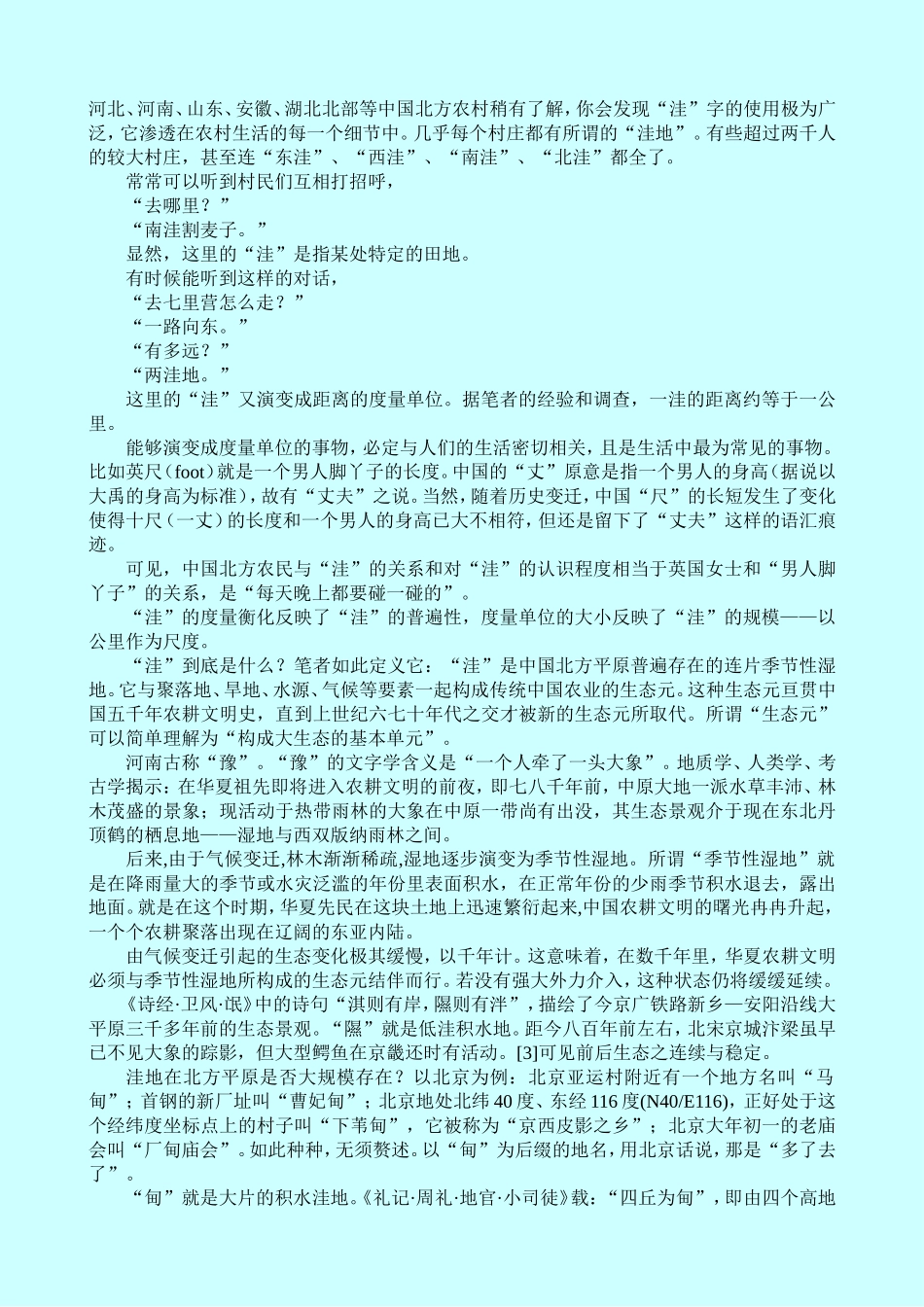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孟凡贵(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7年2月15日内容提要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高粱”,在上世纪70年代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客观描述了自50年代兴起的全国大规模治水、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论述由水利建设引发的农业生态革命及其深远意义,从而凸显了农业集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道别高粱话沧桑“洼地”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古农业生态要素,它的本质特征是水涝与盐碱。大面积种植高粱正是针对这种生态的必然选择。如果不改变这种生态的本质,就只能在洼地里种植高梁。第二部分斥卤生粱说轮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先民与水患、盐碱进行了不息的抗争。但由于一直未能组织起强大的社会力量解决“排涝”这个核心问题,以致对大面积低洼、盐碱地的开发陷入周期性的轮回状态。第三部分万流归海见桑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对大江大河进行彻底治理,大力兴建农业蓄排、灌水利工程,一举改变了险恶的农业生态,从而引导了中国农业极为深刻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大禹治水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同时堪称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典范。万流归海见桑田——从5000年大视野看新中国前30年水治与农水建设对华夏农耕形态的深刻革命本文缘起是的,在华北、在东北、在西北,大片高粱地已消失,高粱作为曾被我国广泛种植的传统粮食作物已退出历史舞台。高粱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草桥关民”网友在人民网上发表《高粱地基本消失是农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把高粱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归结于农村由“集体制”向“家庭制”的改革和农民对“精致生活”的追求。[1]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实质是“政治万能论”的翻版——只要坚持私有化方向,高举个性解放的旗帜,什么高粱、谷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进一步溯源,你甚至还能发现这个观点直接传承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学说。据考古发现的炭化高粱种子和编著于公元3世纪的《博物志》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大面积种植高粱的历史长达三千多年,从西周早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早在两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国农业就开始进入“家庭制”。秦始皇统一中国标志着农业“家庭制”的成熟。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几乎在中国农业进入“家庭制”的同时,孔夫子发出了“食不厌精”的感慨——这说明追求“精致生活”也并非现代人的专利。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没有看到高粱有丝毫“隐退”的迹象。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红高粱的“飒飒英姿”在中国农耕文明史上伫立了三千多年?又是什么原因偏偏让我们这一代有幸和它道别?本文就以高粱为脉络,通过描述华夏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生态演变,对高粱的来、去之谜,做出尽可能系统、完整、准确的回答。一、道别高粱话沧桑在正式论述前,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高粱的产量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个子高,产量就高”。与原产于中国的谷子(粟)、水稻,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相比,原产于非洲的高粱在粮食作物中是除谷子之外单产潜力最低的。人们种高粱绝不是“为了追求产量”。1985年,全世界高粱种植面积5019.1万公顷,收获总量7745.2万吨,折算单产不足每(中国)亩103公斤。中国的高粱单产量比世界单产量要高。1986年,中国共种植高粱187.55万公顷,总收获量为538.4万吨,折算单产每亩191公斤。而1985年,中国的水稻产量为每亩356.5公斤,玉米每亩236.4公斤,小麦每亩198公斤,谷子每亩101公斤。[2]除了产量低,高粱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难吃。发达国家一般把它列为饲料用粮,这倒不是因为它所含营养低(其营养成分与玉米相近),而是因为其种皮里含有大量单宁(生柿子中也含有这种物质)。单宁的含量高达整个种子重量的1.5%,它导致高粱味道苦涩,难以下咽。单宁的另一个特点是易于和蛋白质结合,生成极不易被人体消化的胶体——这就是吃了高粱面窝头肚子容易发胀的原因。喝高粱面糊糊不能用筷子搅,稍有搅动面糊就会“泻”,因为搅动会使胶体和水分分离。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