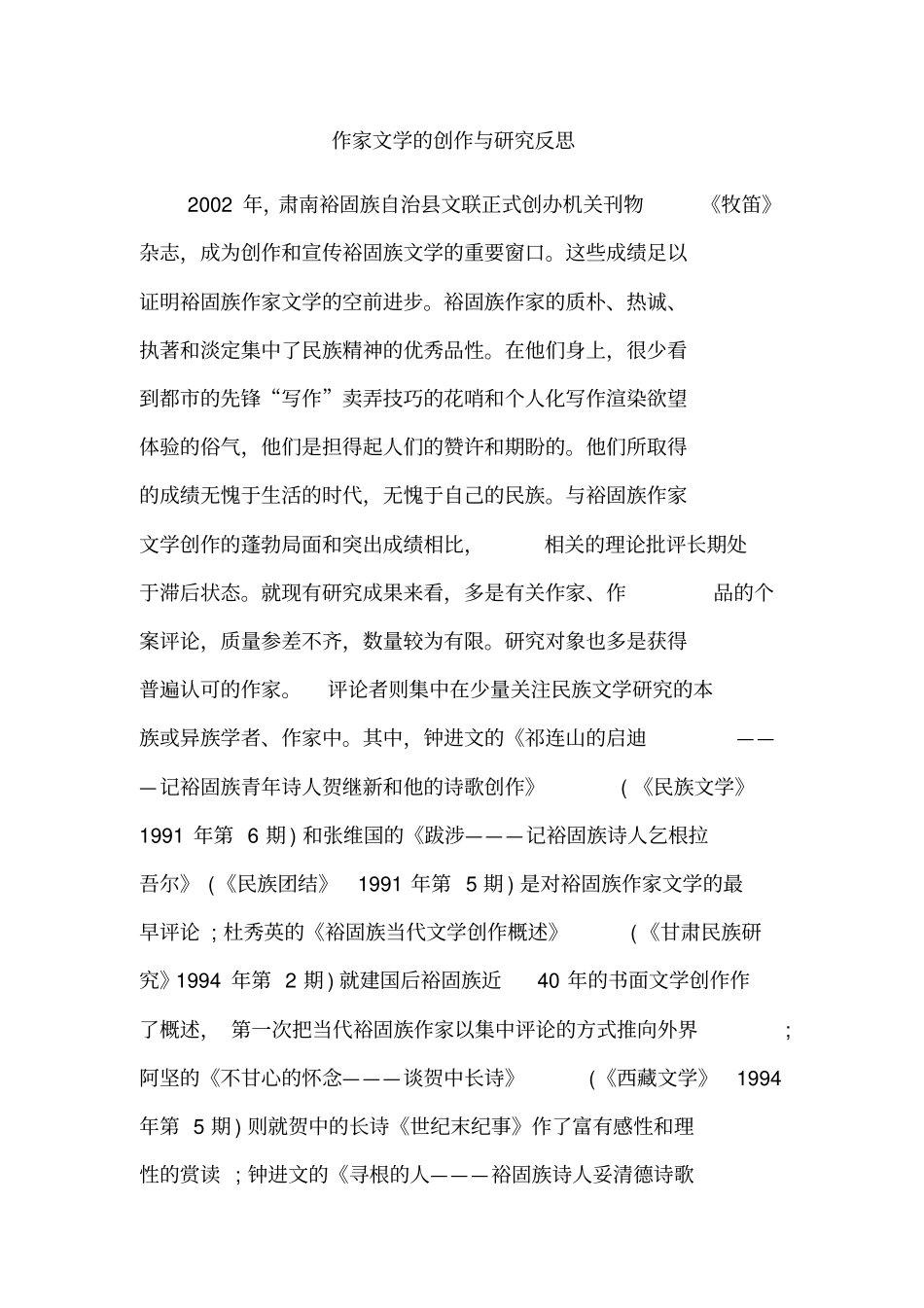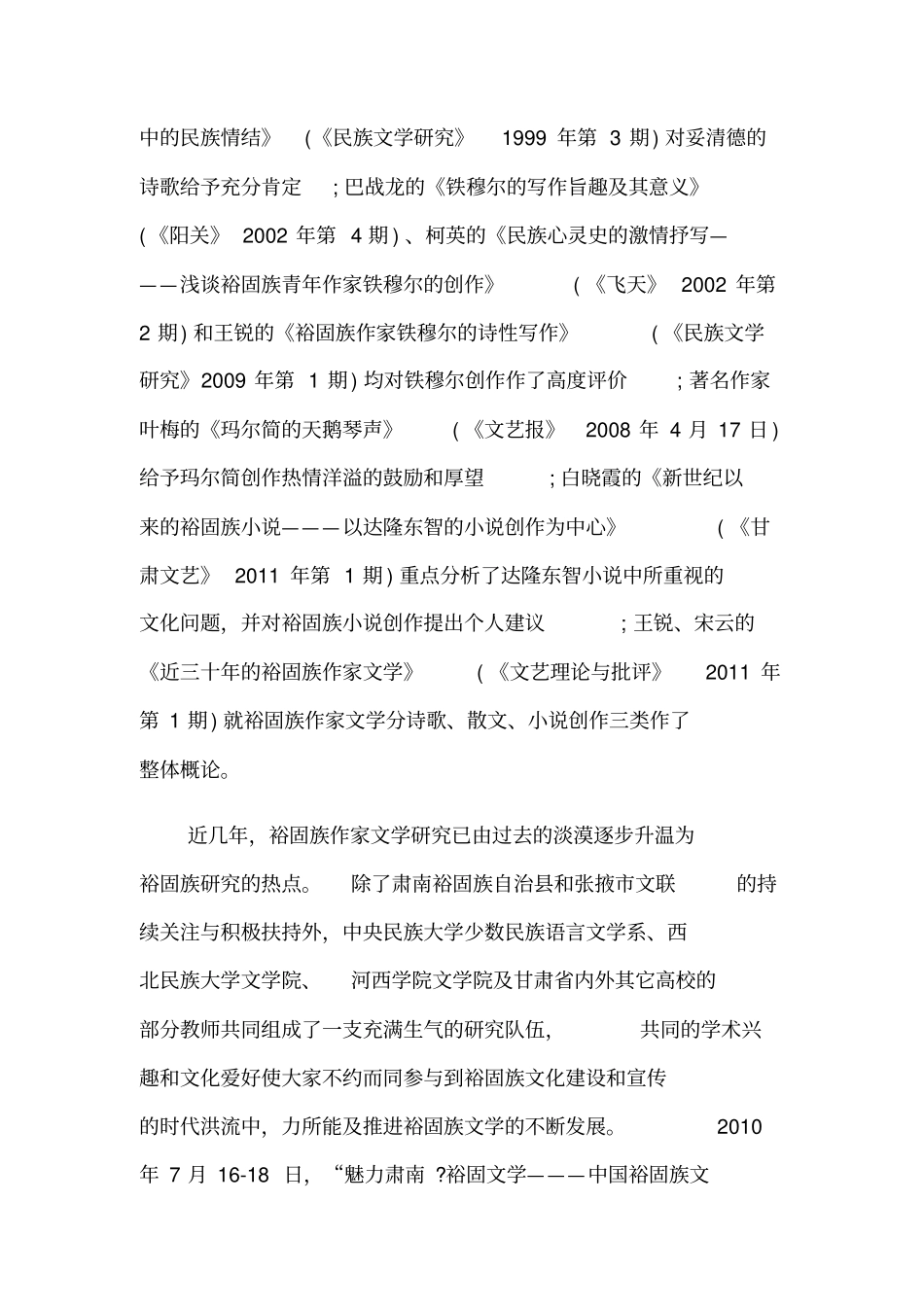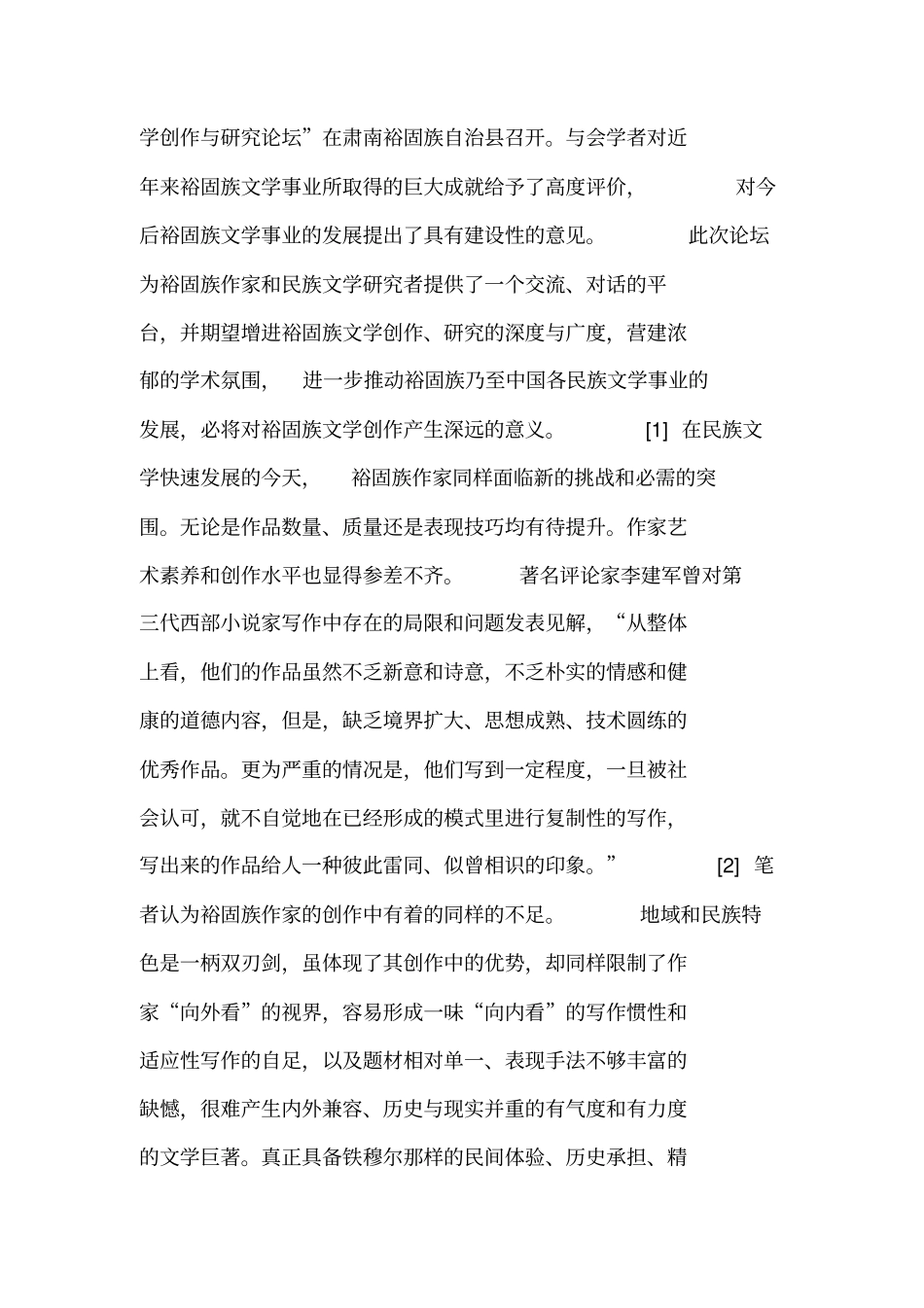作家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反思2002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联正式创办机关刊物《牧笛》杂志,成为创作和宣传裕固族文学的重要窗口。这些成绩足以证明裕固族作家文学的空前进步。裕固族作家的质朴、热诚、执著和淡定集中了民族精神的优秀品性。在他们身上,很少看到都市的先锋“写作”卖弄技巧的花哨和个人化写作渲染欲望体验的俗气,他们是担得起人们的赞许和期盼的。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无愧于生活的时代,无愧于自己的民族。与裕固族作家文学创作的蓬勃局面和突出成绩相比,相关的理论批评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多是有关作家、作品的个案评论,质量参差不齐,数量较为有限。研究对象也多是获得普遍认可的作家。评论者则集中在少量关注民族文学研究的本族或异族学者、作家中。其中,钟进文的《祁连山的启迪———记裕固族青年诗人贺继新和他的诗歌创作》(《民族文学》1991年第6期)和张维国的《跋涉———记裕固族诗人乞根拉吾尔》(《民族团结》1991年第5期)是对裕固族作家文学的最早评论;杜秀英的《裕固族当代文学创作概述》(《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就建国后裕固族近40年的书面文学创作作了概述,第一次把当代裕固族作家以集中评论的方式推向外界;阿坚的《不甘心的怀念———谈贺中长诗》(《西藏文学》1994年第5期)则就贺中的长诗《世纪末纪事》作了富有感性和理性的赏读;钟进文的《寻根的人———裕固族诗人妥清德诗歌中的民族情结》(《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对妥清德的诗歌给予充分肯定;巴战龙的《铁穆尔的写作旨趣及其意义》(《阳关》2002年第4期)、柯英的《民族心灵史的激情抒写———浅谈裕固族青年作家铁穆尔的创作》(《飞天》2002年第2期)和王锐的《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诗性写作》(《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均对铁穆尔创作作了高度评价;著名作家叶梅的《玛尔简的天鹅琴声》(《文艺报》2008年4月17日)给予玛尔简创作热情洋溢的鼓励和厚望;白晓霞的《新世纪以来的裕固族小说———以达隆东智的小说创作为中心》(《甘肃文艺》2011年第1期)重点分析了达隆东智小说中所重视的文化问题,并对裕固族小说创作提出个人建议;王锐、宋云的《近三十年的裕固族作家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就裕固族作家文学分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三类作了整体概论。近几年,裕固族作家文学研究已由过去的淡漠逐步升温为裕固族研究的热点。除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张掖市文联的持续关注与积极扶持外,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河西学院文学院及甘肃省内外其它高校的部分教师共同组成了一支充满生气的研究队伍,共同的学术兴趣和文化爱好使大家不约而同参与到裕固族文化建设和宣传的时代洪流中,力所能及推进裕固族文学的不断发展。2010年7月16-18日,“魅力肃南?裕固文学———中国裕固族文学创作与研究论坛”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召开。与会学者对近年来裕固族文学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今后裕固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此次论坛为裕固族作家和民族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并期望增进裕固族文学创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营建浓郁的学术氛围,进一步推动裕固族乃至中国各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必将对裕固族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意义。[1]在民族文学快速发展的今天,裕固族作家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和必需的突围。无论是作品数量、质量还是表现技巧均有待提升。作家艺术素养和创作水平也显得参差不齐。著名评论家李建军曾对第三代西部小说家写作中存在的局限和问题发表见解,“从整体上看,他们的作品虽然不乏新意和诗意,不乏朴实的情感和健康的道德内容,但是,缺乏境界扩大、思想成熟、技术圆练的优秀作品。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他们写到一定程度,一旦被社会认可,就不自觉地在已经形成的模式里进行复制性的写作,写出来的作品给人一种彼此雷同、似曾相识的印象。”[2]笔者认为裕固族作家的创作中有着的同样的不足。地域和民族特色是一柄双刃剑,虽体现了其创作中的优势,却同样限制了作家“向外看”的视界,容易形成一味“向内看”的写作惯性和适应性写作的自足,以及题材相对单一、表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