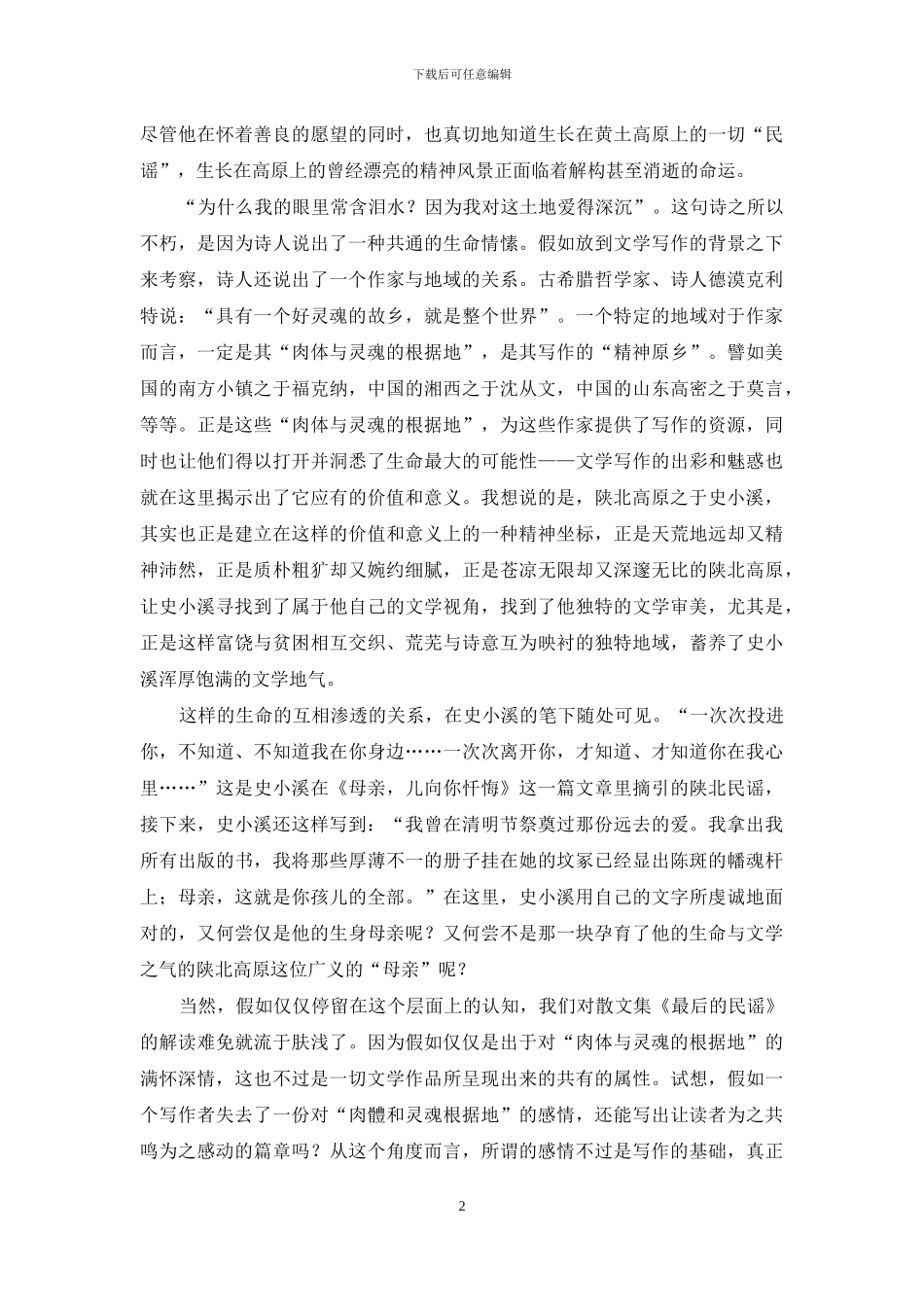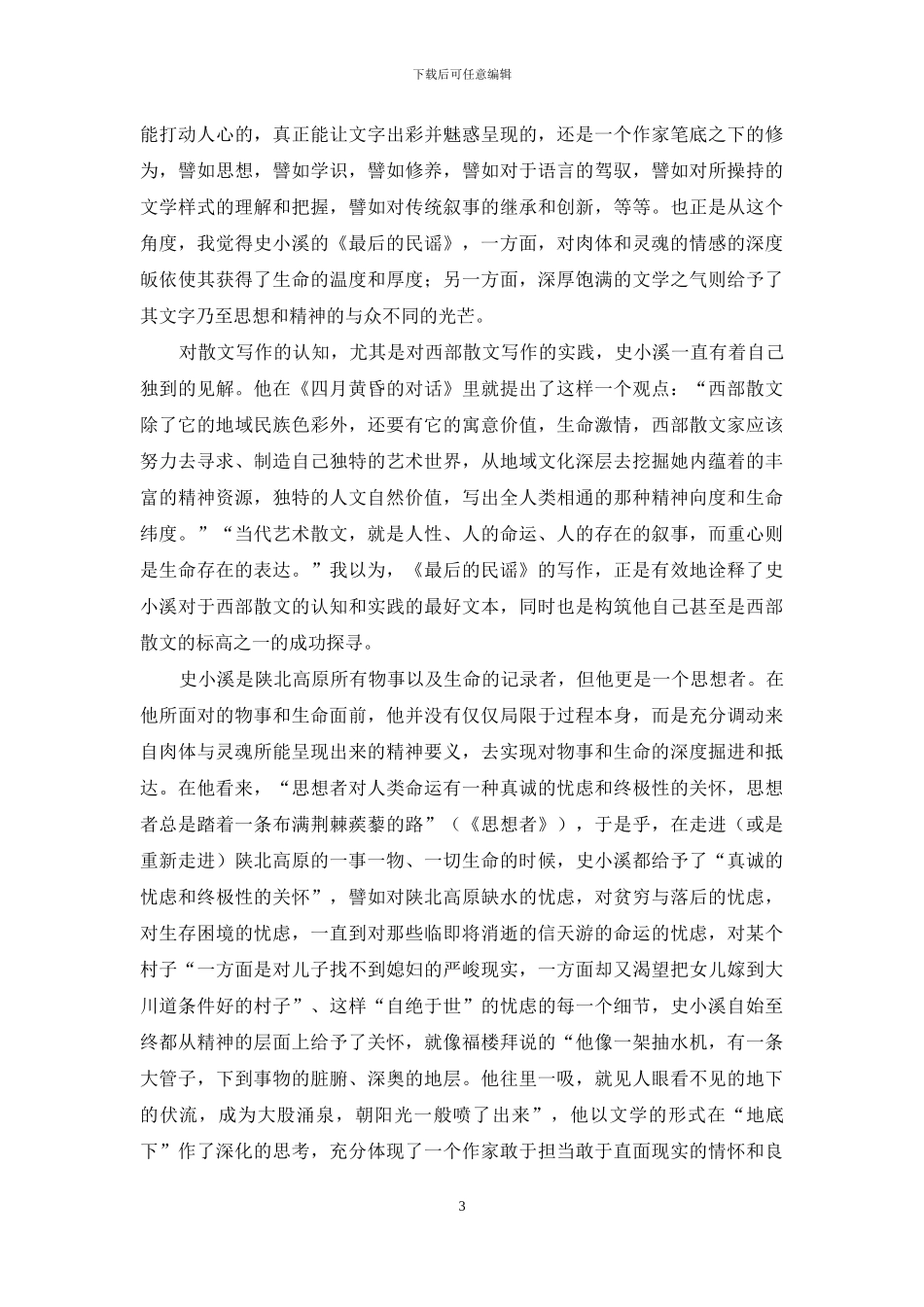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散文的精神之光散文的精神之光 我始终信任,作为民谣,它一定是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植物,无论是从肉体还是灵魂而言,它一定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或可说,一块土地,其精神的丰沛或是贫瘠,一定都与民谣的是否深化有关。到一个人,假如在其精神的血脉和枝蔓里始终有民谣的植被在那里郁郁葱葱,这个人则一定是有着某种诗意的信仰,就像荷尔德林的“诗意的栖居”一样,这个人,必定会让我们看到其跟大地“根土相连”的生命意识,亦可看到根植于大地深处的来自肉体与灵魂的最深切的皈依。 在读了史小溪记录和描写陕北高原的散文集《最后的民谣》后,这样的感觉再一次佐证了我对民谣以及渗透在民谣里的那些生命律动的理解和猜想。且让我们先来读一读史小溪在《最后的民谣》里摘引的一段信天游: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 受苦人希望过好光景。 打碗碗花就地开, 你把你的白脸脸转过来 这只是遍地生长在陕北高原上的信天游其中的几句。但就只这几句,却已把陕北高原的生活与爱情的情态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了,同时表现出来的,还有个体生命所寄寓在那块土地里的渴望和祈祷,所建立起的生命意识和情结,所缭绕不化的来自生命的向往和礼赞。 当然,这里的“民谣”,指的是狭义的具体的民歌意义上的民谣。我真正想要诠释的是广义上的“民谣”,是史小溪笔下的陕北高原上生长的一切物事,一切生命,以及贯穿其间的一切内在的精神秩序。 不过。这由小到大,由此及彼的象征性的深化,却是相通的。事实上也是 ,当史小溪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陕北高原一次次吟唱时,当他满怀深情地说出高原的一事一物,说出生于斯最终也隐于斯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情态时。他的确也正是说出了他对一块土地所寄寓的全部理想,尽管他所用的是挽抚的方式,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尽管他在怀着善良的愿望的同时,也真切地知道生长在黄土高原上的一切“民谣”,生长在高原上的曾经漂亮的精神风景正面临着解构甚至消逝的命运。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之所以不朽,是因为诗人说出了一种共通的生命情愫。假如放到文学写作的背景之下来考察,诗人还说出了一个作家与地域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诗人德漠克利特说:“具有一个好灵魂的故乡,就是整个世界”。一个特定的地域对于作家而言,一定是其“肉体与灵魂的根据地”,是其写作的“精神原乡”。譬如美国的南方小镇之于福克纳,中国的湘西之于沈从文,中国的山东高密之于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