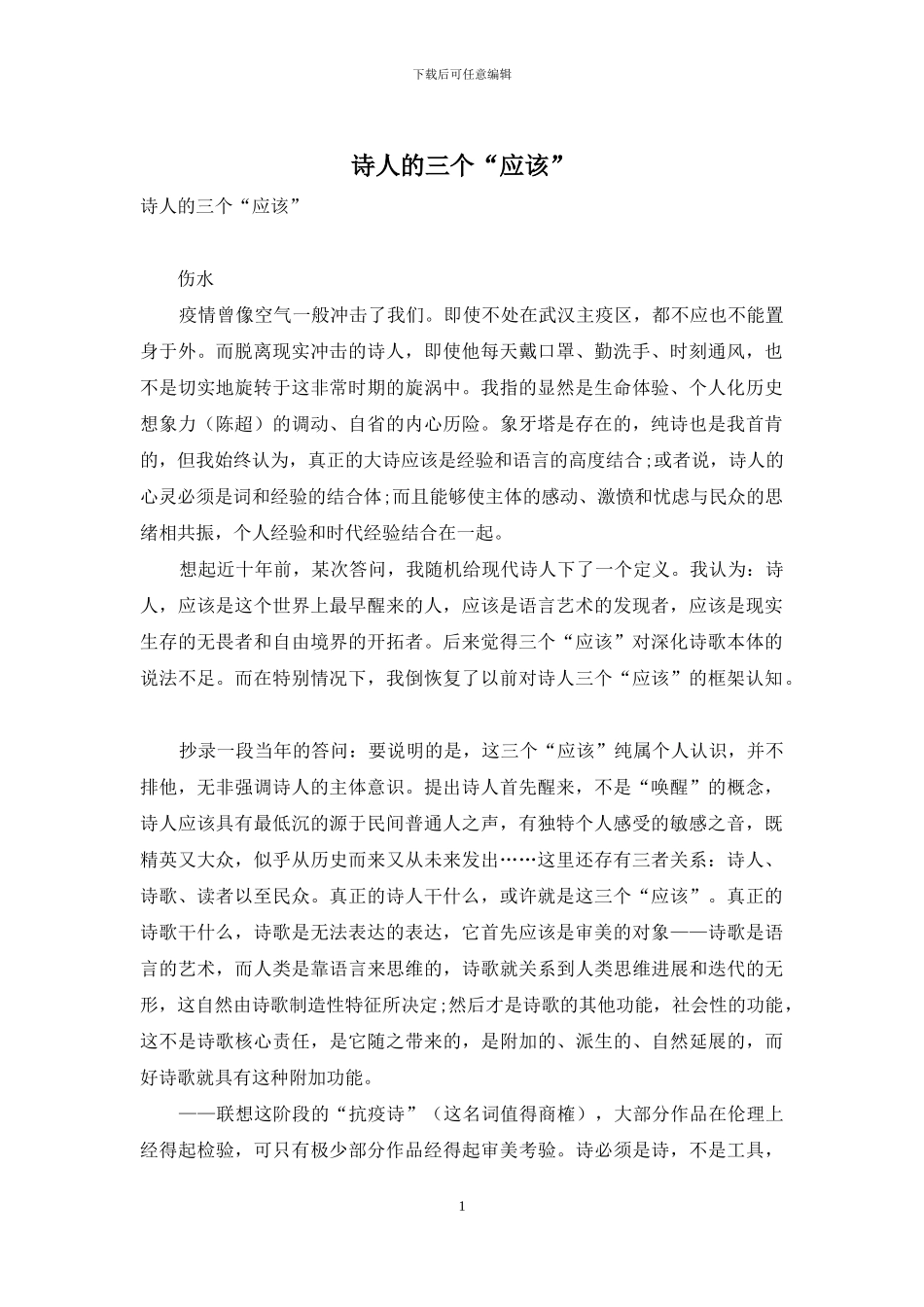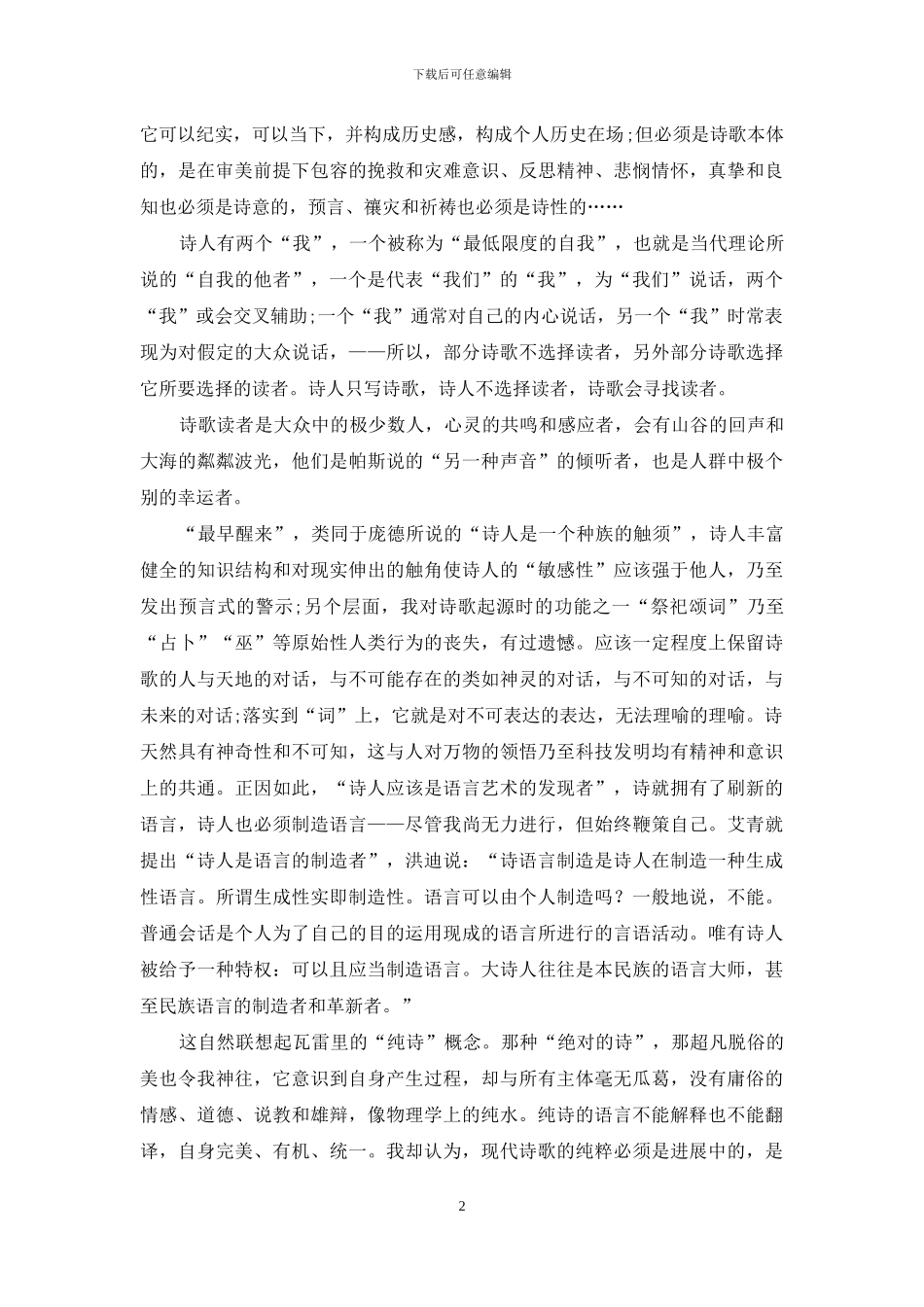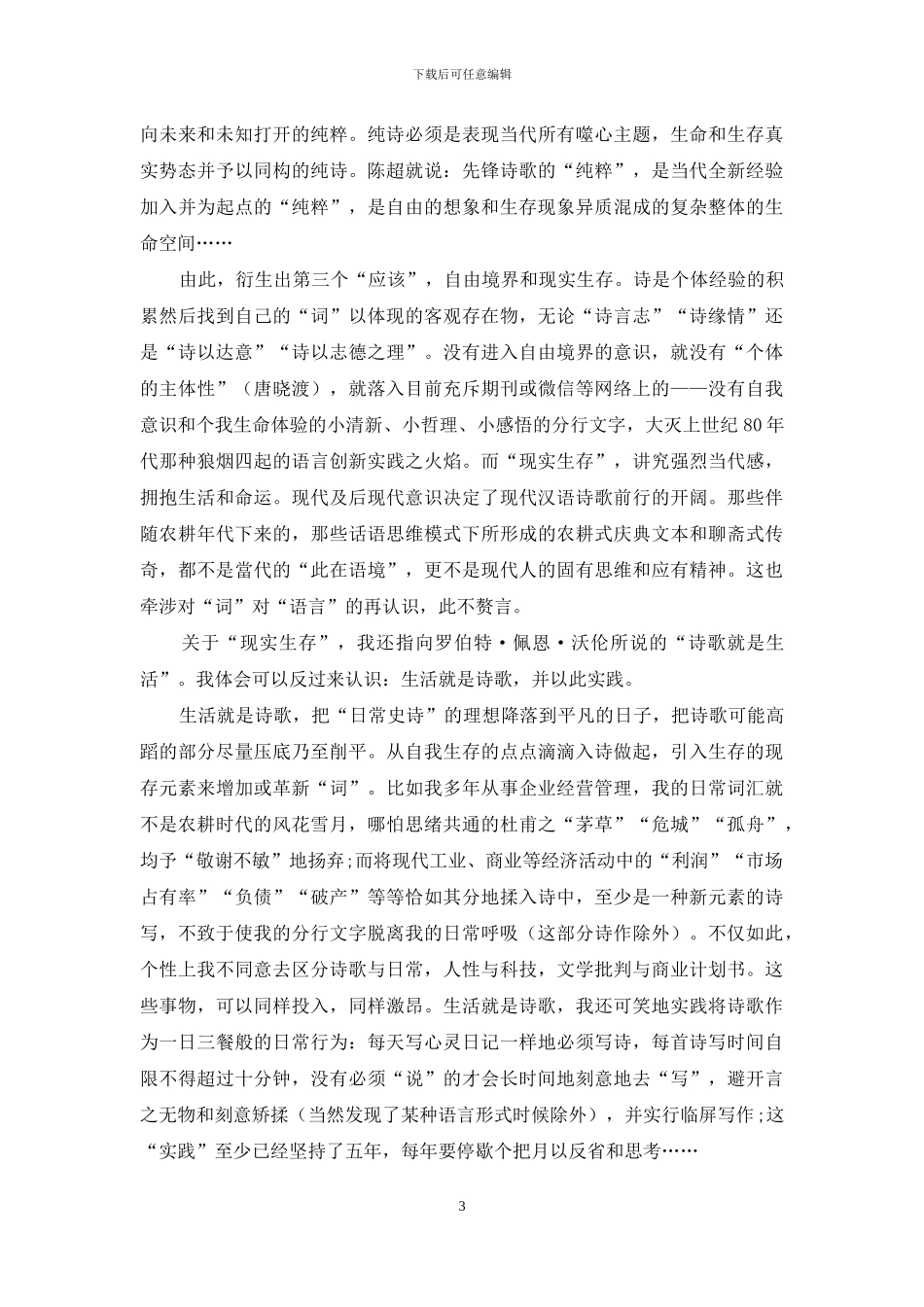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诗人的三个“应该”诗人的三个“应该” 伤水 疫情曾像空气一般冲击了我们。即使不处在武汉主疫区,都不应也不能置身于外。而脱离现实冲击的诗人,即使他每天戴口罩、勤洗手、时刻通风,也不是切实地旋转于这非常时期的旋涡中。我指的显然是生命体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陈超)的调动、自省的内心历险。象牙塔是存在的,纯诗也是我首肯的,但我始终认为,真正的大诗应该是经验和语言的高度结合;或者说,诗人的心灵必须是词和经验的结合体;而且能够使主体的感动、激愤和忧虑与民众的思绪相共振,个人经验和时代经验结合在一起。 想起近十年前,某次答问,我随机给现代诗人下了一个定义。我认为:诗人,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早醒来的人,应该是语言艺术的发现者,应该是现实生存的无畏者和自由境界的开拓者。后来觉得三个“应该”对深化诗歌本体的说法不足。而在特别情况下,我倒恢复了以前对诗人三个“应该”的框架认知。 抄录一段当年的答问: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应该”纯属个人认识,并不排他,无非强调诗人的主体意识。提出诗人首先醒来,不是“唤醒”的概念,诗人应该具有最低沉的源于民间普通人之声,有独特个人感受的敏感之音,既精英又大众,似乎从历史而来又从未来发出……这里还存有三者关系:诗人、诗歌、读者以至民众。真正的诗人干什么,或许就是这三个“应该”。真正的诗歌干什么,诗歌是无法表达的表达,它首先应该是审美的对象——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人类是靠语言来思维的,诗歌就关系到人类思维进展和迭代的无形,这自然由诗歌制造性特征所决定;然后才是诗歌的其他功能,社会性的功能,这不是诗歌核心责任,是它随之带来的,是附加的、派生的、自然延展的,而好诗歌就具有这种附加功能。 ——联想这阶段的“抗疫诗”(这名词值得商榷),大部分作品在伦理上经得起检验,可只有极少部分作品经得起审美考验。诗必须是诗,不是工具,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它可以纪实,可以当下,并构成历史感,构成个人历史在场;但必须是诗歌本体的,是在审美前提下包容的挽救和灾难意识、反思精神、悲悯情怀,真挚和良知也必须是诗意的,预言、禳灾和祈祷也必须是诗性的…… 诗人有两个“我”,一个被称为“最低限度的自我”,也就是当代理论所说的“自我的他者”,一个是代表“我们”的“我”,为“我们”说话,两个“我”或会交叉辅助;一个“我”通常对自己的内心说话,另一个“我”时常表现为对假定的大众说话,——所以,部分...